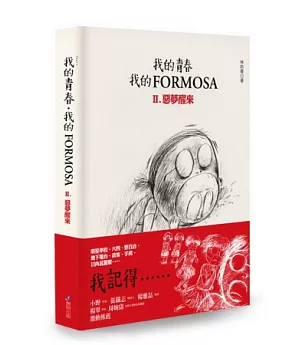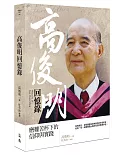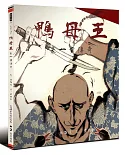自序
別想對我們的舌頭與腦袋開刀
當我還是個中小學生時, 戒嚴無色無味,但早年在暗處乾涸的歷史血淚, 透過「囝仔人,有耳無嘴」或「黑白講話半夜會失蹤」等話語,委婉地暗示市井小民明哲保身之道。爸媽最大的心願就是孩子「平安長大」,不要碰政治,課本裡寫什麼、老師怎麼教,背下來就對了。考試時記得吐出正確答案就好, 不要問太多問題,
「乖學生」就是模範生。學校老師要求我們使用字正腔圓的中文,中文不甚輪轉的阿公阿媽,曾讓我感到丟臉。
長大後,我才逐漸發現了統治者的歷史盲點,也看見了以「國民教育」之名, 銬在自己思想與靈魂上, 名為「政治意識型態」的枷鎖。
《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是我對童年的反思,也是對那個戒嚴時代的反省。當年學會看大環境臉色偎向「體制」, 學會鄙視自己的母語;當年還無法做出是非價值判斷之前,無條件地接受所有的「老師說」與「政府說」。這些體制的說法像晶片般深深植入自己的腦海與血脈內,我得拚命地讓自己吐完這些五四三, 接著為自己補課,補回從小被故意忽視或醜化的台灣歷史與文化。
去年2011年十一月,《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在法國出版,當時正是國內總統大選選戰期間。我在書本最後提出了對台灣現狀的幾點質疑 :當中國特使來台,我國政府撤除國旗,這樣做是否合乎常理?當中華民國在台慶祝「建國百年」,比民國歷史更悠久的台灣原住民成了活動亮點,
但他們的社會與經濟地位仍屬弱勢,語言與文化流失,這樣是否合理?法國讀者看了,也不了解,為什麼一個號稱自由民主與主權獨立的國家會出現這樣的怪事。
今年2012年秋天,這本書在台出版,湊巧也是台灣解嚴二十五週年。記得1991年剛上大學時,曾有同學半開玩笑說,野百合學運之後,學生運動應該沒有什麼議題可以發揮了。二十年過去,證明那位同學果然愛說笑。
獨裁政體在解嚴後看似惡靈退散,但我們的島嶼從未認真面對過去,沒有根除戒嚴時代留下的種種危害民主至毒。解嚴以後,懂得隨著時代快速進化的新舊鬼怪橫行島上。歷史、 人權、 國民教育、 司法、 生態、 勞資關係、 性別教育與文化等面向都有解決不完的問題,有心者前進得非常辛苦。
當我在籌備台灣版時,不想賣掉家園的民眾祖厝被市府拆,財團非法建物依舊盤據著原屬於全體國民的美麗沙灘,被官方與資方漠視的關廠勞工苦行到台北城示威,媒體則成了大老闆的馬前卒,踐踏著社會運動先驅血淚換來的民主資產, 舖天蓋地追殺異議者,連學生也不放過。
沒有了戒嚴,獨裁者們也都死去已久,但當今的新舊霸權要以更細緻的方式, 再次在島嶼未來世代腦中植入他們意識形態的晶片,割除異議者的舌頭,要我們默默看著他人遭受踐踏, 無力也無膽反抗, 人人最好當個「有耳無嘴」的乖順「囝仔人」。
還好,現在的台灣少年人不像我當年那樣盲從,他們有的跟著都更受害者捍衛家園,有的參與守護原鄉文化的草根運動,也有人支持弱勢的漢生病患,還有人串聯起來抵制媒體巨獸。有的背起吉他,有的拿起畫筆,以創作來為社會運動發聲。
當強權者想在台灣再造噤聲的長夜,這些年輕世代們以行動點起了一盞又一盞燈,這是真正照亮台灣前程的光明燈。我想起了更早之前島嶼上的點燈者, 面對強權壓迫,不論是日本或國民黨威權政府,他們甚至傾注了自己的前程與身家性命, 我們的島嶼才有今日民主尚能存活的土壤。
我誠心希望,有更多更多的人站出來,拒絕政商媒霸權對我們的舌頭與腦袋動歪腦筋, 讓解嚴後的台灣成為一個真正自由、 民主與落實人權的美麗之島, 而不是只有權貴安心度日的特權階級天堂。
林莉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