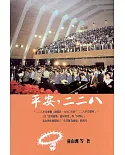作者序
臺灣的啟蒙時代
一九七○年代黨外運動興起,這波運動不同於十年前自由中國組黨運動,是以戰後新生代成為主力,追求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同時,並展開對臺灣自我歷史的探索,尤其關注時間上接近、具參照作用的日治時期社會運動史。
過去不被重視的臺灣歷史,該以什麼樣貌面世呢?一九七二年陳少廷在《大學雜誌》提出看法,一九七七年更明確標示以下定位:
在民國八、九年間,當時的臺灣知識青年,由於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自由思想潮流及祖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衝擊,乃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這項運動,在政治方面形成抗日民族運動;在社會方面形成社會改革運動;在文化方面,則形成新文學運動。這三個臺灣近代化的大運動,匯合而形成一股壯大的潮流。 (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
如此這般「臺灣新文化運動源自祖國五四運動」的論述受到官方歡迎,不斷被引用、延伸,「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化運動」成了臺灣雖已割讓給日本,但仍與中國歷史血脈相連的證據。
同一時期,國立編譯館以楊逵的短篇小說〈壓不扁的玫瑰〉「富於民族意識」的理由,納入中學國文教科書選文。戰後久經冷落的楊逵,是極少數仍然健在的日治時期作家,一時之間聲譽突起,享有同時代臺灣作家不曾有過的無比尊榮。文學刊物誇讚他「繼承祖國反抗日本侵略所表現的堅毅不屈、沉著勇敢的偉大傳統」;青年學生聚集到他的東海花園、以親炙朝聖為榮。(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在背誦這種教科書與民族主義歷史文化論述下成長的我,自然而然認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一面對被塑造為「壓不扁的玫瑰」的抗日英雄楊逵景仰不已;心中卻也納悶:殖民時期的日本政府怎麼這樣寬大仁慈?竟然能允許臺灣青年宣傳抗日,並且承繼祖國五四精神、發揚新文化運動?
七○年代末期臺灣社會已是騷動不安,仍在教科書與兩大報馴化之下的我,渾然無知,只會鸚鵡學舌般地為黨國辯護,不時與父親爆發衝突。我偷偷翻閱父親藏在暗櫃中的黨外雜誌,想要理解他的想法,但諸如「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的標題與報導更添困惑,挑戰因長期被澆灌而僵固的腦袋。國族教育論述啟人疑竇、家庭與學校的衝突,讓我的青春期在認知混亂中拉鋸。直到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場滅門血案當頭棒喝,心神震顫之下,同情與懷疑兩股力量交相激盪,黨國構築的銅牆鐵壁終於迸出裂縫,幾年之後土崩瓦解。
就如同今日對岸中國政府控制教育與資訊,塑造有利論述,以期黨國政權長治久安一般,昔日威權體制下的臺灣社會也是如此。臺灣歷史長期被忽略、被遮蔽,甚至成為禁忌。一九七○年代內外在環境衝擊、民間反身探索,官方意識形態與文化機制自動發揮作用,以抽離背景脈絡的方式剪裁歷史,吻合黨國史觀的論述於焉登場。
然而,一九二○年代日本在臺統治進入穩定期。已在帝國牢牢控制下的臺灣,為何會出現政治社會運動?又如何能夠不受殖民母國影響,卻與祖國關連?「臺灣新文化運動源自祖國五四運動」的說法,未面對臺灣是日本領土的事實,排除時代脈絡,突兀地強調臺灣人的「新文化運動」與祖國血脈相連。在官方容許下,楊逵成為抗日民族主義的活化石,日治時代生龍活虎的左翼色彩完全被抹拭。威權體制下,歷史是政治的奴婢,但蒼白無力的官樣文章,連思想貧瘠的學子也難以說服。
這些年少時期的困惑,成為日後學術研究的動力。我十分慶幸自己生逢其時,一九八○年代末期臺灣歷經反對黨組成、解嚴與民主化,不需像先行者一樣付出血淚代價,就能享有自由思考探索的空間,能貼近自己生長的土地,梳理群體共同的過去,體會前人的憧憬、憤怒與哀愁。
本書是對一九二○年代臺灣民主運動先行者們的致意。長久以來,他們曾經的努力與相關事蹟被政治力量掩蓋,社會大眾所知極為有限。全書以個人多年來的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希望透過淺顯的文字,以普及版型態呈現給讀者。(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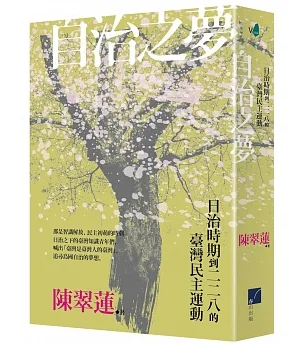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26):高雄縣政府檔案(二)[精裝]](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85%2F07%2F0010850768.jpg&width=125&height=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