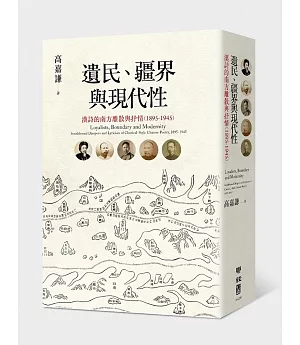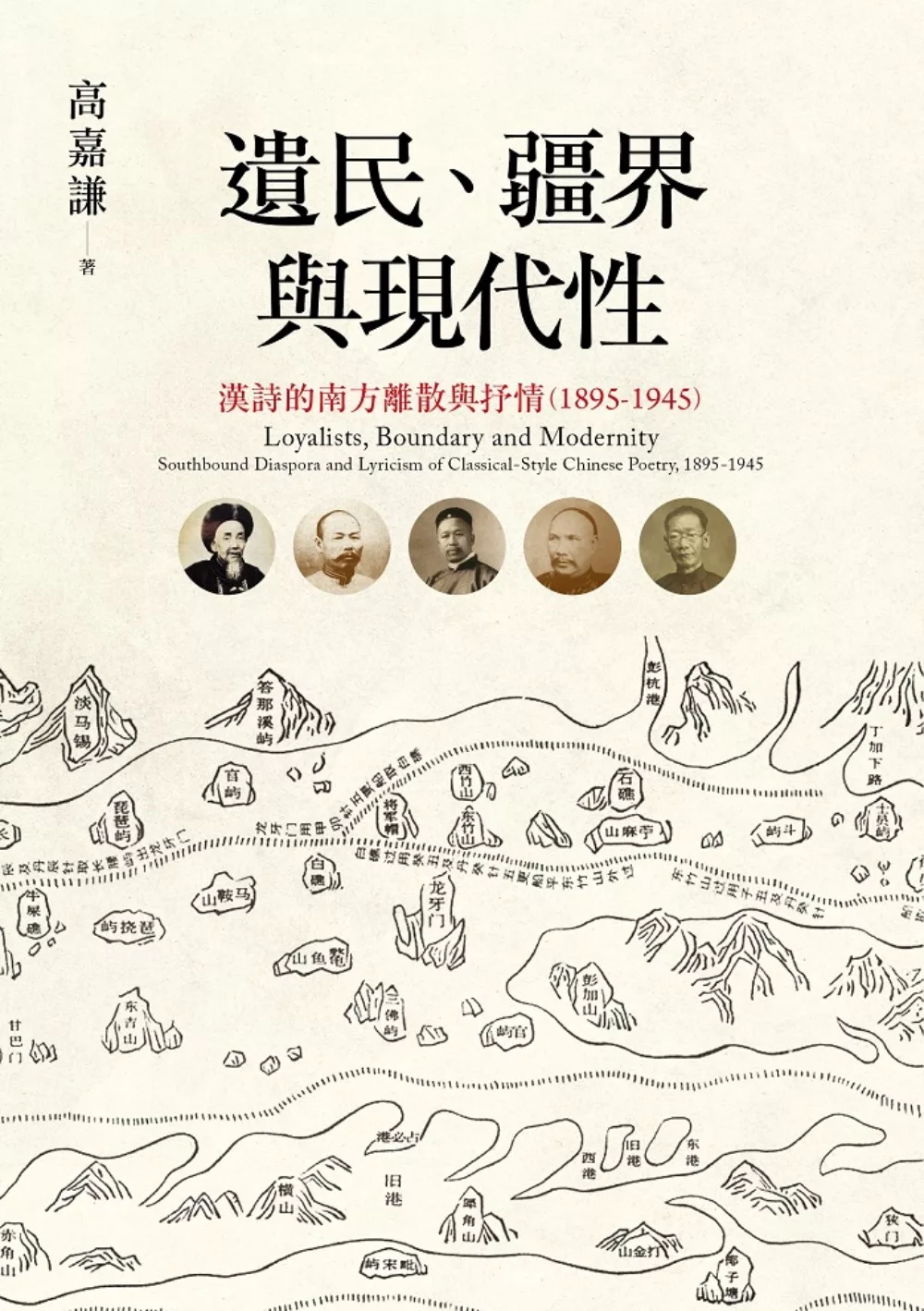序
開往南洋的慢船
南中國海方圓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公元前三世紀就已進入秦帝國的視域。中古以來,這塊海域上貿易航線大開,各種文明來往交織。16世紀初葡萄牙人來到馬六甲海峽,此後四百年歐美殖民勢力入侵,無所不用其極。與此同時,中國人─商旅和苦力,使節和海盜、亡命者和革命者─絡繹於途,帶來更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從馬來半島到菲律賓群島,從香港到爪哇,超過三千五百萬華裔在此落地生根,形成廣義的南洋文化。
這是高嘉謙教授專著《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的背景,全書的焦點則集中19世紀末至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中國境外的「南方」書寫。十八世紀以來東南沿海華人移民海外已經蔚為風潮,乙未割臺、辛亥革命,以迄抗戰軍興更讓許多別有政治、文化懷抱的士子文人也參與了這一行列。當神州大陸不再是托命之地,他們四處漂泊、流寓他鄉,成為現代中國第一批離散知識分子。那是怎樣的情景?康有為、丘逢甲、邱菽園、許南英、郁達夫……,南中國海一艘又一艘的船上,我們可以想見他們環顧大海,獨立蒼茫的身影。
比起當時絕大部分南下的華人,這批行旅者曾經接受正宗傳統教育,對時代的劇變因此有更敏銳的感觸。不論維新或是守舊,他們一旦被拋擲在故國疆域之外,自然有了亂離之感。而當他們將這樣的情懷付諸筆墨時,他們選擇古典詩詞作為書寫形式。面向一個充滿驚奇與嬗變的世界,他們頻頻回首,感時傷逝,因此有了朝代的─也是時代的─遺民姿態。
在名為現代的世紀裡,我們要如何處理這群文人的位置?高嘉謙的專書提出了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如果新的世紀以梁啟超所謂的「新民」作為動力,這些「遺民」也可能帶來新意麼?他們是時代的落伍者,還是主流的挑戰者?民國建立以後,主權、領土、疆界和國家論述興起,這群文人遠走國境南方以南,他們的離散書寫如何指向一種家國以外的空間想像?更重要的是,這些文人以舊體詩詞作為創作依歸。如此,他們的作品還能稱之為新文學麼?橫貫在這些問題之下的,當然是中國現代性的巨大挑戰。
*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是當代中文學界第一部處理這些問題的著作。全書共分為八章,討論遺民漢詩、南方離散,與現代文學的複雜關係。開宗明義,高嘉謙對近代遺民譜系重新做出考察。就傳統定義而言,遺民泛指「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遺民傳統可以上溯到周代,宋元以後形成有體系的論述。是在明清世變之際,「遺民」才陡然成為重要的政治選項,甚至延伸為一種獨特的主體意識、生活方式、論述場域。遺民遙念前朝,不勝黍離麥秀之姿,但在他們保守的政治立場之下,卻藏有捨此一步、別無死所的激進心態。這樣的心態一般謂之忠於正朔,但有鑑於明清之際主體思潮的轉變,我們也未嘗不可說是忠於自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明清遺民「一意孤行」的荒謬性和戲劇性,已經帶有淡淡的現代色彩。
遺民的本義,暗示一個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遺民意識因此指向事過景遷、悼亡傷逝的政治、文化立場。但高嘉謙提醒我們,明末清初朱舜水東渡日本,沈光文寄寓臺灣,他們將前朝故國之思帶往海外,因此將「遺民」意識的範疇從時間的錯置延伸為空間的位移。這一轉變其實和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若合符節。有清一代的海外政策儘管時緊時鬆,海疆的動盪已經不是遠在北方的朝廷所能掌握。
清室覆亡前後,有志之士「乘桴浮於海」不再只是抽象的寄託,而成為實際行動了。
是在這樣的認知下,高嘉謙展開了他的論述。書中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輯「從臺灣、廣東到香港」處理傳統定義的中國南方邊境的個案,包括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日本,丘逢甲輾轉廣東、南洋的行止;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在地文人王松、洪棄生等人去留、仕隱的決定;香港文人陳伯陶等在英國殖民治下,對宋代宗室遺民地景的發現─或發明。第二輯「從新加坡、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處理南方以南的南洋如何成為遺民「現場」,包括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遠走新、馬的始末;新加坡名士邱菽園的星洲風雅傳奇;郁達夫流亡新、馬,以及在印尼的神祕失蹤;臺灣文人許南英漂泊南洋、死於印尼的悲劇。
我們不難看出高嘉謙的用心:他筆下的遺民從嶺南、臺灣、香港一路南下,跨越南中國海,馬來半島,最後來到蘇門答臘。這樣的動線以往的遺民論述未曾得見,而所謂的「遺民」定義因此也有巨大改變。丘逢甲乙未後棄守臺灣民主國,康有為戊戌政變後流亡海外號召勤王,王松、洪棄生在臺灣與日本殖民勢力周旋,陳伯陶在英國殖民地香港遙望宋朝遺民,邱菽園定居英屬新加坡,郁達夫、許南英客死荷屬印尼。這些文人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從大清到民國、從宋代到明代宗室、從嶺南到閩南文化─表達他們的故國之思。由此形成的多元、分歧遺民屬性在在暗示以往的論述已經不足以應付20世紀初以來的劇烈變動。
更何況在此之上,高嘉謙筆下的遺民必須面對西方和日本所代表的異國的、進步的政經、文化與知識衝擊。比起前朝那些仍能夠遙望正朔,涕泣不已的遺民,丘逢甲等人無不顯示一種更根本的存在危機。「我們回不去了」,這些遺民最終的憂鬱來自一種面對時空斷裂,不知何所來、何所之的本體空虛。他們是「現代」降臨後的遺民。
「遺民」之外,高書另一重要命題是「疆界」。學者如葛兆光教授等早已指出,中國傳統地理觀念強調「疆域」而較輕「疆界」;後者的定義其實與現代國家的興起息息相關。疆域不只是土地的統領,也是文化上華夷之辨的判準,而疆界首先強調國與國之間的邊界劃定,以此作為主權的空間界線。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交戰國簽訂《西發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明訂國家基本結構和疆界,開啟我們今天熟悉的國際體制。與此同時,歐洲列國又大肆展開世界殖民行動,南中國海恰是兵家必爭之地。
中國被迫進入這一國際舞臺已經是十九世紀中葉的事。「天下」漸遠,作為現代國家的「中國」浮出歷史地表,而國家疆界齟齬每每在列強壓境下凸顯。香港、臺灣被割讓為殖民地只是最明白的例子。然而從香港、臺灣再南下,問題變得更為複雜。20世紀前半葉的南洋多為歐西殖民勢力侵佔,但在千百萬華裔移民或過客心中,南洋的地理卻另有意義。他們藉由文化、宗族和經濟的紐帶,將渺遠的唐山化為一處處在地的「現場」,竟然也形成無遠弗屆的疆域──一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不能想像的「想像的共同體」。
而在高嘉謙所處理的菁英社群裡,文人彼此更經過漢詩寫作與流傳,打造同情共感的知識和感覺結構。不論抒情言志或是采風酬庸,漢詩的持續力歷久而彌新。高嘉謙的重點則是,對於流亡或離散海外的孤臣孽子,漢詩縝密封閉的程式成為彼此不期然的通關口令。漢詩和遺民兩者之間產生互為表裡的關係。但如上述,新世紀的海外遺民快速移動在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地理現場,因而帶來始料未及的現代意義,那麼海外漢詩流轉在多變的語境和傳佈媒介間,是否也投射了中國國境內無從想像的新視野?「華夷之辨」挪到殖民、遺民、與移民的語境,複雜性更無以復加。
如果《西發利亞條約》之後的國際地理由主權國的疆界來決定,那麼跨越疆界的遺民,和跨越疆界的漢詩所形塑的多重空間,就有了始料未及的顛覆意義。準此,高嘉謙介紹了精采的個案。乙未割臺後,四位臺灣詩人做出四種選擇:丘逢甲內渡中國,另起爐灶;洪棄生株守彰化故園,以棄民自況;王松徘徊大陸、臺灣之間,終與日本殖民政權妥協;許南英為謀生計,遠走南洋。他們出入民族的、國家的、文化的以及詩歌的疆界,他們的詩作也反映同樣的移動軌跡。又比如邱菽園出身福建,幼年赴南洋,最終定居新加坡,因緣際會,成為星洲詩壇盟主,與他往還─或神交─的海外名士包括康有為、丘逢甲、到王松、許南英等。上個世紀初海外漢詩流動之頻繁,由此可見一斑。
*
20世紀儘管新文學當道,舊體詩的命脈其實不絕如縷。199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拜「重寫文學史」運動之賜,現代舊體詩開始得到注意,時至今日,已經蔚然成風。2014年學者齊聚德國法蘭克福,發表《法蘭克福宣言》,為現代舊體詩正名。即使如此,學界對這一文類的定位莫衷一是,或謂之封建傳統的迴光返照,或謂之騷人墨客的附庸風雅,或謂之政治人物的唱和表演。
如果我們按照新文學史公式,視現代文學發展為單一的、不可逆的、白話的、現實主義的走向,舊體詩聊備一格、每下愈況的特徵就愈發明顯。但文學史不必是進化論、反映論的附庸,更不必是意識型態的傳聲筒。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如果可觀,理應在於不必受到任何公式教條的侷限。其次,舊體詩只是傳統詩詞籠統的統稱。十九世紀以來,從文選派到同光體,從大陸的南社到臺灣的櫟社,從丘逢甲到呂碧城,舊體詩體制多元,題材有異,書寫、閱讀主體的位置也大相徑庭。換句話說,在文學現有的單向時間表下,我們往往忽略了「現代」這一場域如何提供了「共時性」的平臺,讓舊體詩呈現前所未見的多聲歧義的可能。
這一觀點引導我們再思考舊體詩的「詩」在傳統中國文明裡的意義,無從以學科分類式的現代「文學」所簡化。作為一種文化修養,一種政教機制,甚至是一種知識體系和史觀,「詩」之所以為詩的存有意義遠非現代定義的詩歌所能涵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文人學者衝刺於啟蒙和革命陣仗之餘,驀然回首,卻每每必須寄情舊體詩的創作或吟誦,彷彿非如此不足以道盡一個時代的「感覺結構」。恰恰是現代文人對舊體詩的迎拒之間,有關中國人文精神存續這類的辯證變得無比鮮活。
目前大陸學界有關現代中國舊詩的研究方興未艾,但對海外傳統卻鮮少注意。這當然是國家文學的疆界意識作祟所致。高嘉謙教授的專著及時推出,因此彌補了一大空缺。高以「漢詩」作為討論的文類命名,有其用心。相對「中國舊體詩」,「漢詩」所包羅的文化、地理意涵更為廣泛,何況海外漢詩寫作甚至有了與日本漢詩對話的層次。王松、邱菽園都有與日本殖民官員文人唱和的例子。我們於是看到海外漢詩的多重承擔:一方面延續中華文化的精粹,一方面卻也必然呈現異地與易地風雅的變奏。
如高嘉謙所指出,境外遺民與漢詩所形構的時空座標(chronotope)多半圍繞異鄉故國、咫尺天涯為起點。「詩可以怨」的主題無比鮮明。但既然這些詩歌是在海外離散的情境中生產,懷抱就有所不同。康有為亡命天涯之際,有緣在新加坡成為邱菽園的座上賓,詩酒酬唱之際,不禁感嘆:
中原大雅銷亡盡,流入天南得正聲。
試問詩騷選何作,屈原家父最芳馨。
這首詩歌感嘆中原正聲傾頹、大雅消亡,是典型孤臣孽子的聲音。但康筆鋒一轉,發現「天南」反而蘊育存亡續絕的線索。從傳統華夷之辨的立場來看,這是異想天開。但唯其如此,我們反而得見「詩可以興」的另類契機。康有為背負「十死身」亡命海外,卻藉詩歌喚起無中生有、死回生的可能。這不是一般審美定義的詩歌;這是古典「詩教」在一個海外現場的魂兮歸來。而這一現場必須奉屈原為名─畢竟那渺遠的「南方」放逐之地從來就是詩騷最動人的源頭。
另一方面,高嘉謙見證邱菽園的傳奇。邱承襲祖蔭,得以在新加坡廣納海外名士,儼然就是二十世紀的孟嘗君。值得注意的是,詩酒風流之際,邱同樣熱衷中國革命,也對新加坡的風土人情頻頻致意。邱的詩歌一般以「詩史」類型最為學者稱道,但高嘉謙指出邱詩的多樣性,狹邪旖旎、感時憂國、風土情懷,無不擅長。尤其他的竹枝詞和粵謳雜糅下里巴人的聲腔格調,或方言外語的諧聲擬韻,將地方色彩發揮得淋漓盡致。邱菽園的詩作因此為傳統興觀群怨的說法,增加了「天南」的向度。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高嘉謙對郁達夫的研究。郁是五四文學領袖之一,以浪漫懺情作品知名,但他的漢詩造詣深厚,充分反映一代新文人的古典底蘊。中年以後的郁達夫歷經國難家難,放棄白話創作,改以漢詩行世。他曾自嘲舊詩的薰染可以造就「骸骨迷戀症者」。但在頹廢的姿態下,他其實暗示白話文未必能直透現實。在人生無言以對的時候,反而是漢詩啟動繁複的隱喻系統,訴說(白話文)一言難盡的生命況味。尤其郁避難印尼的最後幾年,以漢詩銘刻現代中國人的離散困境,沉鬱曲折處遠超過他的白話作品。郁達夫戰後神祕失蹤,竟使他的詩歌和他的生命與肉身糾纏互證,共相始終。
近年華語語系研究受到重視,但仍以白話文學為主。高嘉謙另闢蹊徑,提醒我們在20世紀初的海外遺民漢詩裡,「何為中國」的命題和書寫變得無比尖銳。漢詩有其抱殘守缺的一面,但也從不乏厚積薄發的一面。兩者都在海外遺民詩人的作品和生命中戲劇性的展開,為華語語系研究提供了豐富題材。高在書末提到時移事往,海外漢詩可能成為一種「消失的美學」。文學史的推陳出新我們無從置喙,但既然漢詩曾經影響、形塑一代海外華語世界菁英的心志與行動,我們就有必要發掘、思考它興起和消失的因緣。何況套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式的觀點,華語文學的發展千絲萬縷,誰知道呢,未來巨變的可能,就蘊藏在那蟄伏的過去。
*
高嘉謙教授來自馬來西亞,在臺灣完成大學和研究所教育,目前執教臺灣大學。2003年我適在中央研究院客座,嘉謙主動邀我擔任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嘉謙得到臺灣中文學界完整的訓練,對近現代古典詩詞和詩學的研究尤有興趣。我雖非這一方面的專家,但有感他的真誠和敏銳,願意和他一起問學,也深得教學相長之樂。他果然不負所望,如今已是中文學界的優秀學者。
華人在馬來西亞的處境不易,在種種侷限下,有志向學的馬華青年紛紛出走他鄉,臺灣正是目的地之一。過去幾十年來他們在學界的成績有目共睹,嘉謙的專書就是最新的例子。我甚至要說,海外漢詩流動的課題非他莫屬,因為包含太多他自己的經驗和心路歷程。相對於此,兩岸中文學界對漢詩離散到境外南方以及南洋,又有多少關注?
新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新南向政策」當道,南中國海又見波濤洶湧。在一片喧囂中,我們可曾理解千百年來,一艘一艘往來南洋的船隻早已為這塊海域連鎖出無數航道,藉此華夷文明聚散播遷,蔚為大觀。我們對南洋的認識何其緩慢而有限!高嘉謙的研究正是此其時也。我敬重他致力學問的誠心,也珍惜彼此作為師生暨同事的情誼。是為序。
王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