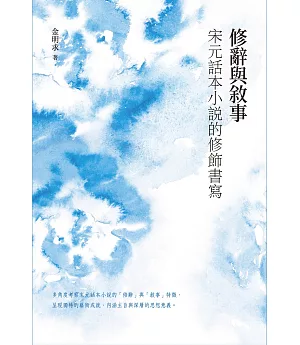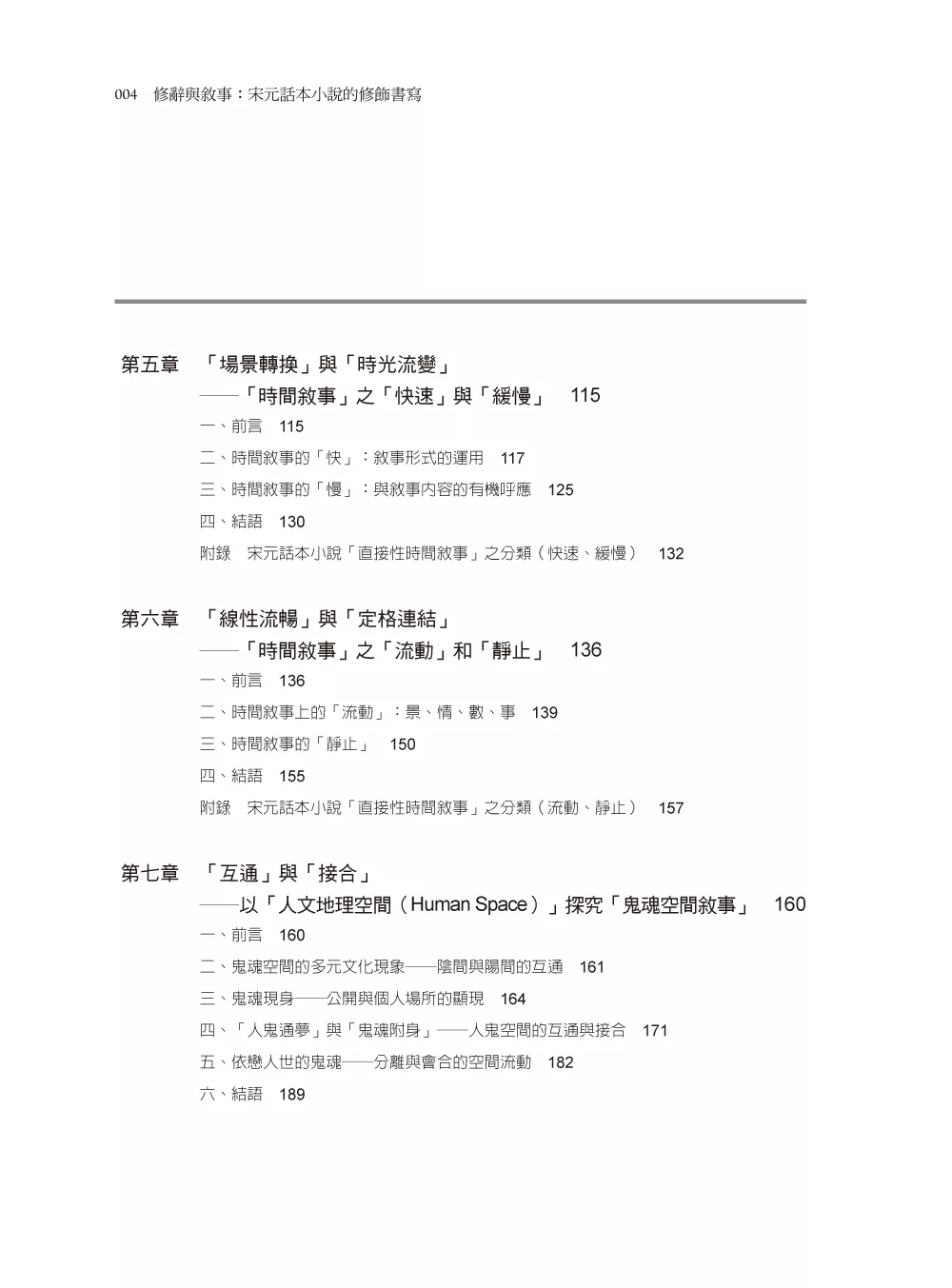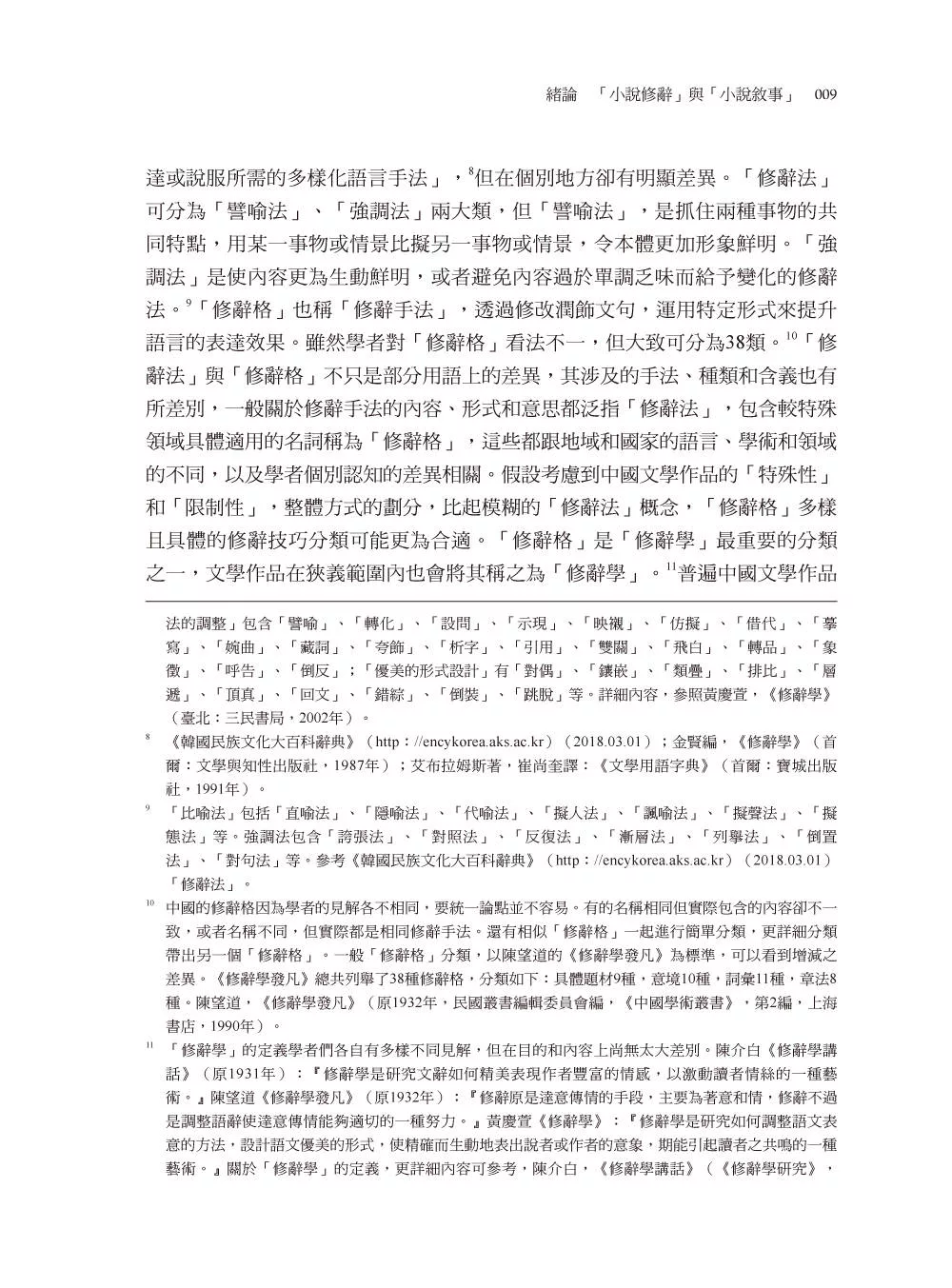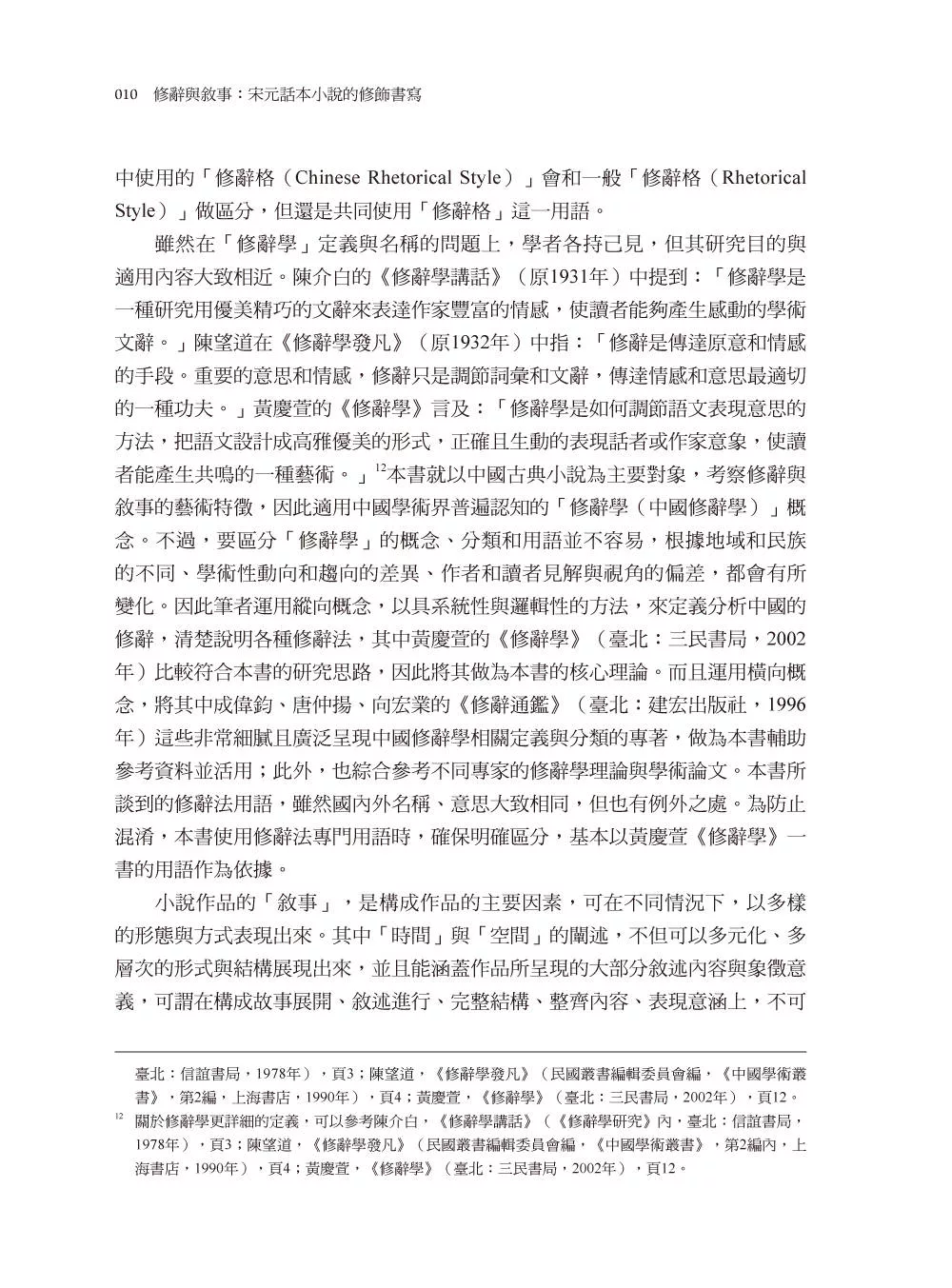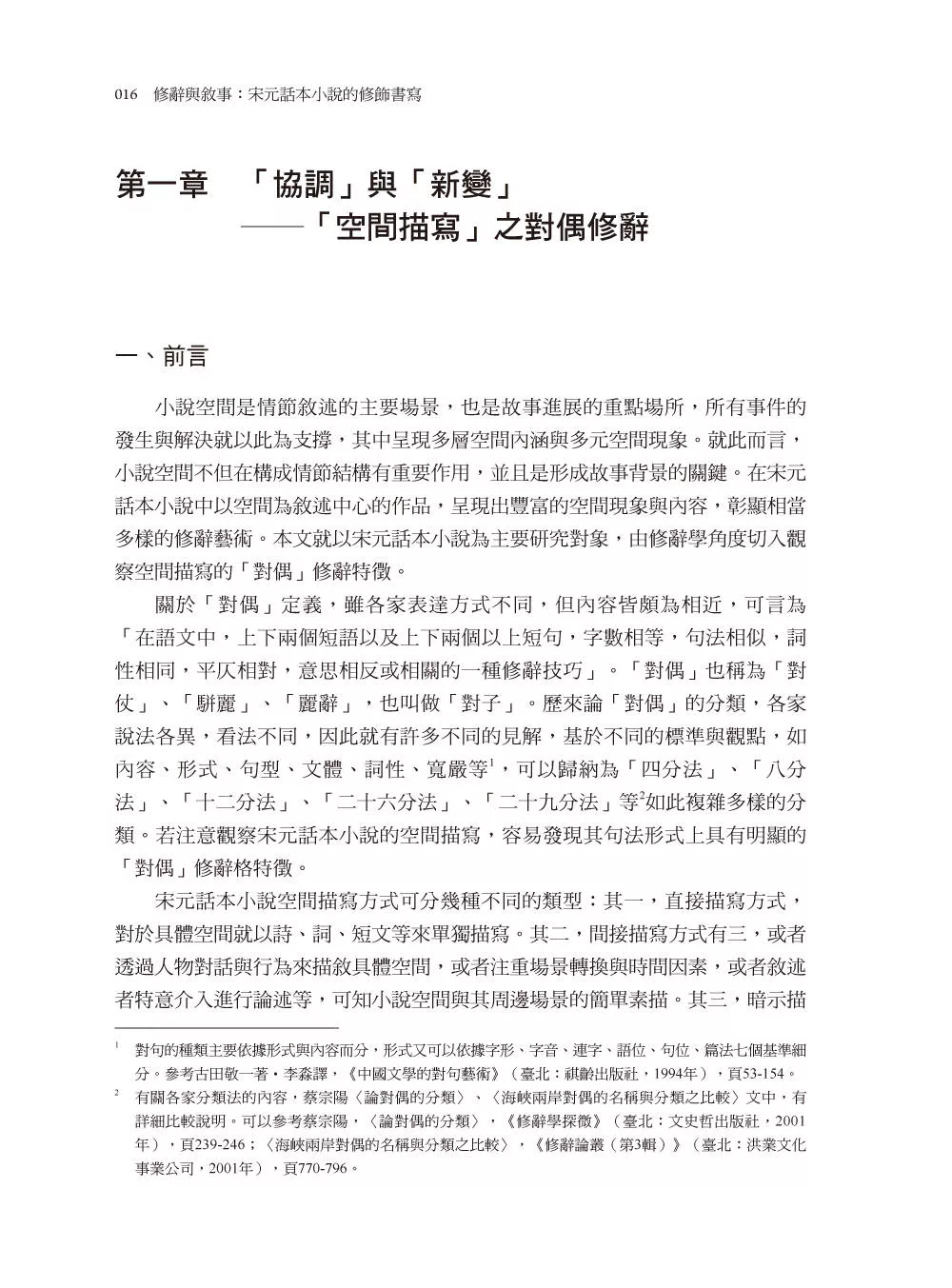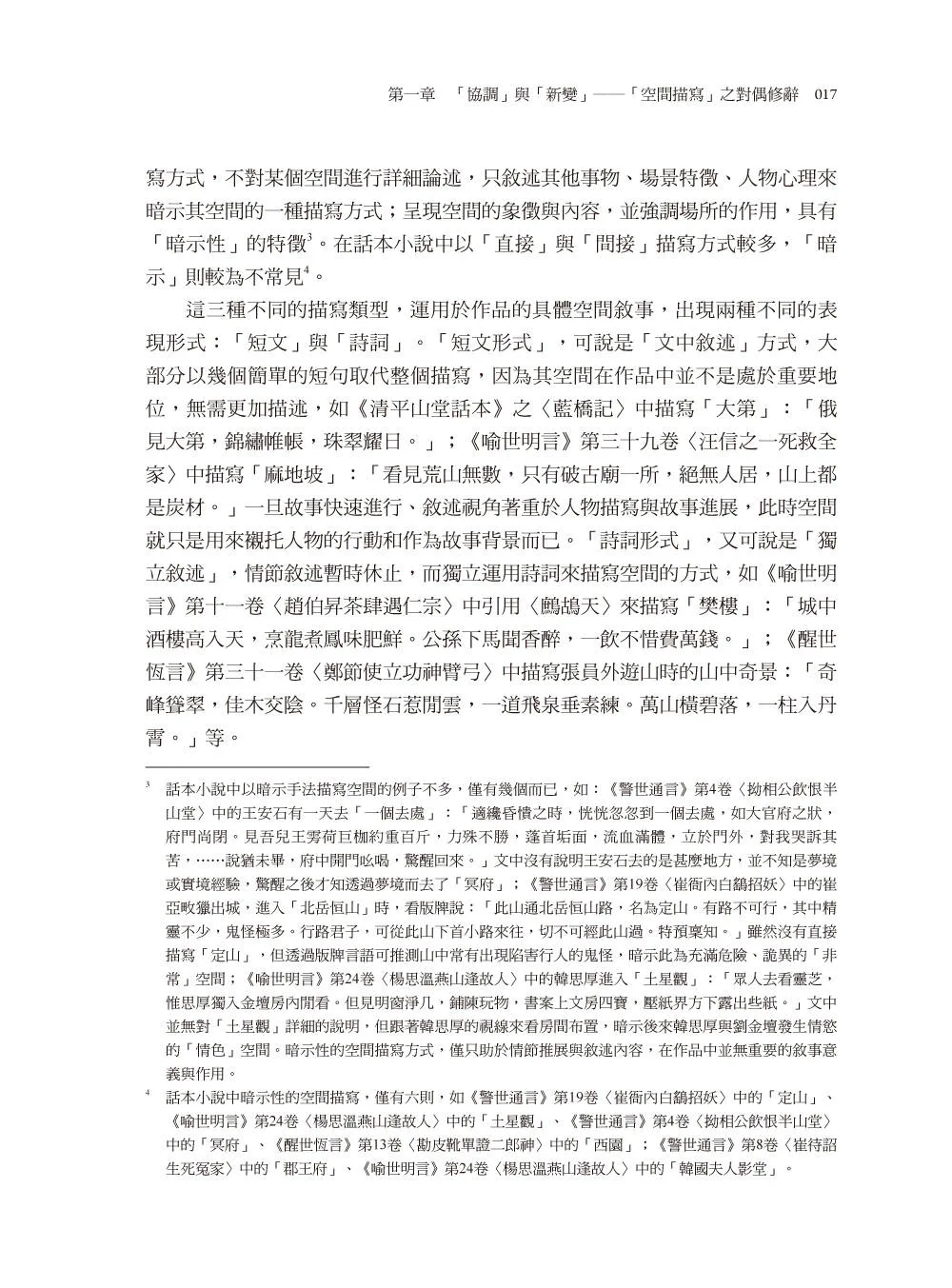序
緒論 「小說修辭」與「小說敘事」(節錄)
「小說」作為一種「說話」的文學藝術,發展於唐代。所謂「說話」,就是「講故事」,是屬於比較接近大眾的通俗文學。說話者須十分注意聽者的反應,只有這樣才能捕捉到聽者曲折跌宕的心情變化。起初「話本」內容比較簡單、粗略,但後來經許多宋元話本小說家不斷補充,再加上文人的加工與潤色,便成為體裁獨特、人物生動的小說。宋元話本故事題材非常寬泛,但每一篇的人物形象、主題思想、社會背景、文化意涵都不盡相同。宋元話本小說題材涉及當時社會生活各種層面,或說男女愛戀情事、或揭露官僚內幕、或處理訴訟案件、或宣揚某人發跡變泰過程、或談論神仙靈怪、風流逸事等。這些豐富廣泛的題材,反映了當時社會各階層的生活面貌與理想世界。
若要研究小說作品,須關注「修辭藝術」。小說作品中「修辭藝術」所涉及的領域,涵蓋的範圍極其廣泛,展現的內容與現象亦十分豐富;不但包含著作品的人物、主題、內容、象徵等部分,也觸及著語言、結構、敘述、形式特徵等面向。但如此龐大並廣闊的「修辭」理論,適用於具體的「小說作品」時,會被限縮在「小說修辭」的概念範疇內。「小說修辭」是作者透過自己在小說中的存在與介入,通過主觀評價與明確的目的、技巧與策略來呈現。其中讀者容易接受作者在小說中所塑造的人物、背景、主題,及其所表達的信念與價值立場,進而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建立一種積極的交流關係。
許多學者對「小說修辭」的淵源、定義、運用與理論等方面問題進行詳細的研究,其成果顯著,但對「小說修辭」定義問題仍各抒己見。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1921~2005)、落奇(David Lodge,1935~)及浦安迪(Andrew H.
Plaks,1945~)的「小說修辭」定義理論。這三人的看法基本上繼承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修辭理論。布斯把小說本身看作修辭的方式,並且注重作者介入性技巧的作用與交流關係;落奇強調小說修辭的說服性以及其產生的積極效果。浦安迪的定義較為周密完整,他特別注意到修辭「關係」的重要性。他主要從布斯所確立的小說修辭意義層次著手,對中國古典小說(奇書)文體進行分析。他將小說修辭分成兩個層次:廣義的小說修辭,是作者如何運用一整套技巧來調整和限定他與讀者、與小說內容之間的三角關係。狹義的小說修辭,則是特指藝術語言的節制與運用。前者屬於「西方的修辭觀念」,而後者則是「中國的修辭觀念」,可謂「語言字義」上的修辭,即語法相對應的修辭。
歷來從「修辭學」角度來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學者,大多限於語言字義上的修辭或一些修辭美學上的部分特徵,如描寫形式上的譬喻、誇張、對比、對偶等修辭格特徵,或偏重於描寫過程中所呈現的修辭美學與審美意識。雖然這些研究在形式修辭技巧、內容描寫修辭藝術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並無像浦安迪所提出的,從作者、讀者與作品之間的關係來深入研究修辭形式、結構與內容。但若糅合這些元素,進行多角度研究,則須將與「小說敘事」並論考究,使兩者互相滲透、互相連結。因此筆者擬以宋元話本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從廣義的「小說修辭」著手,來深入考察作品中較為常見較為複雜多樣的修辭藝術,以及敘述內容上豐富多義的敘事藝術、敘述形式與結構上彈性調整特徵等。
本書提及的「小說修辭」與「小說敘事」,仍以「修辭學」為理論基礎。「修辭學」的定義、分類、名稱、內容和形式,按照國家、語言、階層等的不同將呈現出多元面貌。見解雖然隨著東西方的邏輯脈絡、界定方式、學術領域之不同而產生相異,卻皆能互為參照與溝通。但各種論者對「修辭手法」、「修辭技巧」的名稱與定義,稍有歧見。「修辭學(Rhetoric)」,可稱之為「修辭法(Figure of
speech)」或「修辭格(Rhetorical
Style)」,可謂是在調整或修飾語言,提高表達效果的過程中,長時間形成的特殊構造和型態,在語言表達時依各個種類來進行分類,已是被認同的表現方式。「譬喻」、「設問」、「誇飾」、「引用」、「象徵」、「對偶」、「類疊」、「倒裝」等修辭手法都包括在其中。雖然「修辭法」和「修辭格」是「運用不同的方式傳達想法,表達或說服所需的多樣化語言手法」,但在個別地方卻有明顯差異。「修辭法」可分為「譬喻法」、「強調法」兩大類,但「譬喻法」,是抓住兩種事物的共同特點,用某一事物或情景比擬另一事物或情景,令本體更加形象鮮明。「強調法」是使內容更為生動鮮明,或者避免內容過於單調乏味而給予變化的修辭法。「修辭格」也稱「修辭手法」,透過修改潤飾文句,運用特定形式來提升語言的表達效果。雖然學者對「修辭格」看法不一,但大致可分為38類。「修辭法」與「修辭格」不只是部分用語上的差異,其涉及的手法、種類和含義也有所差別,一般關於修辭手法的內容、形式和意思都泛指「修辭法」,包含較特殊領域具體適用的名詞稱為「修辭格」,這些都跟地域和國家的語言、學術和領域的不同,以及學者個別認知的差異相關。假設考慮到中國文學作品的「特殊性」和「限制性」,整體方式的劃分,比起模糊的「修辭法」概念,「修辭格」多樣且具體的修辭技巧分類可能更為合適。「修辭格」是「修辭學」最重要的分類之一,文學作品在狹義範圍內也會將其稱之為「修辭學」。普遍中國文學作品中使用的「修辭格(Chinese
Rhetorical Style)」會和一般「修辭格(Rhetorical Style)」做區分,但還是共同使用「修辭格」這一用語。
雖然在「修辭學」定義與名稱的問題上,學者各持己見,但其研究目的與適用內容大致相近。陳介白的《修辭學講話》(原1931年)中提到:「修辭學是一種研究用優美精巧的文辭來表達作家豐富的情感,使讀者能夠產生感動的學術文辭。」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原1932年)中指:「修辭是傳達原意和情感的手段。重要的意思和情感,修辭只是調節詞彙和文辭,傳達情感和意思最適切的一種功夫。」黃慶萱的《修辭學》言及:「修辭學是如何調節語文表現意思的方法,把語文設計成高雅優美的形式,正確且生動的表現話者或作家意象,使讀者能產生共鳴的一種藝術。」本書就以中國古典小說為主要對象,考察修辭與敘事的藝術特徵,因此適用中國學術界普遍認知的「修辭學(中國修辭學)」概念。不過,要區分「修辭學」的概念、分類和用語並不容易,根據地域和民族的不同、學術性動向和趨向的差異、作者和讀者見解與視角的偏差,都會有所變化。因此筆者運用縱向概念,以具系統性與邏輯性的方法,來定義分析中國的修辭,清楚說明各種修辭法,其中黃慶萱的《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2002年)比較符合本書的研究思路,因此將其做為本書的核心理論。而且運用橫向概念,將其中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的《修辭通鑑》(臺北:建宏出版社,1996年)這些非常細膩且廣泛呈現中國修辭學相關定義與分類的專著,做為本書輔助參考資料並活用;此外,也綜合參考不同專家的修辭學理論與學術論文。本書所談到的修辭法用語,雖然國內外名稱、意思大致相同,但也有例外之處。為防止混淆,本書使用修辭法專門用語時,確保明確區分,基本以黃慶萱《修辭學》一書的用語作為依據。
(......中略......)
總而言之,宋元話本小說中「修辭」與「敘事」的結構與內容,經常互為反應、相互影響,不可分割。二者皆在「修飾」與「實質」之間進行調整,進而作為作品敘述的關鍵因素。小說作品本身就備有「虛幻」與「實質」間相互衡量和互為投影之特性,並有「修飾」與「真相」間調節與反應之特性,這兩者以「不同」卻「相近」的敘述方式,在小說內進行調和與接合,是完成作品敘事與結構的關鍵因素,並成為重要的藝術形式。因而,本書就以「修辭」與「敘事」的多樣理論與概念為基礎,以宋元話本小說為研究範圍,透過多角度視角來考察作品的「修辭」與「敘事」特徵。其中也插入相反的「負面角度」與相近的「連結角度」,仔細考察作品諸多藝術成就。以上研究敘事內容複雜、模糊、抽象,修辭現象規則、實質、具體,不但呈現出作品獨特的藝術成就,進而凸顯其中所內涵的主旨與深層的思想意義。在理解作品時,這可以更為接近故事的本意與主題,並獲得更為貼切、透徹的詮釋,更易於掌握作品中常被忽略的敘事與修辭方面的藝術成就。
本書選定的宋元話本小說,以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與《宋元小說家話本集》中所列舉的現存宋元話本小說為基礎,選取共同認定的宋元話本小說作品,再加以參考孫楷第、鄭振鐸、譚正璧、樂蘅軍、韓南、王定璋等人的考證與統計,選定46篇宋元話本小說,將其作為研究範圍。本書所引用的宋元話本小說的主要依據,是《清平山堂話本》、《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及《三言》部分篇目。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平山堂話本》與《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二本,原則上不根據校本改動底本文字,若有異錯字、脫文,則在校記中標明,但筆者在本書中引用文字時,均據馮夢龍《三言》(臺灣三民書局版)與程毅中《宋元小說家話本集》(濟南齊魯書社版)來補足、改正,並參酌《京本通俗小說》、《醉翁談錄》、《繡谷春容》等書。關於《三言》版本的資料,筆者仔細對照目前可見的《三言》刊本,本書所用的刊本是在鑒於各刊本利弊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誤字校正,加上正確標點、劃分段落,一般坊本所刪文字,悉以臺灣三民書局出版者加以補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