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期待霧散櫻開
櫻花,它的嬌妍讓人目眩,它的淒美使人落淚。《風中緋櫻》就是這樣一本淒美而引人入勝的悲壯史詩。它將歷史文獻分析、深度田野訪談和報導文學,做了絕佳的整合與示範。更難得的,它揚棄了非善即惡、非親即仇的簡易二分法,從人性與文化的面向切入,彰顯時局動盪下的悲歡離合,深刻的剖析了牽扯在這個事件中的核心人物的恩怨情仇。
1930年爆發的「霧社事件」,經過學術界和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努力,我們對這個震驚台灣和日本的「抗日事件」的起因和經過,大致上已經有了相當清楚的瞭解。但是,很少報告像《風中緋櫻》一樣,從社會和文化層面去探討「霧社事件」。在閱讀《風中緋櫻》這本書時,我們不只會緬懷1930年泰雅族人那一段英氣凜然的壯烈歷史,而且也將反思族群間的爭戰與和平問題。
從日本移植過來的霧社櫻花,和富士山下的櫻花一樣絢麗,而在日本人長期統治的影響下,一些泰雅族人也感受了日本文化的特性。其中最重要而影響深遠的觀念是「義理」,這是階層化的日本社會的核心價值:在上位者需盡心照顧下屬的福祉,而下屬亦須盡所有的力量回報,其中最有尊嚴而最受尊敬的回報方式是生命,這是「義理」的極致境界。在泰雅文化方面,傳統的泰雅族部落主要是由偏父系的親屬成員組合而成,部落成員共有一個祖先,所有部落成員不僅必須遵守祖先的遺訓,而且部落中任何成員的行為後果都由所有成員共同承擔。這種共負罪責、禍福與共的觀念,導致泰雅族人堅強而有效率的部落集體行動。只有從泰雅與日本文化的雙重影響這個角度,我們才會瞭解花岡一郎、二郎兩個家族的集體上吊,以及一郎的切腹自殺,這些悲壯的行動底層所蘊含的深層文化意涵。
族群衝突的超越和解決是本書的另一個重點。如果說莫那.魯道所率領的馬赫坡等部落族人的起義是悲壯的,那麼日本人對待中山初子和中山清的方式則是淒美的。《風中緋櫻》採用相當吸引人的報導文學手法來表現這些主題,它切入這些主題的角度不僅提供原住民文學另一種詮釋的角度,而且讓我們在看待族群間的衝突、對抗或調適現象時,可能用比較成熟的視野去思考與反省。《風中緋櫻》就是這樣一本悲壯、淒美而又嚴肅的書。歷史的軌跡不斷的往前延伸,但是族群的仇恨與罪贖卻可以不必重演,端視領導者的智慧。回首七十年前的「霧社事件」,期盼泰雅族人、原住民、台灣、中國大陸,以及整個世界,都能霧散櫻開,以喜悅快樂的心情迎接櫻花盛開的嬌妍與絢麗,而在落櫻飄零時不再感傷。
本書作者鄧相揚先生世居埔里,對於故鄉埔里的關懷與認同不言可喻,他不僅關心並積極參與埔里的社區發展工作,而且對地方文史工作也投入相當多心血,這方面的努力與成就可從他的自序略窺一二。相揚同時也是中央研究院多年的好友,本院各研究所的同仁到埔里地區進行研究時,他總會騰出時間,盡其所能的予以接待和協助,本院語言所的李壬癸,民族所的許木柱、潘英海、黃智慧,史語所的劉益昌等同仁,都已經與相揚成為長期的友人及研究的同好。作為中央研究院的行政主管,我要感謝相揚和埔里地方首長、民意代表及其他關心埔里的文史工作者,從前年開始,積極的推動中央研究院埔里院區的成立,當然我同時也感激院區預定地的地主台糖公司的慷慨與協助。懷著感激之心,中研院埔里院區無論是在學術研究主題或地方事務的參與方面,都將盡其所能的回饋埔里所有人士的厚愛,一如相揚對埔里的關心與熱愛。
自序 風中緋櫻
鄧相揚
1999年9月9日9時9分,正是「久久」的時刻,我和妻子美碧通過國際電話,彼此誓言要「久久」相愛,並且全家相約要在歲暮時,到紐西蘭的吉斯本,去迎接地球上千禧年第一道曙光的到來!
妻子帶著三個兒女,前去「白雲之鄉」的紐西蘭,接受kiwi的教育已有五個寒暑,我深愛家鄉,因此留在埔里,從事醫檢所的執業工作外,業餘之暇,繼續進行我的田野調查和研究的工作。我甚至立誓要出版有關「霧社事件」、泰雅族、平埔族群、邵族…等的十本專著,來獻給故鄉埔里和水沙連的鄉親,以完成我的職志和宿願,而《風中緋櫻》一書便是其中之一。
經過長時間的努力,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時許,我完成了這本《風中緋櫻》的初稿,也完成了積欠已久的宿願,心中的喜悅難以抑止。躺在床上準備就寢,雖然感覺有一點疲憊,但在昏昏沉沉中卻也不忍進入夢鄉,因為腦海中總是盤旋著《風中緋櫻》的故事情境……。
《風中緋櫻》一書,是我從事「霧社事件」田野調查工作十餘年來,繼《碧血英風》《合歡禮讚》《霧社事件》《霧重雲深》等拙作發表之後的第五本專書,主要敘述花岡一郎、二郎之所謂「花岡情結」和「花岡精神」糾葛的真相,期冀以報導文學的寫作方式,來呈現「霧社事件」的史實;由於情節複雜,因此,書中的人物故事,歷經十餘年時光的追溯工作,我才得敢落筆書寫。
興起我寫花岡一郎、二郎故事的緣由,要追溯到三十年前,先父鄧阿僯曾帶著我到廬山溫泉的碧華莊去泡湯,那正是高永清、高彩雲夫婦所經營的溫泉旅館,先父告訴我有關花岡一郎、二郎以及初子的遭遇,在那個年代,花岡的故事,大概埔里人都耳熟能詳。後來高彩雲帶著孫子從霧社來埔里求學,就居住在我家隔壁,因此有十餘年的時間,我常去造訪她,期間帶給她不少的困擾。每到她家拜訪及訪談,都會被她的日式儀禮所吸引,通常她也用日語和人交談,所以感覺上她像彬彬有禮的典型日本婦女,但事實上她卻是一位賽德克婦女,她經歷過不平凡的年代,可以說終其一生都充滿著傳奇,因此,要和她訪談以及要整理她的事蹟,必須要很認真做功課,始有成果。
在寫作期間,我驀然發現自己的頭髮已出現了不少白髮,心中總有時光流逝的唏噓之感,但當《風中緋櫻》初稿得以完成時,心中卻是暢快無比,於是我在歡心喜悅的笑靨中逐漸睡去…。
天搖地動,轟隆乍響,時間正是「1999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隔鄰三棟的五樓建築物應聲倒下,一道閃光和噪音把我從睡夢中叫起來,當我逐漸清醒過來之後,發現是地牛正在摧殘大地,我驚覺生命即將毀滅,夢想和希望亦將消失。
如果想逃命,一定會有「希望」,如果能夠保住生命,我將擁抱「來生」!如果有「來生」,我將完成宿願!
餘震不斷,房屋已呈半倒狀態,暗夜裡我從三樓的瓦礫堆中爬出來,驚慌中正想跳樓逃生,隔壁的蔡旭洲先生適時丟上一條繩索給我,我靠著這條繩索快速滑下,雖然滑下時受了輕傷,但很慶幸總算保住了性命,在此,我還要再次感謝蔡先生的救助之恩。
一片淒黑,尖叫聲和消防救護車的警嗚劃破了長空,地牛翻身的災情不斷傳來,逃難的鄉親擁擠在街上的空地中,許多人呼天搶地的哀慟著,因為他們的親人正陷在瓦礫堆中等待救援!汽機車橫衝直撞,每部車上都擠滿了老弱婦孺,大家慌慌張張的往郊區空曠的方向逃去!
地牛並沒有停止憤怒,整夜都在怒吼,又有更多的人擠進我住家前的圓環內避難,我蜷曲在圓環內的樹下,等待天亮,淒風苦雨讓我更陷在茫然無助中,我甚至不敢奢望會有黎明的來臨!
好不容易挨到黎明,天更烏黑,又下了一場苦雨,像是冬雨寒霜般的嚴慄,整個埔里陷在愁雲慘霧中,大家更是驚悸萬分,有人在暗泣,更有許多人在嚎啕大哭!
鎮公所倒了,警察局塌了,銀行毀了,醫院傾了,學校更垮掉了,而我執業的檢驗所也倒了,消息進一步傳來說我草創的「向陽文化博物館」也毀了,我感覺到天昏地暗,而心在飲泣!
餘震不斷,心更驚慌,焦慮寫在臉上,在忐忑不安中,我奮不顧身潛入危樓去搶救擋案,那是我耗費十餘年的青春所調查和搜集而來的資料,更是水沙連地區重要的文史資料,危樓內有許多「霧社事件」、泰雅、平埔族群、邵族等等的檔案資料,而《風中緋櫻》的稿件便是其中之一。
地動如此憾悸,在它的摧殘之下,襁褓裡的嬰兒失去了母親,白髮蒼蒼的老父失去了壯年兒子,而新婚不久的新娘,也失去了她的丈夫,地震不僅奪走人間的團圓至愛,更造成許多人的流離失所;災區裡哀鴻處處,我身歷其境,所以感受特別強烈,在自我哀憐中,我也感受到《風中緋櫻》一書中人物的心情寫照,驚濤駭浪的「霧社事件」,不也就是用恐懼和顛沛流離來寫的;而生命的真諦是,從苦難中重新站立起來,去繼續未竟的志業。
家園殘破,在埔里震撼過後的一片廢墟中,我全心全力和鄉親投入家鄉的重建工作,藉此讓自己忘掉憂鬱煩惱,一段時日後,我逐漸從憂傷中平復來,但還是常常無法安眠,就在無法就寢的許多夜晚中,我重拾撼動的筆,急書把這本《風中緋櫻》定稿下來,希望能作為「霧社事件」七十週年的紀念作,並以此獻給抗日烈士和遺族後裔,特別是高彩雲、高光華、郭明正、邱建堂、高信華等人,如果沒有他們的大力協助與支持,這本紀念作是不可能出版的。
台灣緋櫻仍然依戀著霧社的嚴冬,我感到今年的冬天特別寒冷,風裡,我看到霧社的緋櫻在空中飛盪飄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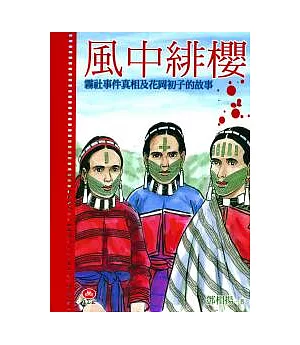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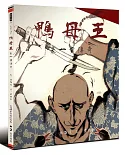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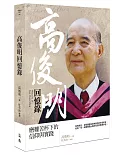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25):高雄縣政府檔案(一)[精裝]](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85%2F07%2F0010850770.jpg&width=125&height=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