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奧賽美術館的右翼
文∕陳漢金
奧賽美術館從一座廢棄的火車站改裝成美術館的1985年,筆者剛到巴黎求學。此後,它逐漸成為我在索爾邦大學修習音樂學之外的「第二個學校」- 靠著一張研究通行證,我能夠避開等候入館的人群,從側門自由出入,進去看畫、聽演講或聆賞該館的晚間音樂會,而有助於我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藝術發展上的跨領域認知。
最初,我經常隨著人潮往左側擠,那邊有庫爾貝、米勒的寫實主義畫作,以及所有的印象派畫家的創作,是整個美術館的大熱門。後來,我也到冷清的右側逛逛,發現那兒陳列的是從底樓的學院派到二樓象徵主義的作品,這些作品顯得較難懂而乏人問津。
「奧賽」的左側僅靠著塞納河岸,視野寬闊,光線充足 - 寫實主義與印象主義是對光線敏感的「白天的藝術」。奧賽的右側則緊臨著街道,不僅沒有視野,光線也相當暗晦 - 象徵主義是「夜晚的藝術」,太充足的光線是有礙神秘與夢幻的。館方當初的如此安排,應不是重「印象」而輕「象徵」,而是考慮到兩個畫派各自的特性,讓它們能夠「各得其所」。奧賽的左側,就像法國政治的「左翼」(les
gauches)一般,傾向於自由放任,強調「進步」的精神 - 寫實派與印象派的前後呼應,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實證主義(positivisme)與社會主義(socialisme)盛行之下興起的。至於奧賽的右側,就像「右翼」(les droites)一般,較珍視傳統的價值、較輕忽物質性而注重靈性、精神性
-「世紀末」象徵派與頹廢思潮的興起,可說是寫實派與印象派的反作用,它們嘗試逃脫現實,沉緬於唯美的、虛擬的幻境中。
起初,筆者受到根深蒂固、人云亦云「印象派音樂」觀念的左右,想到奧賽的左翼去尋找德布西,卻找不到他,後來才發現,原來他的靈魂是徘徊在右翼幽暗的長廊中,與許多象徵派畫家共同作著「白日夢」-
別忘了,德布西是《月光》、管弦樂《夜曲》、《格拉納達夜晚》、《月落古寺》的作者;在《牧神午後前奏曲》、《比莉蒂絲之歌》、《排簫》中,他夢到了古希臘;在《天國的少女》、《沉沒的教堂》、管弦樂組曲《春天》中,他經由時光隧道,回到了中世紀;在《寶塔》、《月落古寺》、《金魚》、《海》裡,他神遊於遙遠的、虛構的東方世界。德布西可能不屑於寫實主義、印象派「散文」式的平鋪直敘、浮光掠影,而偏好細緻微妙、委婉含蓄的「象徵」詩境,他是以音樂寫詩,而不是以音符寫散文。
「印象派音樂」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早在德布西在世時,已成為一個迷思,儘管德布西本人極力反對這個「標籤」不適宜地被貼在他的音樂上。此詞長久以來大行其道之際,最近數十年來,卻已逐漸激起反對的看法,例如美國牛頓出版社(Norton)《西方音樂史》的第五版(1996年)宣稱:「德布西是曾經對二十世紀音樂產生根本影響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風格中的一個面像 - 經常被誇大的 -
以印象主義一詞加以概括形容」。在同一部著作的最近一版(2006年),則改成:「德布西的音樂經常被稱為印象派音樂,以便和印象派畫家們類比,但是它卻與象徵主義較接近…」。
德布西的音樂被稱為「印象派音樂」,就像整個奧賽美術館被一般人俗稱為「印象派美術館」一般,是不明究竟的稱法,然而要打破這個迷思卻是不容易的。無論如何,打破這個迷思的確有其必要,唯有如此才能認清德布西兼容傳統與創新、頗具前瞻性的音樂。在此書中,筆者嘗試透過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世紀末」政治、社會、文化背景的描述,音樂史、美術史與文學史的比對,聽覺藝術與視覺藝術的類比研究,以闡明德布西音樂的真正面貌。
由於德布西的音樂創作博大精深,涉及管弦樂、室內樂、鋼琴曲、藝術歌曲、清唱劇、歌劇、舞蹈音樂諸領域,筆者在此書中,先是把介紹的範圍限定在室內樂與管弦樂,期盼能夠在此較小的範疇內,將基本觀念交代清楚之後,將來有機會再繼續從事德布西其他樂曲種類的探討與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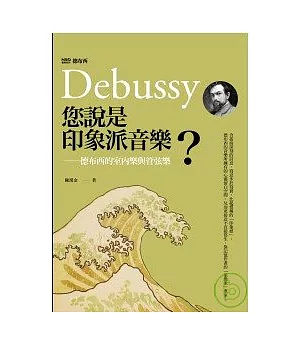

















![聽見臺灣的聲音:江文也作品集2016-[2CD]](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76%2F01%2F0010760154.jpg&width=125&height=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