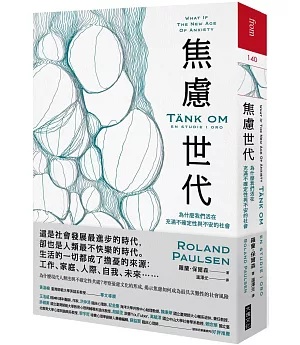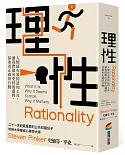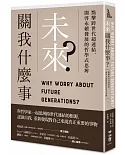導讀
面對焦慮,學習與不確定共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黃涵榆
《焦慮世代:為什麼我們活在充滿不確定性與不安的社會?》(後引為《焦慮世代》)譯自目前任教於瑞典最高學府隆德大學的社會學家羅蘭.保爾森(Roland Paulsen)2020年以瑞典文出版之新書Tänk om : en studie i
oro,為目前獲得翻譯版權六個國家語言譯文之一。《焦慮世代》一開始就提出一份值得重視的統計數字:憂鬱症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躍升為全球第四大常見病因,在二十一世紀第十年來到第二位,在世界衛生組織在二〇一七年提出的報告裡,已成為首位,而全球罹患憂鬱症的人數在二〇三〇年左右將增加近百分之二十。當然,焦慮並非是臨床上的憂鬱症患者的專利,它已是當代普遍的情緒氛圍。面對精神問題的普及化,我們似乎無法確定更多教育、就業機會或社會福利就能解決問題。作者保爾透過哲學、精神醫學、生物學、文學與電影的跨領域方法,以及近距離的個案訪談與田野考察(不論是擔心掉落河裡的腳踏車會造成污染毒死河中的魚的丹尼爾,或是總是坐在公園椅子上自言自語長篇大論的女人),兼具宏觀的歷史視野與個案研究的親近與細膩,交織出不同的思考路徑和觀點,希望能夠解釋為何憂慮和恐懼會成為主導生命的因素。
《焦慮世代》一書中的「焦慮」是一個精神「問題」概括性的用語,涵蓋恐懼、憂慮、恐慌、悲傷、孤單、愧疚、恥辱、癡迷等;懼高症、疑病症、社交恐懼症、食物中毒恐懼症都是常見的焦慮類型,工作、學業、經濟收入、人際關係、性取向、自我形象、生命無意義等經常成為焦慮的根源。這表示「焦慮」並非一個具有清楚界線、單一的身心狀態,而是具有擴散性和不確定性的特質。生物取向的現代神經醫學也許會依據一些個案,主張焦慮導因於腦額葉皮質、基底核和丘腦之間的傳導失調,現象學與存在主義哲學把焦慮解釋成一種主體面對存有的根本情境或虛無的情感狀態。在日常情境裡,我們總習慣認定焦慮是一種紊亂的情緒狀態,麻煩的是思考不見得能夠解決情緒問題(受精神問題所苦的哲學家比比皆是)。即使事實擺在眼前或者經過透徹的思考,不安的感受還是有可能引發「反事實思維」,為過去懊悔,為未來惶恐。
保爾森從宏觀的歷史視角指出,現代人普遍沒有辦法與不確定性共處,《焦慮世代》主旨之一就是要考察我們是如何走到這樣的境地,焦慮何以具有時代性或者為何會在現代社會裡擴散。計算與運用時間的方式、生活型態、生產模式、經濟收入等都是相關因素,只是當中的因果關係也許並不如我們所想的那麼直接。例如,焦慮的程度和工作與財務壓力不必然成正比,好比我們讓高收入和社經地位的人知道,他們可以或其實過得好好的,對於減輕他們的焦慮不見得有幫助。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凡事力求精準計算,各種事物與活動也似乎都在加速之中,但是我們並不因此能有更多時間安心悠閒地過活,時間總是不夠用,時間依舊與我們的經驗和感受脫離或疏離,躁鬱症和妄想型思覺失調症患者飽受時間催促,憂鬱症和非妄想型思覺失調症患者容易覺得時間變慢甚至停滯。而更多的(消費、職業、生活方式等)選擇反而徒增選擇的困難,如同整體的經濟成長和各種進步不必然使人更幸福,反而更讓人對未來信心不足,覺得生命意義遞減⋯⋯
要理解這樣的矛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焦慮世代》提供了一些思考引導。整個西方社會和資本主義文明發明了各種消除未來的不確定性的方法,企圖將風險極小化,將機會極大化。這其實反映了整個西方現代世界機械式的宇宙觀和「除魅」的發展方向,不論是人類的身體、思考、自然、宇宙、基因遺傳都被套入規則或定律。我們習慣用科學解釋一切事物,但是科學無法告訴我們該如何活著,我們甚至覺得風險變得無所不在,從恐怖主義攻擊、像是COVID-19這樣的大型傳染病、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到股市崩盤、通貨膨脹、肥胖、食安,到隱藏在日常生活角落裡的各種騷擾和暴力。作者保爾森提醒我們,風險總是不離敘述和想像,透過媒體戲劇性或誇大的傳播,類似恐怖主義攻擊和大型傳染病較易引起注意,滋生更多的風險,即便慢性病或其他日常的意外死亡人數更高卻容易被忽視。我們不可能完全控制風險,保爾森強調,「在每種文化中,焦慮和擔憂都找得到蓬勃發展的養分」,宗教信仰、性、侵害以及人際關係是四個最為顯著的風險區域。
毫無疑問地,個人也早已是個岌岌可危的區域,各種風險、自我評價、孤單、性壓抑等等,都讓人焦慮不堪。但是當我們企圖理解甚至解決個人精神問題,我們必須先看清一個事實;病痛與受苦的理解、感受、診斷與治療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都受到家庭成長背景、社會、文化或宗教影響,不單單是個人看不看得開的問題。我們甚至必須肯認每個人不論性別、年齡、職業、家庭的外在內在條件,都有焦慮的可能甚至權利,都願意去理解它,無須感到羞恥與慚愧。這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有集體的認知、環境、行動、體制和政策形成的支援網絡。如作者所強調的,「精神健康是由社會所創造。精神健康的存在與否,基本上是一項社會指標,因此社會與個人行動亦不可少。我們不僅得將焦點擺在集體行動的效力上,更得關注個體行動的效果。只將注意力擺在個體症狀上,就會造就所謂的『去肉身化心理學』,將個體腦中的思緒與感受從社會結構和背景中抽離。」強調精神問題和健康的集體性也意味著丟棄先天精神病態的假設(沒有人先天或生下來就註定是精神病患者),那也等於把精神病患視為無法修理的壞損機器。
《焦慮世代》另一個值得重視的面向是建構與想像精神醫學與醫療社會的未來。當精神問題越來越普遍,單純依靠談話診療的精神分析和生物醫學導向的精神醫學都引發不少小的檢討聲浪,精神醫療需要進行什麼樣的改革、納入什麼樣的非西方元素自然會是重大課題。書中提到迷幻劑與談話診療法並用的嘗試,或是史蒂文.海耶斯(Steven
Hayes)提出的「接納與承諾療法」(acceptance-commitment-therapy,簡寫ACT)強調保持思想、感覺和印象的原始樣貌,盡量不去干涉、抵銷或淡化它們。作者也推崇佛教思想與當下的偶然共存的修為,認為那能提供讓人從煩優中抽離的契機。佛教思想如何發揮精神療效也許見仁見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可以試著想像控制與治療之外的可能,如作者所言,「藉由肯定、接納不確定性,我們能發現每份擔憂都包含一粒真理,使我們更接近神秘,體悟到我們知道的是如此地少。接納不確定,我們就有機會去了解,原來認為自己能掌控一切是多麼瘋狂的想法。」這當然不是最終的解答,但至少是面對普遍化的精神問題必要的態度。
筆者覺得台灣長久以來都不是一個細心面對和回應他人感受的社會,對於精神問題若非抱持刻板印象,就是築起一道堅固的牆抵擋在外、視而不見,若要建立一個良善的醫療社會,我們還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像《焦慮世代》這樣的書讓我們看到改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