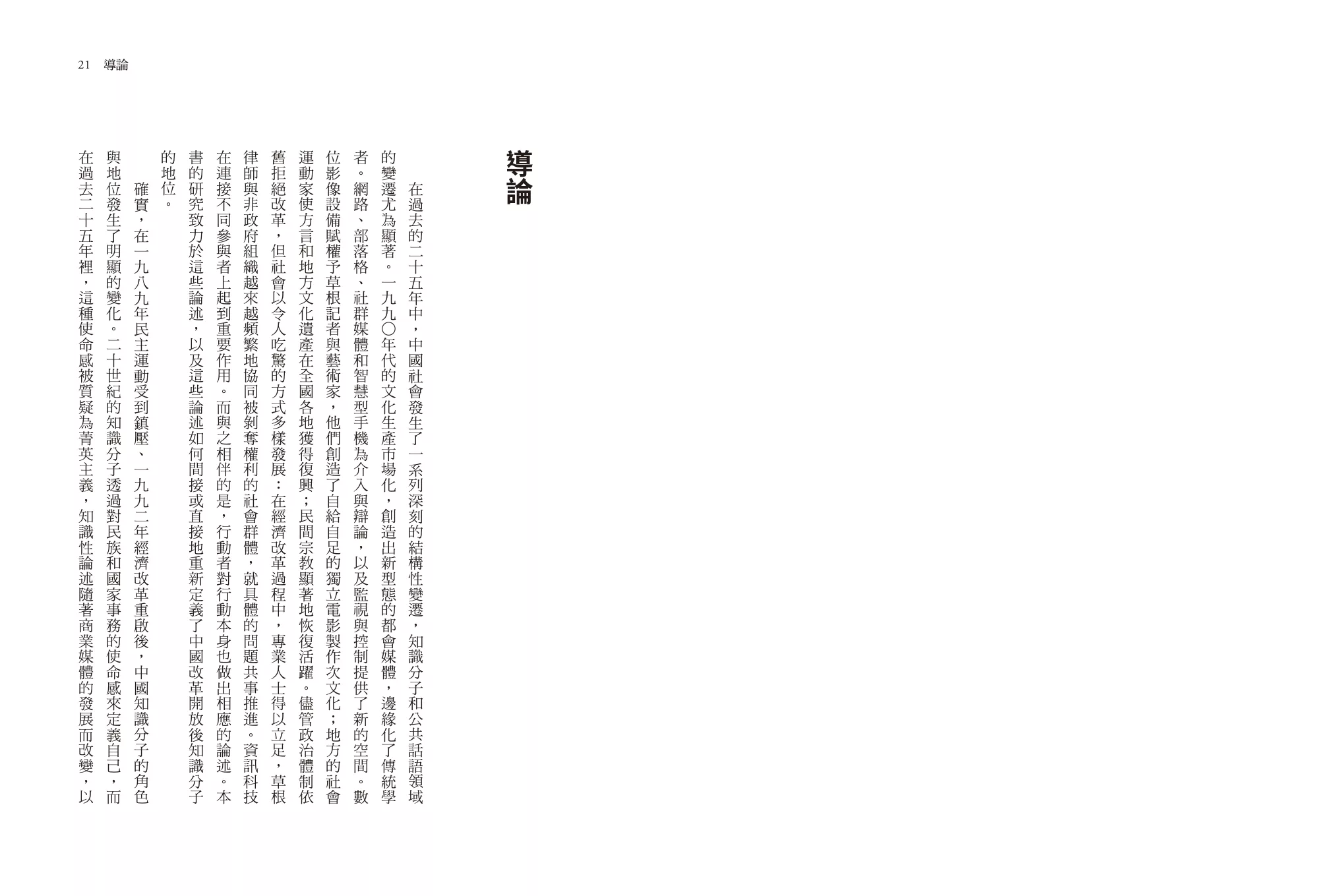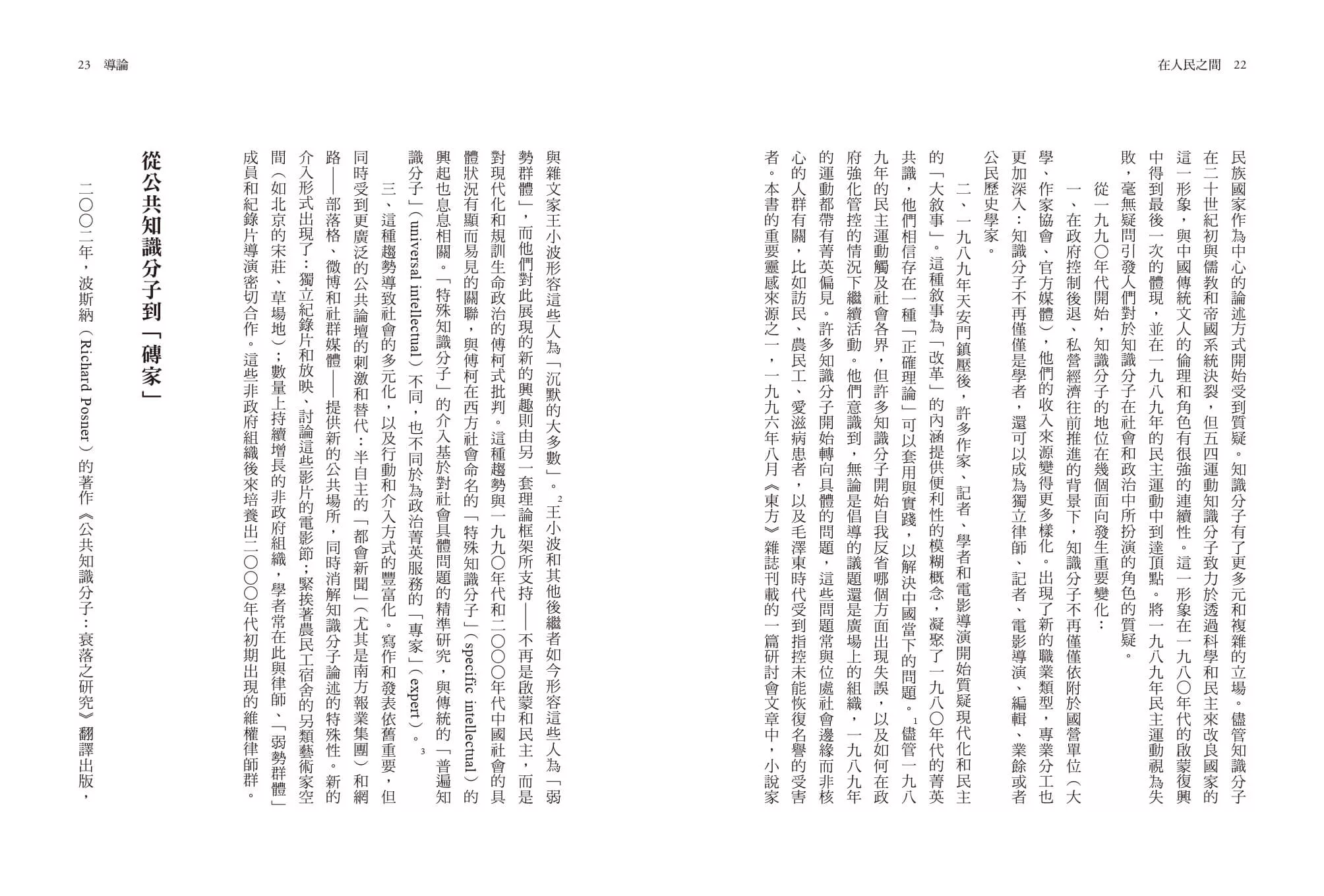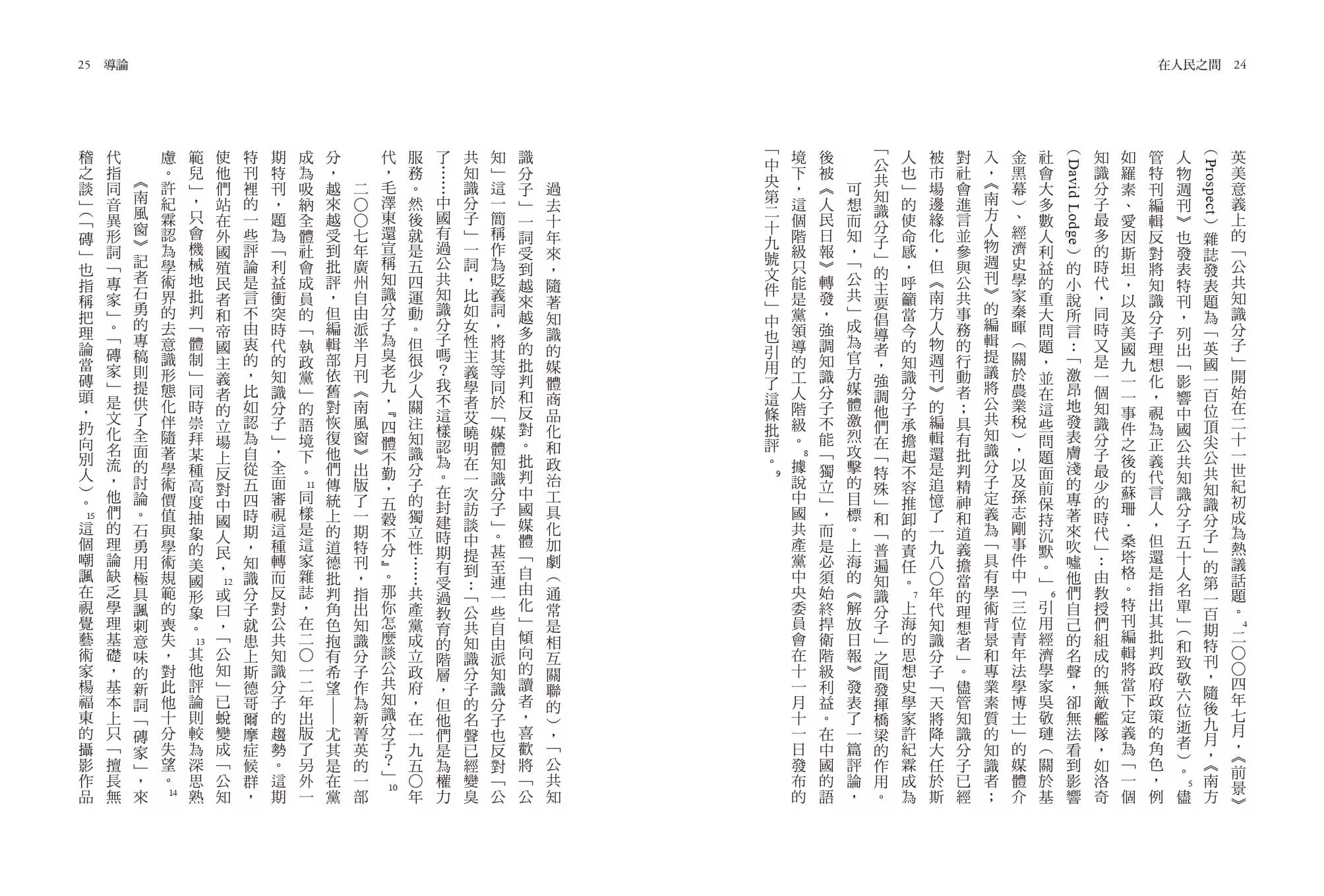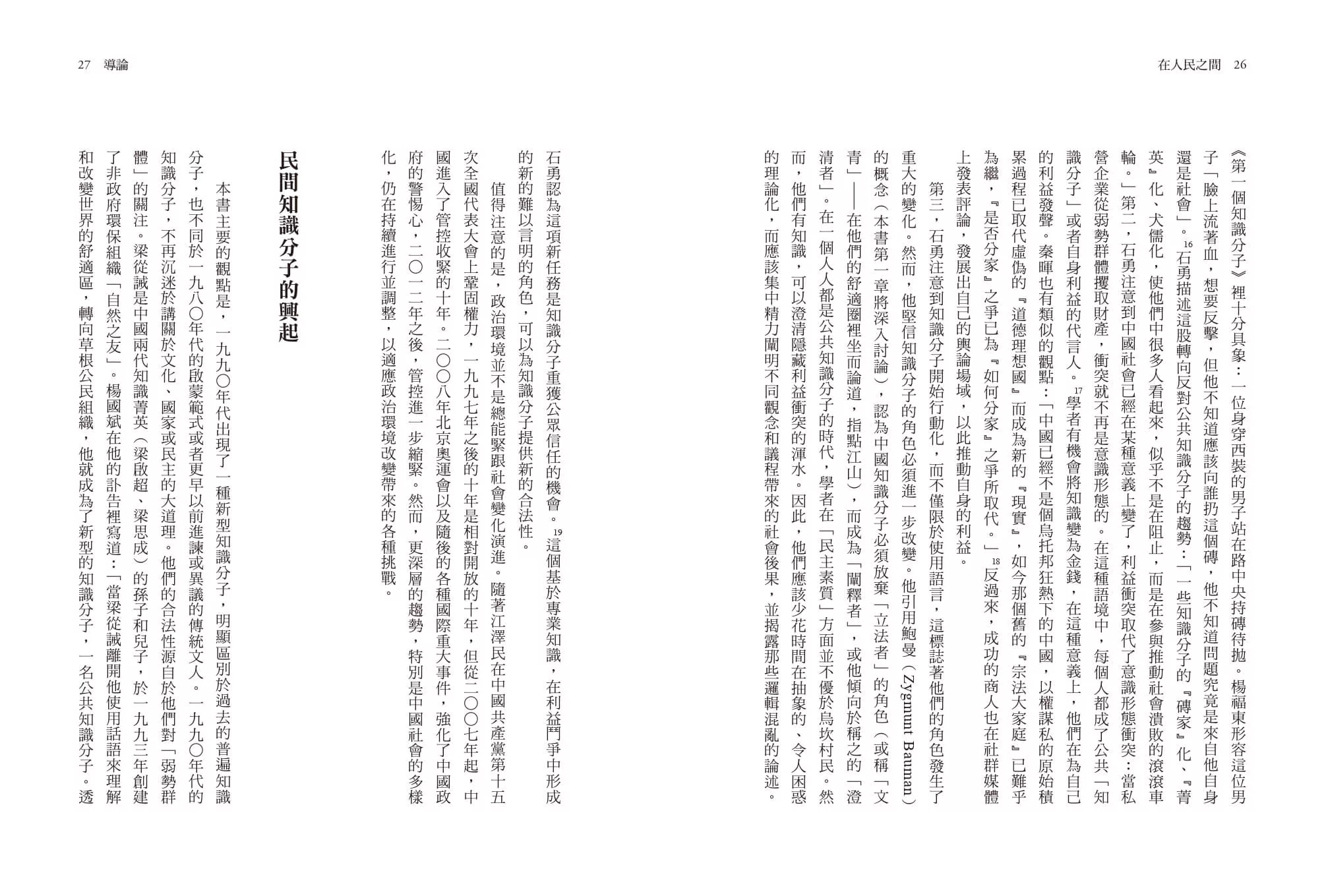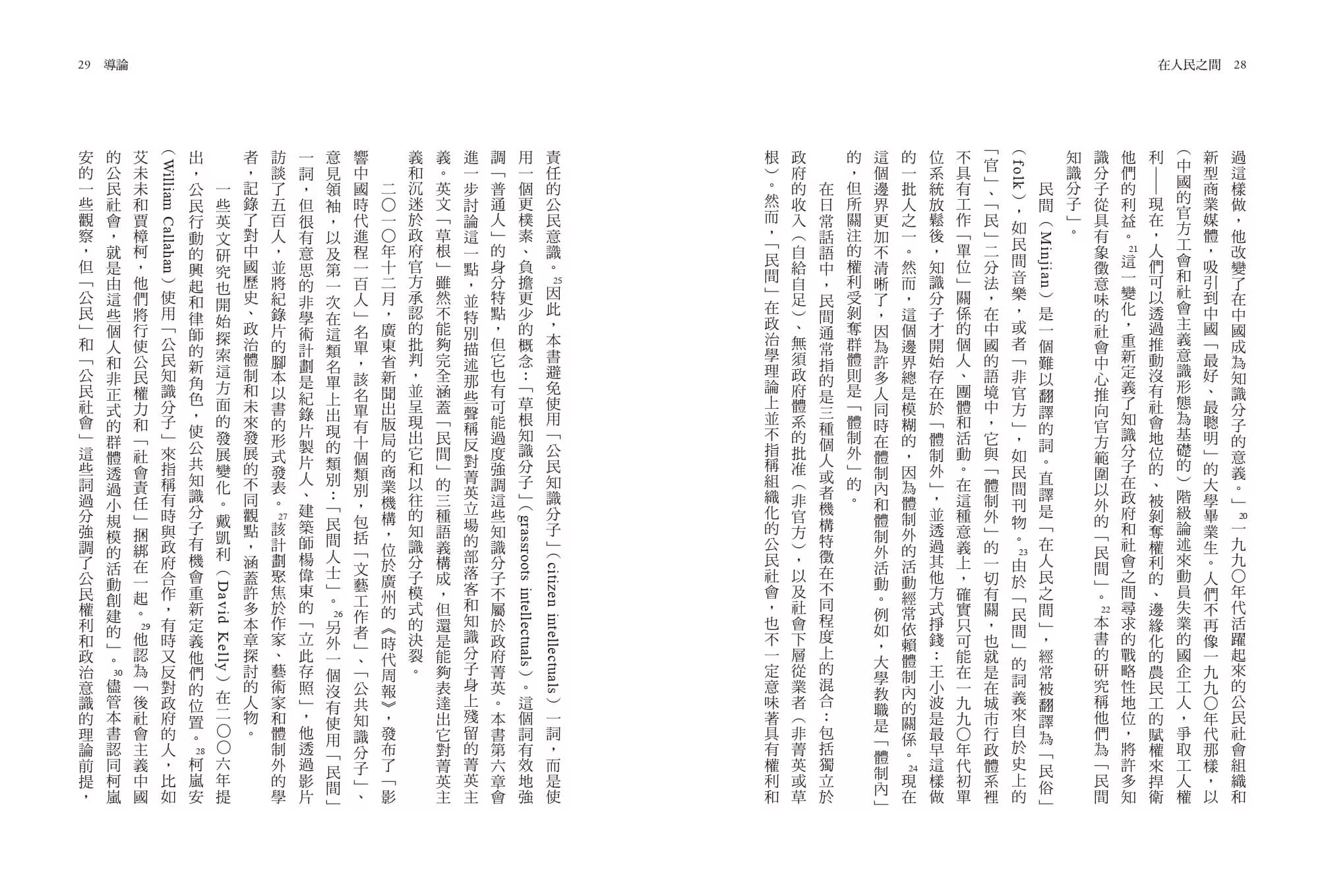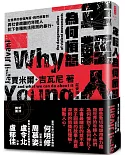推薦序
民間作為抵抗的社會網絡(節錄)
《在人民之間》英文版原名《民間》(Minjian)。這部專書介入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轉型與理論定位的辯論,並且以出色的研究對「草根知識分子」這個主題做出卓越的貢獻。
熟悉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讀者,傾向從國家、市場、社會(或公民社會、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的三分法來定位知識分子。在西方式社會脈絡中,公共知識分子屬於公民社會這個場域。然而,在當下中國語境,所謂公知被揶揄為「磚家」,傳統上通才型啟蒙知識分子的地位也急遽殞沒。那麼,我們如何精準捕捉形形色色的專業人士,包括女權活動家、獨立電影導演、業餘史家、維權律師、NGO工作者、媒體記者、地下刊物編輯、部落客和社會學者,她/他們既不從屬於國家、也不依循市場邏輯或試圖掙脫市場誘惑,從各自實存的特定社會角落,依憑其專長知識,提出對國家和市場的批判,她們具有共通的社會特徵嗎?
針對這個問題意識,魏簡爬梳西方理論傳統中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流變,從專業化與自主性這兩個維度的分析,得出「特殊知識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這個類型,這類人具有專業化的特定知識,但在財務與政治上能夠獨立於國家控制之外。在中國這樣的黨國資本主義(之前是國家社會主義體制),財務自主尤其緊要,因為國家掌握龐大而無所不包的經濟資源,對人民施展廣泛的吸納與懲罰。至於知識分子如何逃脫國家監控,或者,是否能夠真正掙脫政府控制,則是一門從實踐中才能檢證的抵抗藝術。于建嶸似乎是這方面的佼佼者,他在從商致富後獲得「自由」(他說:賺錢是為了自由),投入法學研究得到博士學位,他以「訪民」研究樹立了一種介入模式,並在宋莊藝術村成為農民和創作者。
魏簡從理論檢討中得出特殊知識分子這個理念型之後,回溯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傳統。他以「民間」來總括當代中國各種草根知識分子的抵抗空間。這群「體制外」的人,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大都不再標榜政治正確的宏大敘事,甚或與「中國情結」保持距離。因此,可以想見她們與政權鼓吹的主旋律的距離,也標記與儒家文人學官傳統的割裂。例如,作家王小波在一九九○年代擔任了開路先鋒,對「沉默的大多數」做了深刻的剖析,自己也認同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反對人民為國家做出無意義的犧牲,即使被貼上「民族虛無主義」的標籤亦不畏懼。王小波提示了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思考與生存方式。
筆者認為,本書在理論和方法上皆有創新之處。魏簡在提出民間知識分子這個理念型的過程,重新(或原創地)定義了「民間」這個直觀、簡潔但豐富的概念:民間是存在於政權邊緣或遊走體制內外的社會網絡,這個網絡由偶發事件與眾多發聲者交織而成,這些發聲者在認同上貼近、或等同於事件當事人的底層社會位置,基於特定知識或個人知識而發聲或採取行動。⋯⋯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定格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草根轉身
「知識分子」這個概念,自「八九學運」以鎮壓收場後便在中國逐漸衰微。及至現在,「公共知識分子」或者其縮略語「公知」,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網路話語中幾乎成了罵人的詞彙,指高高在上地指點江山以博取粉絲和社會地位的投機者,有時還暗含崇拜西方、給政府添亂的指控,讓人避之唯恐不及。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簡則在本書中提出,九○年代以來,知識分子群體並非在中國匿跡,而是轉換了存在和表達的形式。
魏簡認為,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知識菁英階級,他們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更獨立於體制、更草根,他們不執著於討論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等宏大議題,而是將目光集中於特定社會議題、弱勢群體,用更專業化的討論介入公共話語—魏簡將這種新型知識群體定義為「民間知識分子」。
為了在學術脈絡中定位這一觀點,魏簡比較了布赫迪厄和傅柯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布赫迪厄始終將知識分子理解為菁英階層的一部分,他們利用在專業領域積累的聲望對政治議題發聲。而傅柯則更重視知識分子的專業見解,將「特殊知識分子」定義為基於其專業造詣參與到特定議題的公共討論中的人,這種對具體事務的討論也使得他們更貼近大眾。魏簡認為,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無疑是傅柯式」。
魏簡隨後透過五個分主題的研究,描繪「傅柯式」的中國知識分子。首先,魏簡詳細解讀了王小波的雜文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和倡議。王小波被九○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知識群體奉為圭臬,他對傳統文人的泛道德化和家國情懷的諷刺,及對自由和理性的推崇,都極大地影響和反應了九○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轉向。
如果說對王小波的文本解讀是為全書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描繪定下基調的話,魏簡在其後四章對中國民間史家、獨立導演、草根專業人士和民間言論群體的詳細記述,則是為中國的新型知識群體勾勒出了極為具體的面貌:他們在體制的打壓和收編的夾縫中求生;他們關注「中國崛起」的宏大敘事下隱匿的真相,無論是反右和大饑荒受難者的口述史,還是農民工、訪民等弱勢群體的社會境遇;他們構建一個個帶有烏托邦意味的、獨立又聯結的社群,一度形成了一張平行於主流的社會網絡—至少在習近平對民間社會的打壓全面來臨以前。⋯⋯
趙思樂/前中國時政記者、現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博士生
中文版序(節錄)
習近平執政後,中國社會的政治極化無疑更加嚴重。對意識形態的重新強調和由宣傳部門鼓動的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話語,激發社會中的一批高調群體,他們特別積極地傳播黨國的觀點。意識形態整肅是持續進行的反腐敗運動的核心內容之一,而正因如此,人們越來越難公開發表與黨的路線直接衝突的觀點。許章潤可能還不算是民間知識分子,但他因為發表控訴檄文而被剝奪教學資格和進入公共空間的權利,只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有最低限度的人身自由。二○一八年的修憲更是將黨之於國家的領導地位進一步法律化,使得文化、資訊和媒體領域的幾個重要機構直接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監管。其結果是出現許多好鬥的主權主義者,他們認為西方世界已經衰落,並從納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國家主義觀點中得到啟發。他們鼓吹「入關」:亦如滿洲人奪取儒家意義上的「天下」,中國現在也應該奪取世界體系的控制權,對其進行重組以為自己服務。面對「入關學」的興起,據說一些無力的批判者接受「加速主義」的哲學,認為中共的過度膨脹會加速它更早崩潰。但有一些人則支持「躺平」,盡量迴避國家主導的官方領域和過度競爭的「內捲」式市場。雖然這些人稱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知識生產者」,但他們展現出相對於國家和市場的獨立性,這是民間領域的一個重要特徵。
不論如何,新冠疫情的爆發還是向人們展示了在官方體制外,各式各樣的民間知識仍在生產和傳播。吹哨人如李文亮和艾芬醫生在向公眾披露疫情上發揮重要作用,而一些科學家則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在公共伺服器上與全世界的科學家分享有關SARS-CoV-2基因序列的敏感資訊。以艾曉明為代表的民間知識分子、以方方為代表的知名作家以及許許多多普通公民,在封城期間不顧難以預測的官方審查,透過網路日誌發表並交流想法。甚至在中央政府官員來到武漢宣布「戰勝」病毒並進行「感恩教育」時,也有公民在自家窗前進行公開抗議。李文亮的微博帳號成為一座非正式的墓碑和藍儂牆,國家容忍網路用戶在此有限度地公開表達批判性觀點。
十年前,吳介民提出「第三種中國想像」,旨在突破傳統的機會與威脅二分法,直接觸及中國的公民社會。由於疫情和更早之前的趨勢,中國無論在實體或思想上對於外面的世界都越來越封閉。然而中國的社會和思想領域遠不像受到嚴格管控的公開記錄中所描述的那般鐵板一塊,而是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二○二一年七月十四日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