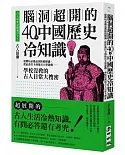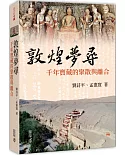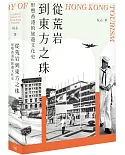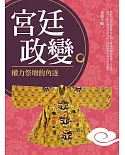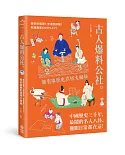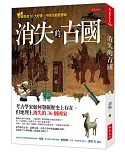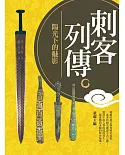引言
「第二軸心文明」的當代追索
100年前亦即1919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五四運動,其震天價響的口號,唯有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可以救中國,此一片面理解西方啟蒙運動的狂熱,其結果帶給中國吸取西方文化的迷思。杜維明教授在反思啟蒙的論述中指出,中西社會在「後啟蒙運動」中都偏離了方向,走向「工具理性」所發展出來的一種「宰製性的科學主義」;以及從極端的個人主義所導致的一種帶有侵略性的經濟人的觀念的出現。這些都遠離了那時蘇格蘭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與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等人注重處理道德情操的「復性」(renaissance)問題。簡言之,對源于西歐的啟蒙運動,從近代中國的歷史經驗審視,其教訓是不應走上「全盤西化」的移植,也不應盲目的批判,而應是一種「批判式的繼承」進而到「創造性的轉化」,才能得到較全面的理解與應用上的超越。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在1953年出版英文版的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歷史的起源與目的》,他將歷史文明發展分為四期:(1)史前時代—語言之產生,工具之發明以及火之點燃和應用。(2)古代文明時期—主要是文字的產生、運用與文明的累積。約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河流域,稍晚在中國黃河流域,產生了古代的文明。(3)軸心文明時期—公元前500年左右為中心,分別在猶太、希臘、埃及、中國、印度等地出現突破性的文明觀念。雅斯培「軸心時代」恰恰與《莊子.天下》所謂「道術將為天下裂」、韋伯有關世界宗教的「先知時代」,聞一多(1899-1946)〈文學的歷史動向〉有關四大文明「同時猛抬頭,邁開大步」等說法比雅氏的論說要早六年。他倆開啟了人類的「第一軸心文明」的論據。(4)科技文明時期—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具有深刻影響的事件,並且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影響,開啟了人類近代科學技術的時代。他認為中國、印度、猶太、希臘文明不約而同的在500年間都有一批先知突破古文明階段,進到了第一「軸心的時代」(Axial
Age),此時代「超越」(transcendent)的文明,對於宇宙和人生的體認及思維,都躍上、提升了一個新的層次,超越之前的文明,從出現後到現在都沒有間歇,沒有死亡或停止,就好像「車輪當中的軸心」一樣,至今仍然成為這些國度人民生活價值與行動的核心。
雅斯培提出「軸心文明」的論述影響深遠,至今仍在中西文明對比與會通上具有指標性的巨著,他反省何以兩次世界大戰都發生在啟蒙運動發生的地區,也就是當今的西歐文明何以導致競爭、衝突乃至戰爭不斷的深層思考?原因可能就在西歐單元軸心的主導與思維。雅斯培審視多元歷史與哲學的傳統,他將哲學的功用分以下6個方面:
其一是歷史編年學的角度(historisch-chronologischer Aspekt)。
其二是實質性的角度(sachlicher Aspekt)。
其三是個人的角度(persönlicher Aspekt)。
其四是文化積澱的角度(genetischer Aspekt)。
其五是實用的角度(pragmatischer Aspekt)。
其六是動力學的角度(dynamischer Aspekt)
從這些角度的分析,筆者認為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重視哲學內在理路的發展,同時也重視哲學思想的外在社會脈絡與功用,他重視軸心文明是一文化積澱的結果,以及至今仍然具有實用的價值以及對後啟蒙人類社會仍能產生互補的動力學原理等實質性功效之所在。
在西方學術界關於雅斯培軸心文明的討論與文獻太多,但重要的討論會與論文集有三:
(1) Schwartz, B . I.等人所發起的第一次大型討論,並於1975年由美國人文學會的機關刊物“Daedalus”發表。
(2) 1986年Eisenstadt, S. N.等人所發起的第二次大型討論與出版。
(3) 2001年由Arnason, J. P., Eisenstadt, &Florence ,B. W.等人再發起第三次大型討論,並於2005年出書。
上述三次的討論都以Jaspers的論述為中心,邀請對仍深具價值與作用的幾個不同古代文明有專精研究的學者分別從倫理學、宗教學、哲學、文化及社會科學的領域,對其軸心文明及其超越展開跨文明的論說與比較。他們普遍認為科學主義、科學革命時期,其文明雖突破了宗教的束縛,科學主義雖帶動後來的科技發展,發生了工業革命,以致推動西方現代化,但在雅斯培看起來科技文明仍為一間歇性的文明,非為人類文化世界的最高價值,未來人類文明的突破需要幾個軸心文明的對話與再創造,以進入「第二個軸心」。也就是說不以啟蒙運動為唯一的文明指標,第二軸心文明必須以第一軸心文明彼此間相互對話、吸收的精神彼此學習與包容。馮友蘭的學生在美國任教的趙復三教授指出:「把現代化與西方化等同起來只能是殖民統治殘餘思想的產物,而不是真正科學的社會理論。世界現代化進程是世界多元化發展的進程。而不是單一化的進程。中國的現代化不僅需要發展生產力,而且需要一個「發展的文化」(A
Culture of Development)。應用在本文第二軸心的觀念,也就是文明不應該獨尊,依循文明動力的發展型態也不是單一類型的,彼此間應該是相互借鏡,無論是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儒家文明都需要經過一個「新的發展式文化」的相互學習與尊重,並不斷因時、因地而有所調整與創造。
誠如當代中國學者湯一介所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例如,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把目光投向其他文化的源頭古希臘,而使歐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輝,「中國的宋明理學(新儒學)在印度佛教衝擊後,再次回歸孔孟而把中國哲學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當今世界多種文化的發展正是對2000多年前的軸心時代的一次新的飛越。據此,我們也許可以說,將有一個新的第二「軸心文明」出現,21世紀世界文化發展很可能形成若干重要的文化區:歐美文化區、東亞文化區、南亞文化區和中東與北非文化區(伊斯蘭文化區),以及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猶太文化等」。1992在西安與湯教授開會後,其言論一向是筆者所關注。西方學者中也不乏跳出西方中心論來看「現代性」問題者,鐵倫洋凱(E.
A. Tiryakian)就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全球的軸心轉移的時刻,現代性的「中心」正在發生變異,即它正從「北美」向「東亞」移轉。東亞經濟超過半個世紀的蓬勃發展,其共同點之一就在於此地區儒家文明普遍被尊重與傳承,它的義理絕然不同於西方啟蒙運動、或者是基督新教倫理地區的發展經驗。
在中西文明與兩岸政治交涉與會通的過程中,本書的重點包括四個部分,首先從傳統軸心文明,特別是儒家、道家文明如何與當代的思想與問題展開對話,從而突顯傳統中國優質軸心文明的永恆價值。第二部份在於探討20世紀以降中、日、台的民族認同與文化流變的省思,特別是兩岸的民族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戰爭物語」與當代跨國的災害關懷交錯搓揉,從而突顯「和的文化」在中、日、台東亞地區的重要性。第三部分則在探討兩岸政治體制
100多年來的轉型經驗,特別是中西文化如何影響憲政主義的落實?政治體制如何形朔兩岸關係?再以若干案例來探究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最後則藉由超越意識概念比較中西文化,從後冷戰時代的東亞文化抉擇,香港中文大學全球在地化的經營模式,東南亞陳嘉庚、楊忠禮如何以儒家倫理實踐其企業與奉獻精神,再以因戰爭的印記而漂流到台灣的「社區發展」權威學者徐震教授以及在美國著名的漢學家余英時的史學成就,來印證一代學人超越、會通古今與中西成就出「新文化發展」的第二軸心文明典範。本書大部份篇幅曾經在過去20年相關的研討會或者是學報中發表,以系統性的觀念集結成書,在體例上依當時的寫作規範而呈現,內容上做了若干補充,格式上保持原來體例,不做太多的調整,一併說明,敬請多予批評指教,不勝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