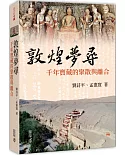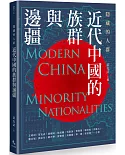《樸園文存》編前言
關於朱樸(省齋)的文章,我在幾十年前就在《古今》雜誌讀過,但並沒有想過要編他的文集,而後來又接觸到他在香港出版的《省齋讀畫記》、《書畫隨筆》、《海外所見名畫錄》、《畫人畫事》、《藝苑談往》五本專談書畫的書籍。這五本書早就是絕版書,市面買不到,我記得多年前北京張大千研究專家包立民先生來台北,還請我幫他複印,由於他臨時要,好像只找到四本複印而已,也無法全套齊全。
二○一六年一月份,我將五十七期的《古今》雜誌,重新復刻,精裝成五大冊上市,極獲好評,這是對朱樸前半生在文史雜誌的貢獻之肯定。今年(二○二一)我將他後半生對書畫鑑賞的五本著作重新打字校對編排,甚至想辦法把原書黑白的畫作恢復彩色的,希望對他晚年著作的流傳有些助益。在編完這些書後,我突然想到他早年的文章則付諸闕如,也從沒有結集過。那對於他早年的人生歷程及思想似乎無法一窺究竟。因此才萌生有編此《樸園文存》的構想,雖然北京我的朋友謝其章兄曾編過《樸園日記》,但只收十九篇文章,就其文集而言明顯是不足的。於是我花了一段時間,光去中央研究院的圖書館就先後兩次,「上窮碧落」地找了能找到的舊雜誌,還利用上海圖書館製作的「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去尋找,分別從《新人》、《東方雜誌》、《中央導報》、《申報月刊》、《中華月報》、《宇宙風(十日刊)》、《宇宙風(乙刊)》、《大風旬刊》、《興亞月報》、《中央月報》、《太平洋周報》、《古今》、《天地》、《藝文雜誌》、《雜誌》等找出他早期的文章;至於他晚年定居香港時期,主要的文章發表在《熱風》、《大華》、《大人》等雜誌上。
朱樸曾在〈樸園隨譚之二:記筆墨生涯〉一文中,談到他曾經寫過一兩篇關於經濟的文章,於《時事新報》刊出,但目前沒找到。香港中文大學的劉沁樂同學幫我找到一九二○年出版的《新人》第一卷第五期的〈六種雜誌的批評〉可算是相當早的文章,當年他只有十八歲,尚在中國公學讀書。這是對當時銷路最廣最具影響力的六種雜誌:《新青年》、《建設》、《新潮》、《新群》、《解放與改造》、《新中國》提出批評。而在他進入《東方雜誌》編輯部之後,我找到了一九二二年的〈社會制度論〉,一九二三年的〈評合作運動〉兩文均發表在《東方雜誌》,他離開雜誌社之後,他說他幾乎沒寫過任何文章,直到他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刊登於《東方雜誌》的〈國際合作論〉,那是他去歐洲考察所寫的,這和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他給汪精衛的信談〈自治期間合作運動之重要性〉是前後呼應的。
朱樸與汪精衛相識極早,應該在一九二十八年秋冬之際,當時汪精衛在巴黎,朱樸去歐洲考察,因林柏生之介而認識。但認識周佛海相對比較晚,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樸在上海創辦了《古今》雜誌,第一期有〈記周佛海先生〉一文,署名「左筆」,文中開頭說:「在舊曆新年久陰乍晴的一天,記者承本刊朱社長的介紹,特往拜謁大名鼎鼎的『和平運動總參謀長』周佛海先生。」由此觀之,朱社長(朱樸)與記者「左筆」應該是兩個人,幾十年來也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包括我自己。朱樸在〈《古今》一年〉文中也說:「去年今日《古今》創刊號出版,孤軍突起,一鳴驚人……,有一個刊物想魚目混珠,竟冒用我『朱樸』的名字及《古今》中另一作者『左筆』的名字寫些無聊的文章。」朱樸再次強調「左筆」是另一作者,莫非「此地無銀三百兩」,但卻沒有任何證據來證明兩者「同屬一人」?而直到晚近我看到梁鴻志給他女兒梁文若的遺書(此遺書寫於一九四六年,直到一九七○年金雄白才發表於香港《大人》雜誌)中提及「吾鄉薄產,損耗已盡……字畫尚有數件,將來擇兩件以畀左筆」,此時朱樸早已和梁文若結婚了,因知「左筆」正是指梁鴻志的女婿朱樸。而若沒見過這份遺書的人,焉能得知此署名?由於「左筆」的署名,我陸續在一九四三年的《太平洋周報》找到〈陳彬龢論〉、〈陶希聖論〉、〈張善琨論〉、〈邵式軍論〉等四篇文章。這些人物在當時都是赫赫有名的,朱樸要月旦他們或許有些顧忌,因此在此特殊場合才用「左筆」的化名。
《古今》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創刊,一九四四年十月停刊,在這兩年多的時光中是朱樸寫作最豐收的時期,他寫了不少文章都發表於自己的刊物中,有系列長文〈樸園隨譚〉共十篇,除〈引言〉外,有〈記筆墨生涯〉、〈談命運〉、〈懷北京〉、〈記雁蕩山〉、〈憶錢海岳〉、〈《蠹魚篇》序〉、〈海外遊屐夢憶錄〉、〈小病日記〉、〈《往矣集》日譯本序〉。他也談到他用「樸園」名字的由來是一九四○年四月一五日,他從上海某名收藏家處購得文徵明巨幅真跡一件,得意之餘,就在卷面上書「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樸園主人購於上海」十九個字,這是他自稱「樸園主人」之始。這其中〈懷北京〉包括他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七日發表於《申報》的〈遊頤和園記〉,而〈記雁蕩山〉則包括一九三六年七月發表在《中華月報》的〈遊雁蕩山記〉,新文中引錄舊文,新瓶舊酒,我也姑且放在此系列。除此有關《古今》創辦的經過,有〈發刊詞〉、〈漫談《古今》〉、〈編輯後記:介紹周黎庵〉、〈滿城風雨談《古今》〉、〈《古今》一年〉、〈《古今》兩年〉、〈小休辭〉,這幾篇文章我把它放在一起,從這組文章中,你將可以看到《古今》的開場與收場。
一九四三年十月蘇青創辦《天地》,由於蘇青曾在《古今》發表文章,朱樸是欠了蘇青的人情,可能拗不過蘇青的邀稿,於是在《天地》創刊號寫有〈梅景書屋觀畫記〉一文。蘇青的邀稿是很難推辭的,朱樸的夫人梁文若就說過,蘇青索稿是急如星火的。她在《天地》第五期以一九三五年秋寫於東京的〈減字木蘭花〉詞云:
瀟瀟夜雨,不管離人愁幾許。好夢難成,斷續風聲斷續更。
此情誰慰,往事煙塵空灑淚。費盡思量,縱使相逢也斷腸。
應命後,第六期又交出〈談《天地》〉一文,她說:「在目前上海所出版的各種文藝刊物中,我不避嫌的說,水準最高的要算《古今》了吧。其次,《天地》無疑的要站到第二席了。這兩個刊物的名字我想再好也沒有了,一個代表『時間』,一個代表『空間』,真可謂包羅萬象,無所不涵。記得杜少陵(甫)曾有詩句曰:『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以贈《天地》與《古今》,真是天造地設,妙古絕今,可謂巧合之至。《古今》上的文字大多是比較嚴肅的,《天地》上的文字大多是比較輕鬆的,各有所長,無分軒輊。」在讚美《天地》之餘,總不忘推銷自己丈夫的《古今》。
在《古今》第五十四期朱樸發表他的〈樸園日記〉第一篇〈甲申銷夏鱗爪錄〉,之後沒想到《古今》在第五十七期就停刊了,於是〈樸園日記〉第二篇〈重陽雨絲風片〉就移到北京的《藝文雜誌》刊登,《藝文雜誌》是一九四三年七月由周作人領銜的「藝文社」創刊於北京,偽新民印書館印行,主要作者除周作人外,還有俞平伯、錢稻孫、龍榆生等學界人士以及其他文壇人士。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終刊,共出版了二十三期。朱樸這篇文章登在一九四五年第三卷第三期,也就是終刊號上。也因此〈樸園日記〉第三篇〈北上征塵記〉又移到上海的《雜誌》刊登於一九四五年第十四卷第五期。而他在寫這篇文章時正是他要去北京之時,據日記所言,他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抵達北京的。而緊接著〈故都墨緣錄〉是他到北京後一個多月寫的,刊登於《雜誌》一九四五年第十四卷第六期。
朱樸在〈人生幾何〉文中說:「我由北京來港是一九四七年,並非一九四八年。」而此後寫文章則用「朱省齋」(偶而同期有兩文才兼用朱樸或樸園)之名。此時的文章大量刊登於香港《熱風》雜誌上,《熱風》是曹聚仁、徐訏和李輝英等,在香港創辦的創墾出版社所出的文史半月刊,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創刊,至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六日停刊,共九十九期。朱省齋從第二十三期寫起,幾乎每一期都有文章發表,有時同期還會有兩篇文章。香港中文大學的劉沁樂同學幫我查到朱省齋發表文章在《熱風》的期數是:二十三、二十六、三○、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六十一、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八○、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七、九十八等期。這些文章大半以上都是談書畫鑑賞的,而且很多都收入他的《書畫隨筆》、《藝苑隨筆》兩本著作中,但還有二十二篇不屬於書畫鑑賞的,沒有收入,我就把它收入此書中。附帶說明的是在臺灣《熱風》雜誌,除中央研究院圖書館有收藏二十五到四十八期外,所有圖書館無一收藏,我也曾經一度想放棄再查找,因為疫情期間我也無法去香港圖書館,又不敢麻煩香港的朋友。無計可施之餘,我把這訊息放在臉書,沒想到我的朋友「百城堂」主人林漢章兄,說他有八十幾本,可以借我,於是除了〈多難只成雙鬢改:知堂老人贈聯記〉一文(由香港劉沁樂同學去圖書館影印外),全部都找齊了。真是天助我也,也感謝漢章兄和臉友沁樂同學的大力協助。
〈多難只成雙鬢改:知堂老人贈聯記〉這篇文章有個故事,也顯見他和周作人交情之深。文中說:「甲申(一九四四)之冬,余北遊燕都,除夕,知堂老人邀讌苦茶庵,陪座者僅張東蓀、王古魯。席間,余出紙索書,主人酒餘揮毫,為集陸放翁句『多難只成雙鬢改,浮名不作一錢看』十四字相貽,感慨遙深,實獲我心。聯旁並附小跋曰:『樸園先生屬書小聯,余未曾學書,平日寫字東倒西歪,俗語所謂如蟹爬者是也。此只可塗抹村塾敗壁,豈能寫在朱絲欄上耶?惟重違雅意,集吾鄉放翁句勉寫此十四字,殊不成樣子,樸園先生幸無見笑也。民國甲申除夕周作人。』虛懷若谷,讀之愧然。」後來朱樸將該聯製版刊登於《逸文》雜誌。「不料製版之後,經手者竟謂原聯已失去,無法覓回;我為此事,耿耿於心,無時或釋。」直到一九五六年冬曹聚仁在北京見到周作人,回到香港告知朱省齋,知堂老人關心他的近況,朱省齋「因即馳函道念,並附告以失聯經過。」兩星期後,回信來了,周作人再書原聯給他,並另附小跋。這聯及跋語就製版刊登於《熱風》雜誌第九○期封面上。
而〈憶知堂老人〉寫於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文中開頭說:「消息傳來,知堂老人已於去年十一月在北京謝世了。」文中再次引用〈多難只成雙鬢改〉一文,並歷數他在一九五七、一九六○、一九六三與周作人見面。當時正是「文革」初始,紅火朝天,消息阻隔,因此會有「海外東坡之謠」。朱省齋寫這篇悼文時,知堂老人還活著,只是被紅衛兵批鬥中,直到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他才嚥下最後一口氣,享年八十二歲,應了他自己說「壽則多辱」的話。
沈葦窗在〈朱省齋傷心超覽樓〉文中說:「我草創《大人》雜誌,省齋每期為我寫稿,更提供許多書畫資料。」《大人》創刊於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創刊號就刊登朱省齋的〈賞心樂事話當年〉(該篇原題為〈人生幾何〉)。與他在汪偽時期即有若金蘭之誼的金雄白在〈倚病榻,悼亡友〉文中說:「說來似乎是迷信,當《大人》雜誌創刊之前,葦窗兄拉他寫稿,第一篇他寫的是以往半生中的若干賞心樂事,而安上的題目竟然是〈人生幾何〉,發表時偏為他改易了,他還為此而有些不懌,且一再為我言之。他對『人生幾何』這一句成語,不知何以偏好得會有些流於固執,終於他為另一雜誌寫了另一篇〈人生幾何〉,出版以後,又欣然指給我看。言為心聲,現在想來,也許省齋那時的心理上,早有此不祥之感了。」〈人生幾何〉後來刊登於一九七○年九月一日出刊的《大華》復刊號第一卷第三期。這篇文章也是因為有人傳言「朱樸已歸道山」,於是朋友曹聚仁、高伯雨紛紛寫文章辯駁,然而辯駁文章也有些錯訛,於是朱省齋特別寫此一長文,最後他說:「對於生死這個問題,一切宜聽其順乎自然,泰然處之,千萬不要看得太重。曹孟德說得最曠達:『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而這篇文章發表後三個多月,朱省齋遽歸道山,因此金雄白說:「也許省齋那時的心理上,早有此不祥之感了。」
朱省齋晚年曾經患過嚴重的心臟病,金雄白在〈倚病榻,悼亡友〉文中言及朱省齋最後的日子:「大約是一九七○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是我與他最後的一面了,我們又在常去的咖啡室中會面,他看見我病骨支離的樣子,殷殷囑咐我還要加以調養。我想到他已是六十有九歲,我說:「明年是你的七十大慶了,以你早幾年的病況而能霍然全癒,更值得祝賀了。』他竟然說:「真是人生幾何!明歲的賤降,擬約少數的親友,歡聚一天。』又那裡料到,這一天就永遠不會來到了。他逝世那一天(案:十二月九日),晨起還偕同夫人同出早餐,回家以後,坐在客室中的沙發椅上,忽然覺得胸口有異常的痛悶,神色又轉而大異,他夫人知道情況嚴重,立即延醫診治,迨醫生來到,早已返魂無術。那時我又患著肝炎症,在病榻上看到了報上的噩耗,使我無限震悼,相別還不及一月,而從此人天永隔,使我也更有了『人生幾何』之慨!」
《大華》在復刊號一卷七期刊出〈大鶴山人瀟湘水雲圖〉是朱省齋生前就交雜誌主編高伯雨的,而在他過世後的近一個月才刊出,可說是朱省齋最後的絕筆之作了。
拉雜寫來已經五千餘字了,希望這篇〈編前言〉能對整本書的理解有所幫助。這些文章來自不同的雜誌報刊,大概是依照時間順序編列,有些則是自成一組而稍做調整,其目的是要讀者明白他思想或興趣的轉變,或記其旅遊賞畫之過程。
蔡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