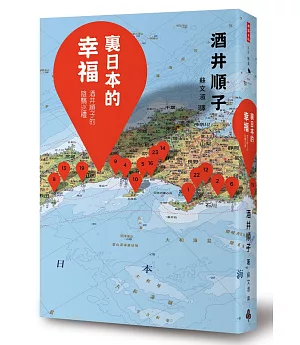無所匱乏、欲求又多的時候,人很容易會看不見某些事情,
但有些歡喜,真的要待在『背後』才懂得。
社會文化觀察家 酒井順子
繼《敗犬的遠吠》、《無子人生》後
沉澱人生重新體會裏日本的美好
日本揜藏著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佳美之地─裏日本
保留現今表日本所沒有的文化魅力
人生裡會有悲傷、會有想要靜一點的時刻,在這種時刻,裏日本正是我們最完美的去處。裏日本能夠容受我們心境上的這種幽微變化,它具有這種特質。
不是那種太熱情、太積極的,而是淡然包圍你整個人的那種溫柔。
名人推薦
新井一二三、野島剛、張維中
誠摯推薦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酒井順子 Sakai Jyunko
1966年生於東京都。
高中時期於雜誌《Olive》上連載專欄。
立教大學社會學部觀光學系畢業後,任職廣告公司,而後專事寫作。
2004年以《敗犬的遠吠》獲頒講談社散文獎與婦人公論文藝獎。
著作閎多,中譯著作已有《都與京》、《緩緩前行,女子鐵道》、《人到中年,更是理直氣壯》、《無子人生》等多部作品。
譯者簡介
蘇文淑
建築系畢,現居京都河畔,譯字為生。
[email protected]
酒井順子 Sakai Jyunko
1966年生於東京都。
高中時期於雜誌《Olive》上連載專欄。
立教大學社會學部觀光學系畢業後,任職廣告公司,而後專事寫作。
2004年以《敗犬的遠吠》獲頒講談社散文獎與婦人公論文藝獎。
著作閎多,中譯著作已有《都與京》、《緩緩前行,女子鐵道》、《人到中年,更是理直氣壯》、《無子人生》等多部作品。
譯者簡介
蘇文淑
建築系畢,現居京都河畔,譯字為生。
[email protected]
目錄
前言 「裏」性的魅惑
陰翳 浮現在幽暗中的金澤金箔與能登漆
民藝 鳥取與新潟的名企劃人
佛教 淨土真宗與一向一揆
神道 「裏」大社、「表」神宮
美人I 日本海美人隔縣說
美人II 最強美女傳──越後與出雲
流刑 被流黜的浪漫──佐渡與隱岐
盆踊 藏起面容的蠱惑
文學I 「表」男與「裏」女的故事──《雪國》
文學II 泉鏡花與金澤
文學III 水上勉的不幸之為用
田中角榮 新潟人氣王的日本改造
鐵道I 北前船、在地線、北陸新幹線
鐵道II 陽到陰,陰至陽
幸福 家家戶戶「日本最幸福的縣」
核電 水上勉之憂「文明過剩」
金澤 映亮暗空的繽紛
觀光 因有暗影,才有光
後記
陰翳 浮現在幽暗中的金澤金箔與能登漆
民藝 鳥取與新潟的名企劃人
佛教 淨土真宗與一向一揆
神道 「裏」大社、「表」神宮
美人I 日本海美人隔縣說
美人II 最強美女傳──越後與出雲
流刑 被流黜的浪漫──佐渡與隱岐
盆踊 藏起面容的蠱惑
文學I 「表」男與「裏」女的故事──《雪國》
文學II 泉鏡花與金澤
文學III 水上勉的不幸之為用
田中角榮 新潟人氣王的日本改造
鐵道I 北前船、在地線、北陸新幹線
鐵道II 陽到陰,陰至陽
幸福 家家戶戶「日本最幸福的縣」
核電 水上勉之憂「文明過剩」
金澤 映亮暗空的繽紛
觀光 因有暗影,才有光
後記
序
推薦序
作為「後山」的日本海
新井一二三
有一次在台北,我向一位朋友提到:
「工作完了就要坐火車去宜蘭了。」
他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於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宜蘭是我老家!你知道嗎?每次從台北坐火車,經過多座隧道,終於在左邊看到大海時候的感覺,簡直像川端康成小說《雪國》的第一句: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
當時我覺得怪裡怪氣,因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寫的是積雪的日本海岸,人家的故鄉倒是陽光燦爛的台灣東岸。然而,很多年後看著這本《日本海的幸福》,我忽而發覺:其實,他的感覺非常準確;日本海在多數國人的印象中,的確是跟台灣東岸一樣的「後山」。
本書的日文原名叫《裏邊多幸福(裏が、幸せ。)》,只是在中文裡和日文裡,「裏」字所指的意思不完全一樣。日文的「裏邊」相當於中文的「後邊」或者「背面」。所以,「裏街」是「後巷」,「裏書」是「背書」,「裏金」是「小金庫」,「裏社會」是「黑社會」。怪不得,曾被叫做「裏日本」的日本海沿邊地區居民提出了抗議,結果,如今在日本的主流媒體上看不到「裏日本」一詞了。但是,把太平洋沿邊看成「表日本」,把日本海沿邊看成「裏日本」的感性,仍然保留在多數日本人的心目中。所以,即使用婉言說「裏邊」,大多日本人還馬上曉得是日本海邊的意思了。
台灣東岸被稱為「後山」,是歷來漢人移民建設的城市如台南、彰化、萬華等等都在面對台灣海峽的西岸所致吧。相比之下,東岸面向的是無邊無際的太平洋;雖然在語言文化方面跟台灣原住民有很多共同點的南島語諸族住在大海那邊,但是由漢人角度來看,無非是化外之海。日本海的情形有點不一樣。畢竟,古代從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傳到東瀛的先進文化,無例外地渡過日本海而來的。全日本兩大神社之一出雲大社就位於日本海邊。直到公元十九世紀的江戶時代末期,從商城大阪經瀨戶內海、關門海峽,沿著日本海岸一直航行到北海道的「北前船」曾是非常重要的貿易徑路。具有歧視味道的「裏日本」一詞普及,則是促使日本近代化的美國船隻出現在太平洋岸,使得橫濱、神戶等開放港口設在太平洋岸,這回先進的工商業文化設施以及鐵路等等,都領先在太平洋岸建設所致。
本書作者是以《敗犬遠叫》走紅的酒井順子。她在東京出生長大,就讀了聖公會開設的立教女學院,從高中時候開始就在商業雜誌上寫專欄,至今做了三十多年的職業作家。她的優勢是一方面精通東京的女性流行文化,另一方面則一貫保持局外人的視點。她的文筆往往散發出男性御宅的味道來,卻對日本女性的生活細節永遠額外熟悉。
曾經在日本,對鐵路感興趣的主要是男性,鐵路書寫也被松本清張、西村京太郎等男性推理小說家壟斷。公然表明喜愛鐵路旅行的女作家,酒井順子大概就是第一人。她為自己塑造的角色是女校裏的T,喜歡專門做傳統上屬於男性的活動,包括一個人的鐵路旅行。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日本很多旅館都不接待單獨女客的,怕是失戀了想不開,搞不好晚上要上吊了事。後來,職業女性增加,為出差或休假,一個人出來的女性就多起來了,旅館業方面也捨不得錯過女客生意了。儘管如此,單獨旅客在日本始終是例外;不分男女,多數人還是選擇跟異性或同性朋友一起旅行,選擇單獨活動的,若是男性就被視為御宅,若是女性則被視為敗犬。好在今天日本的御宅/敗犬一族有了口齒清楚的代言人:酒井順子。她為他們選擇的旅遊目的地,就是少有人走的「裏日本」,該說順理成章了。
原來,她在立教大學讀的是觀光學,怪不得對各景點的市場潛力很有辨識力。加上,她對日本文學的造詣又深。在這本書裡,她就通過川端康成《雪國》,水上勉《風的盆戀歌》等以「裏日本」為背景的小說來探討外地以及本地出身的日本人對「裏日本」有什麼樣的看法。最後,她也指出來,日本的政治領袖中,「裏日本」出身的政治家占的比率非常低,才一成左右。其中最著名的新瀉縣人田中角榮不僅來自「裏日本」,而且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恨不得拉高故鄉「裏日本」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於是策劃的北陸新幹線近年終於開通,教「表日本」居民去日本海邊比原先容易多了。果然,酒井順子的這本書跟北陸新幹線都於二〇一五年幾乎同時問世。
這些年,台灣人對東岸的印象變得正面多了。說到花蓮、台東,很多人都想到藍色的天空似地發呆一會兒,然後嘆著口氣說「好美」,感覺挺像本書標題中的「幸福」。相比之下,日本人對「裏邊」的心中距離還相當遠,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冬天下大雪吧?」而那有貶意。結果,本書介紹的很多景點,都還沒有太多日本遊客去的。所以,台灣讀者看完之後,趕緊去走走,保證能看到沒被過度商業化的旅遊景點。不亦樂乎?
前言
「裏」性的魅惑
至今我還清清楚楚記得第一次搭乘山陰本線時的驚愕,因為山陰「本」線嘛,沿路上應該會經過一些熱鬧的區域才對,沒想到一路上出乎我意料之外全是單軌,窗外望出去也渾然鄉下景色,甚至已經完全不只是「鄉下」了。只見日本海無比澄澈、青山無比碧翠,而夾雜在青山與碧海間一小塊平地上的房舍風格統一,一路上可以說絕景綿延,我那時候想,原來日本也有這種風景?
還有我第一次搭機降落在能登機場時,心底也很感動。能登機場位於本州往外突出的能登半島右側,當時從機艙中望見下方一整片的蒼綠,感覺自己好像是一隻正要悄然降落到那片林中的侯鳥。
有一次我因為取材關係,走在丹後跟若狹的小小半島上,那一路上也是絕景不斷。如果那種美景是在東京近郊,肯定會看得到一大堆觀光設施,但在那裡連一個也沒有。我就只是在寂靜包圍著的路上信步徜徉在一個又一個的美景之中。
仔細想想,這些令我驚豔的地方幾乎都位於日本海這一邊。從小我在東京出生長大,由於交通不便,難得跑到日本海這邊一趟,但只要來,一定看得到許多安靜綻放著光彩的地方。以前我誤以為只要有美景的地方,就一定看得到眺望台、咖啡店跟土產店,但來到日本海這頭,才發現絕美的景色就只是存在那裡而已,旁邊什麼也沒有,叫人怎麼能不驚訝呢?
這些美好的地方,都是以前被稱為「裏日本」的地區。所謂「裏日本」,是相對於太平洋這一側的「表日本」而言,由於「裏」字這種說法讓有些人不開心,現在已經很少人用了。
可是我覺得,日本海那一頭的許多觸動人心的美景之所以能保留至今,難道不是因為它們位於「裏側」嗎?仔細想想,「裏日本」這個詞其實散發出了一種難以言喻的誘惑力,尤其當對著萬人大開門戶的「表側」早已被人摸個透徹,冠了個「裏」字的地方如今反而讓人覺得好像有點什麼,譬如「裏原宿」是這樣,「裏磐梯」也是這樣。我不禁覺得,所謂的「裏」就是揜藏著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佳美之地。
「裏日本」這個概念,在近代之前似乎不存在於日本。《裏日本》(古廄忠夫著,岩波新書)與《裏日本如何形成》(阿部恆久著,日本經濟評論社)這兩本書中,對於「裏日本」有詳盡描述。在近代之前,日本海側其實是很繁華的區域,海上有北前船來來往往,陸上有加賀百萬石榮極一時,在宗教上,更是被稱為淨土真宗的「王國」所在,農業也極其興盛。這個與京都、大阪等大都市相連的日本海區域,無論在物質或精神文化面向上都很昌榮。
情況是到了明治維新後才開始轉變,當時日本正全力發展工業化,先是交通上從海運時代進入了鐵路時代,鋪設鐵道主要以東京、名古屋跟大阪等大都市為主,亦即先連結起後來被稱為「太平洋工業帶」的路線,先不管日本海這頭。我們看一下明治三十九年的鐵道地圖,很明顯可以看到鐵軌幾乎全鋪設在太平洋這一側,至於日本海這頭,只有從新潟到直江津、富山到福井這幾段而已,可以說幾乎等於一片空白。相對於早早鋪設的山陽線,山陰線幾乎「晚了二十年」。
軍事設施、官立高等教育機關也主要設置在太平洋這一頭,可以說,資本主義在日本一步步形成的過程中,也逐漸形塑出了「裏日本」這個概念。
這個詞開始廣受使用,似乎是到了明治二十年左右。一開始,大家只是把它當成一個表現地理位置的字眼,但來到了明治三十年代,它開始隱喻了存在於表、裏日本之間的經濟與社會階層差異。
對於明治時代還沒有任何殖民地的日本而言,「與太平洋工業帶之間夾著脊梁山脈的裏日本,被當成了絕佳的後山地帶,於是人力、物資與金流的移轉體系,就這麼在呈現出明顯表裏差異的同時,逐漸形成了。」古廄先生在他的書裡這麼陳述。從那時候起,農家次男跟三男到太平洋這一側的大都市討生活,連帶地讓物資、金流也跟著積累在太平洋這頭的模式已經逐漸形成。
東日本大地震引發了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大家交相指責東北地方簡直被當成了自己國內的殖民地,但其實早從明治時代起,裏日本就一直扮演著日本國內殖民地的角色,讓資金得以被積聚在太平洋這頭的大都市中。
除了經濟差距外,還有一項是我們容易在去裏日本時感受到其「背後性」的,那就是氣候。冬天時從東京往北,明明東京這邊還在出太陽,過了個隧道,那頭卻完全是個雪國。每每我在冬日搭上從太平洋這邊前往日本海那邊的列車,一定會看到這種對比。
日本的國土細長,在這細長的國土中央坐落著山脈,於是造就了日本海側跟太平洋側明顯的氣候差異,然而表現出這種差異的「裏日本」與「表日本」這兩個詞,卻逐漸受到摒棄。似乎是在一九六○到一九七○年代之間,日本的電視台跟報紙公司覺得這兩個字眼是歧視用語,最好不要使用。
所以現在我們幾乎不會在媒體上看到「裏日本」這個用法。可是自從我在裏日本各地看過了那麼多夢幻美景之後,「裏日本」這三個字,之於我是愈來愈有魅力了──就算只是一個生長在表日本的人一廂情願的想法。
在這種情況下,有一次我有機會入住石川縣和倉溫泉的名旅館「加賀屋」,發現原來加賀屋第三代老闆小田禎彥會長與夫人居然是我以前大學的學長與學姊,而且他們兩個人就是在我念的觀光學科(現在改為學系)的前身觀光講座與旅館研討會上認識的,所以我們有了一些機會交談。
那時候小田會長說了一番話,令我到現在印象都還很深刻。他說,他在思考石川縣的觀光產業今後應該如何發展時:
「裏日本一定會變得愈來愈像表日本,這是沒辦法的事,但以前大家都想變成亮麗熱鬧的觀光區,今後卻不見得要往那個方向發展吧?」
這一番話讓我很意外,但也覺得真是說到了我心坎裡。一直以來,我以為裏日本的人可能不是那麼喜歡「裏日本」這個詞,還有它所影射的含意,沒想到原來有人覺得「裏」反而是一種可以發展的觀光特質,這麼說的,還是個像會長這樣的商界要人。
後來我又有機會去加賀屋請教小田會長夫婦關於「裏日本」的一些問題。加賀屋是間很大的旅館,我抵達時,除了大女將之外,連一幫女服務生也全出來門口迎接我,很親切。以加賀屋這麼巨型規模的傳統旅館來說,能到今天還維持著迥異於西式飯店的氣息,我相信一定是因為那裡的從業人員全都貫徹了「以客為尊」的精神。
「說到什麼是觀光,就是《易經》裡所謂的『觀國之光』,也就是『去看一國之光』。什麼是『光』呢?不見得一定要是燦爛眩眼的,而是那個土地上的特有文化或者我們去其他地方看不到、嚐不到的一些事物,那就是那個地方的『光』。我們從這個角度來想,北陸地區有什麼呢?我們北陸有的就是雪多、雨多,人家說『忘了帶便當也別忘了帶傘』,真的就是這樣。可是這種濕度與這種陰翳,也有些人喜歡哪!
有些觀光區是像夏威夷、拉斯維加斯那樣亮晃晃、熱熱鬧鬧地,但不是所有人都想要那些。我們人生裡會有悲傷、會有想要靜一點的時刻,在這種時刻,裏日本不正是我們最完美的去處嗎?裏日本能夠容受我們心境上的這種幽微變化,它具有這種特質。」
小田會長一開始就這麼講。
的確,我在日本海這頭旅行時常覺得大家都好親切,不是那種太熱情、太積極的,而是淡然包圍你整個人的那種溫柔。
「我們有句老話說:『能登連泥土都親切』。」
會長說古時候聽說有個武士跑來能登的山裡測量,載滿了測量儀器的馬匹在山坡上拐了腳,當地馬伕居然先衝著馬兒問:「還好嗎?沒關係嗎?」這種連對牲畜都關懷的親切之情讓武士很感動,於是有感而發講了這一句「能登連泥土都親切」。
「以客為尊的精神,我想也是從這種人文風土裡培養出來的吧。」
接著他又說:
「我覺得裏日本很可能會是『慢一圈的領先者』。我們跟表日本比起來,當然是開發得慢了一點,但也因此得以保留現今的表日本所沒有的魅力,大自然跟人文風俗都沒被破壞得太嚴重。二○一五年,通往金澤的北陸新幹線開通後,我想來來往往的人一定大量爆增,但我們到時候也不能忘了我們在『背後』特有的魅力。要是全日本到處都變成同一個模子打造出來的,不是很無聊嗎?我們這兒啊,冬天很漫長,天地一片灰白,要耙掉屋頂的雪、要做這做那,真的讓人很崩潰,但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忽然有一天,太陽嘩──地露臉了,大家心想春天終於來了!這種日子裡,我們北陸人心底那種歡欣喜悅大概是表日本的人絕對無法理解的(嘻嘻)。無所匱乏、欲求又多的時候,人很容易會看不見某些事情,但有些歡喜,真的要待在『背後』才懂得。」
另一方面,大女將真弓女士則是從東京遠嫁來能登。
「我那時從金澤過來還要三個多小時,也沒柏油路,一路上昏昏暗暗的,好像松本清張先生筆下《零的焦點》那種感覺。一到冬天就下大雪,三八豪雪(一九六三年)那時候,我真心懷疑自己到底來了什麼地方?」
「她是被我騙來的啦。」
會長說完又呵呵笑。大女將接著說:
「但習慣了以後就覺得這邊空氣好、東西好吃,看得見海又看得見綠意,心情很開闊。就連雪花紛飛或是吹來這兒特有的冷冽寒風時,都覺得別有滋味。說實在的,表面上看不見的地方,其實藏了很多剔透的美好。」
她說完後,會長接道:
「像我這種生意人就會想,要是把現在一些愈來愈不常見的日用品湊在一塊兒,弄間旅館擺些五右衛門浴缸跟蚊帳之類,名字就叫做『裏日本』,一定很有意思。」
我也覺得如果有這種旅館,我也想住。
要說「裏性」這種特質是顯眼或不顯眼的,當然不顯眼,但不顯眼就不能製造出經濟效益嗎?未必。尤其在經歷過東日本大地震後,整個社會上的風氣已然不再是「必須不斷追求發展」,在這樣的時機點上,「裏日本」做為商機的可能性,不也挺可觀嗎?
幸福或發展,不見得一定要光鮮亮麗,幸福也可能有別種樣貌。這一點,裏日本已經證明給我們看了。事實上眾所皆知,北陸三縣鰲居全日本人民幸福滿意度調查的前幾名,可見「背後的幸福」的確存在。
那一天,我也在加賀屋裡著著實實享受了一番能登精神風土中孕育出來的體貼好客。我泡在溫泉中,忍不住疑猜,「這邊的人該不會是想獨享這種背後的幸福,所以才這麼低調吧?」
譬如當我想起表、裏日本之間的差異時,我常會想到長嶋茂雄與野村克也這兩位棒球名人。棒球巨星長嶋茂雄出生於千葉縣,大學時代加入了東京六大學棒球聯盟大展身手後,長期活躍於巨人隊,最後晉升為教練。野村克野則出生在面朝日本海的京都府網野町(現京都丹後市),高中畢業後,以零簽約金練習生的不起眼身分進了南海鷹隊,後來成為太平洋聯盟的強打好手,最後以名教練的身分遊走於各大球團。
這兩位棒球明星的強烈對比非常有名,野村就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說:「如果長嶋跟王貞治是向日葵,我就像是不聲不響悶著開的月見草。」我覺得他這句話說得很漂亮、也說得夠堅毅。他把自己放在與向日葵截然不同的位置上,反而突出了自我的存在。
讓我們再進一步想想,我們有誰能夠決定向日葵跟月見草誰比較美、誰比較幸福呢?我們當然也無法去比較,罹病後又失去愛妻的長嶋先生,與有堅毅的妻子在背後撐持,一路擔任教練直至七十四歲高齡的野村先生誰比較幸福。
還有,我讀新潟出生的漫畫家柳澤公夫的散文集《人生到底怎麼回事》時,有個段落也讓我看得瞪大眼睛。他說:「其實我私心希望,我們新潟縣就一直當個陰影下的存在就好。」「大家都說我們是裏日本、裏日本,好像我們活得多謹小慎微一樣,其實這裡好吃的東西多得不得了。我們每天都『嘻嘻咿』地偷偷笑著吃好的,像這樣的地方,不反而很棒嗎?」我看到這段落時心想「嚇!這裡也躲了一個喜歡『裏日本』的!」而且果然,他們真的偷偷在那邊「嘻嘻咿」地自己享受美好生活耶!
有一天,我碰到了一位京都的茶人,他說;
「『裏』都是收藏寶物或身分高貴者所在的地方哪。妳看,皇帝在京城裡住的地方,不是就叫做『內裏』嗎?」
沒錯!我聽了恍然大悟。珍貴之物、高貴之人是絕不可能隨隨便便出現在別人面前的,這麼說來,在日本國內負責擔任鄙俗任務的,不反而是表日本了嗎?
悄悄揜藏著珍貴美好的地方──裏日本(我就是故意要在書裡這麼叫它)。它的魅力以及它那屬於內面的「裏性」,接下來就讓我們慢慢來探究。
後記
先前在書中也提過,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首相是田中角榮,再順帶一提,我是出生在經濟高度成長期(譯註:一九五四年底~一九七三年底)的孩子。
我生於一九九六年,出生前兩年,日本剛舉辦完東京奧林匹克,也開通了東海道新幹線。伴隨著公害等成長的傷痛,日本不斷往前發展,國民生產毛額(GNP)也超越了當時的西德,躍居全球第二。一九七○年,舉辦了大阪萬國博覽會,田中角榮憂心只有東京跟東海道路線通過的地區會受到矚目,因此提出了《日本列島改造論》。
高度經濟成長期結束後,迎來了泡沫經濟期,我剛好就是在泡沫經濟時期就業,也就是說,我年輕時的日本一直是往上發展的,景氣非常之好。
往上發展時的社會所追求的是「光鮮亮麗」,我還記得約莫八○年代左右,內向的人會被鄙視為「陰沈」的人,當時整個社會上,無論精神或物質方面要求的都是「光」。
我有這種印象,很可能是因為我出生於經濟高度成長期,要是問一個熟知二次大戰時情況的人,大概會跟你說「才不是咧,日本早從戰敗後就一直想像美國那樣強大了」。再問一個知道更早狀況的人,可能又會說「亂講!日本從明治維新後就一直想變得像歐美那麼強了」。所以如果我們把眼界放大一點來看,或許可以說,在這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時間裡,日本一直在追求物質與精神面向上的「光鮮亮麗」。
不過時代終於也走到了這個地步,最近風向好像開始有了轉變。泡沬經濟破滅後,面臨了景氣低迷、少子化情況無力回天,我們終於知道了,無論經濟或人口都不可能會「永遠攀升」。
如此一個時代裡,日本人──尤其是年輕人──似乎開始覺得「也不需要什麼東西都亮成那樣吧?」特別是在經歷了東日本大地震與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社會上開始重新審視物質上的光明。夜晚的街頭跟屋子裡,需要那麼亮嗎?為了消滅「黑暗」,我們花了多少電?
精神面向上,感覺也不再人人追求陽光。我還記得應該是在八○年代左右,「御宅」這個字開始夯了起來,這個原本是用來尊稱「你家」的字眼,在當時那個還只顧著往陽光狂奔的社會中,成了一個揶揄別人「總是窩在家」的字眼,但顯然泡沫經濟破滅後,我們都赫然發現,原來御宅族的內面性有時候也具有強大的爆發力,「超酷日本」這旋風有一大部分就是由御宅族掀起,而人們也注意到,比起要上不下的亮,暗有時反而更具能量。
我就是在那陣子開始對「裏日本」這個字眼很有感覺,也就是在社會上瀰漫著一股「繼續這樣追求亮麗發展下去,真的好嗎?」的氛圍中。夜晚暗一點、人口不會再繼續成長、錢不會像從前賺得那樣多,這些又有什麼關係呢?當社會上這樣想的人逐漸增多時,「裏日本」這個詞,以及從前被稱為「裏日本」的地區開始散發光芒。
臨接日本海的那一側跟臨接太平洋的這一側相比,經濟規模與人口數都小很多,感覺上好像有點落後。不是下雨就是在下雪,似乎永遠灰白白一片。可是實際上只要去那裡晃過一遍,你就會發現,那兒的人看起來好像都過得還挺不錯的。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為「亮眼」等於「幸福」。幸福的人不總是笑得很開心嗎?但終究也活了這麼些年了,我也了解到,一直笑著的人不見得真的過得那麼好。有多少人相信雜誌上「過得不開心,就要笑得更用力」的說法而勉強自己笑?又因為硬擠出笑容,而把自己擠得不成人形。
而那些看起來不是那麼開心的人,其實也不見得就有多不幸。有些人雖然不太愛笑,但內心世界充實滿足;有些人不太愛講話,但很容易一頭鑽進自己的世界裡,鑽研出一番成果……。
同樣地,有多少住在大都市或表日本地區的人被過度的明亮、過多的資訊與過雜的交談,給搞得筋疲力盡?又有多少住在雲多雪深、看似不繁榮的裏日本地區的人過得幸福而滿足呢?如我這樣一個從小在東京這種不夜城長大的人,也終於恍然大悟,原來亮麗、繁華從來都不見得會跟幸福成正比。
空氣新鮮、風景好、住起來又舒服、人人看起來好像都心滿意足,這樣的地方就存在於裏日本。而這種幸福,正是因為位居「背後」才得以擁有。裏日本的這種充實特質,或許也是我們今後日本所需要的。
我們從地球的角度來看,日本原本就是位於地球的「背面」。就算聚焦於亞洲地區,日本也一直是依附在中國這種先進國家的邊陲上。對於全球來講,東方之巔的島國日本,感覺上大概是一個位於地球背面的「裏地球」「裏世界」吧?
可是我們的祖先一直想「追上歐美、超越歐美」,一路看著前面往上衝,有時候不免走上歧路負了重傷,但咬咬牙,還是撂下去拚搏,所以才有今時今朝,可是為了站上世界的「前方」,我們祖先犧牲了多少、又吃盡多少苦頭?
來到今日,日本人卻心生疑惑,「站在『前方』『光明燦爛』真的很幸福嗎?」當然這種低吟,是站在祖先打落門牙和血吞所打下的基礎上才得以有的餘裕,但享慣了祖先福報的我們,終究也累了,不想再硬撐下去了。
裏日本那樣的幸福,之於此刻的我們,不正是我們所亟需的參考?
我的意思並不是:
「『裏』才是『表』。」
不是的。表裏不見得是上下關係,雖然很多人認為表為優、裏為劣,但我反倒認為表裏是一種橫向關係。只有在背後才看得到的幸福,應該是當前所有的日本人所需要。
換個話題吧。福井人一到冬天好像就會吃水羊羹的樣子。有個福井人告訴我,他一看見水羊羹的廣告,就想:
「啊──,冬天到了。」
水羊羹不像一般羊羹,由於含糖少,只有冬天時能保存得久一點,好像是因為這樣才會習慣在冬天吃。
整個盒子灌得滿滿的水羊羹,表面上已經切開一些縫了。一盒水羊羹的大小,差不多跟一盒都昆布(譯註:一種醋味昆布點心,創始者生於京都,因此以「都」為名,也是漫畫《銀魂》中神樂愛吃的零食)一樣。
「冬天跟家人擠在暖桌裡邊看電視邊吃,每個人都可以連吃好幾塊,真的太好吃了,一盒一下子就沒了。」
我聽見這件事時,真心覺得這大概就是所謂裏日本人的幸福吧?看起來不怎麼樣、吃起來也滋淡味薄的水羊羹,一跟家人一起擠在暖桌裡吃,那滋味之好,跟在表參道熱門的店家前排隊半天才終於吃到的鬆餅,哪有孰優孰劣呢?我也從福井買了些水羊羹回家,邊吃邊想「冬天吃水羊羹實在太讚了啦!」一口就吞掉了一個。
我在這書中,不斷細細探索裏日本的特質、裏日本的幸福,那不張揚而卓美逸群、滋味豐富的幸福中,肯定還有很多是我還沒有發現的,這樣的幸福,自然也會密密沁入早已喘不過氣來的全日本人乾涸的身心中吧。接下來的日子,我想我大概還是會繼續往「裏」跑。
最後,本書得以付梓,實在是託了太多人的好意。包括總是溫暖迎接我、悄悄告訴我許多裏日本點點滴滴幸福的裏日本的朋友、陪我穿梭於裏日本大街小巷的高橋亞彌子女士、小學館的岡靖司先生,當然,還要感謝各位讀者讀到最後,謹在此敬表由衷感激。
二○一五年 初春
酒井順子
作為「後山」的日本海
新井一二三
有一次在台北,我向一位朋友提到:
「工作完了就要坐火車去宜蘭了。」
他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於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宜蘭是我老家!你知道嗎?每次從台北坐火車,經過多座隧道,終於在左邊看到大海時候的感覺,簡直像川端康成小說《雪國》的第一句: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
當時我覺得怪裡怪氣,因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寫的是積雪的日本海岸,人家的故鄉倒是陽光燦爛的台灣東岸。然而,很多年後看著這本《日本海的幸福》,我忽而發覺:其實,他的感覺非常準確;日本海在多數國人的印象中,的確是跟台灣東岸一樣的「後山」。
本書的日文原名叫《裏邊多幸福(裏が、幸せ。)》,只是在中文裡和日文裡,「裏」字所指的意思不完全一樣。日文的「裏邊」相當於中文的「後邊」或者「背面」。所以,「裏街」是「後巷」,「裏書」是「背書」,「裏金」是「小金庫」,「裏社會」是「黑社會」。怪不得,曾被叫做「裏日本」的日本海沿邊地區居民提出了抗議,結果,如今在日本的主流媒體上看不到「裏日本」一詞了。但是,把太平洋沿邊看成「表日本」,把日本海沿邊看成「裏日本」的感性,仍然保留在多數日本人的心目中。所以,即使用婉言說「裏邊」,大多日本人還馬上曉得是日本海邊的意思了。
台灣東岸被稱為「後山」,是歷來漢人移民建設的城市如台南、彰化、萬華等等都在面對台灣海峽的西岸所致吧。相比之下,東岸面向的是無邊無際的太平洋;雖然在語言文化方面跟台灣原住民有很多共同點的南島語諸族住在大海那邊,但是由漢人角度來看,無非是化外之海。日本海的情形有點不一樣。畢竟,古代從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傳到東瀛的先進文化,無例外地渡過日本海而來的。全日本兩大神社之一出雲大社就位於日本海邊。直到公元十九世紀的江戶時代末期,從商城大阪經瀨戶內海、關門海峽,沿著日本海岸一直航行到北海道的「北前船」曾是非常重要的貿易徑路。具有歧視味道的「裏日本」一詞普及,則是促使日本近代化的美國船隻出現在太平洋岸,使得橫濱、神戶等開放港口設在太平洋岸,這回先進的工商業文化設施以及鐵路等等,都領先在太平洋岸建設所致。
本書作者是以《敗犬遠叫》走紅的酒井順子。她在東京出生長大,就讀了聖公會開設的立教女學院,從高中時候開始就在商業雜誌上寫專欄,至今做了三十多年的職業作家。她的優勢是一方面精通東京的女性流行文化,另一方面則一貫保持局外人的視點。她的文筆往往散發出男性御宅的味道來,卻對日本女性的生活細節永遠額外熟悉。
曾經在日本,對鐵路感興趣的主要是男性,鐵路書寫也被松本清張、西村京太郎等男性推理小說家壟斷。公然表明喜愛鐵路旅行的女作家,酒井順子大概就是第一人。她為自己塑造的角色是女校裏的T,喜歡專門做傳統上屬於男性的活動,包括一個人的鐵路旅行。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日本很多旅館都不接待單獨女客的,怕是失戀了想不開,搞不好晚上要上吊了事。後來,職業女性增加,為出差或休假,一個人出來的女性就多起來了,旅館業方面也捨不得錯過女客生意了。儘管如此,單獨旅客在日本始終是例外;不分男女,多數人還是選擇跟異性或同性朋友一起旅行,選擇單獨活動的,若是男性就被視為御宅,若是女性則被視為敗犬。好在今天日本的御宅/敗犬一族有了口齒清楚的代言人:酒井順子。她為他們選擇的旅遊目的地,就是少有人走的「裏日本」,該說順理成章了。
原來,她在立教大學讀的是觀光學,怪不得對各景點的市場潛力很有辨識力。加上,她對日本文學的造詣又深。在這本書裡,她就通過川端康成《雪國》,水上勉《風的盆戀歌》等以「裏日本」為背景的小說來探討外地以及本地出身的日本人對「裏日本」有什麼樣的看法。最後,她也指出來,日本的政治領袖中,「裏日本」出身的政治家占的比率非常低,才一成左右。其中最著名的新瀉縣人田中角榮不僅來自「裏日本」,而且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恨不得拉高故鄉「裏日本」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於是策劃的北陸新幹線近年終於開通,教「表日本」居民去日本海邊比原先容易多了。果然,酒井順子的這本書跟北陸新幹線都於二〇一五年幾乎同時問世。
這些年,台灣人對東岸的印象變得正面多了。說到花蓮、台東,很多人都想到藍色的天空似地發呆一會兒,然後嘆著口氣說「好美」,感覺挺像本書標題中的「幸福」。相比之下,日本人對「裏邊」的心中距離還相當遠,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冬天下大雪吧?」而那有貶意。結果,本書介紹的很多景點,都還沒有太多日本遊客去的。所以,台灣讀者看完之後,趕緊去走走,保證能看到沒被過度商業化的旅遊景點。不亦樂乎?
前言
「裏」性的魅惑
至今我還清清楚楚記得第一次搭乘山陰本線時的驚愕,因為山陰「本」線嘛,沿路上應該會經過一些熱鬧的區域才對,沒想到一路上出乎我意料之外全是單軌,窗外望出去也渾然鄉下景色,甚至已經完全不只是「鄉下」了。只見日本海無比澄澈、青山無比碧翠,而夾雜在青山與碧海間一小塊平地上的房舍風格統一,一路上可以說絕景綿延,我那時候想,原來日本也有這種風景?
還有我第一次搭機降落在能登機場時,心底也很感動。能登機場位於本州往外突出的能登半島右側,當時從機艙中望見下方一整片的蒼綠,感覺自己好像是一隻正要悄然降落到那片林中的侯鳥。
有一次我因為取材關係,走在丹後跟若狹的小小半島上,那一路上也是絕景不斷。如果那種美景是在東京近郊,肯定會看得到一大堆觀光設施,但在那裡連一個也沒有。我就只是在寂靜包圍著的路上信步徜徉在一個又一個的美景之中。
仔細想想,這些令我驚豔的地方幾乎都位於日本海這一邊。從小我在東京出生長大,由於交通不便,難得跑到日本海這邊一趟,但只要來,一定看得到許多安靜綻放著光彩的地方。以前我誤以為只要有美景的地方,就一定看得到眺望台、咖啡店跟土產店,但來到日本海這頭,才發現絕美的景色就只是存在那裡而已,旁邊什麼也沒有,叫人怎麼能不驚訝呢?
這些美好的地方,都是以前被稱為「裏日本」的地區。所謂「裏日本」,是相對於太平洋這一側的「表日本」而言,由於「裏」字這種說法讓有些人不開心,現在已經很少人用了。
可是我覺得,日本海那一頭的許多觸動人心的美景之所以能保留至今,難道不是因為它們位於「裏側」嗎?仔細想想,「裏日本」這個詞其實散發出了一種難以言喻的誘惑力,尤其當對著萬人大開門戶的「表側」早已被人摸個透徹,冠了個「裏」字的地方如今反而讓人覺得好像有點什麼,譬如「裏原宿」是這樣,「裏磐梯」也是這樣。我不禁覺得,所謂的「裏」就是揜藏著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佳美之地。
「裏日本」這個概念,在近代之前似乎不存在於日本。《裏日本》(古廄忠夫著,岩波新書)與《裏日本如何形成》(阿部恆久著,日本經濟評論社)這兩本書中,對於「裏日本」有詳盡描述。在近代之前,日本海側其實是很繁華的區域,海上有北前船來來往往,陸上有加賀百萬石榮極一時,在宗教上,更是被稱為淨土真宗的「王國」所在,農業也極其興盛。這個與京都、大阪等大都市相連的日本海區域,無論在物質或精神文化面向上都很昌榮。
情況是到了明治維新後才開始轉變,當時日本正全力發展工業化,先是交通上從海運時代進入了鐵路時代,鋪設鐵道主要以東京、名古屋跟大阪等大都市為主,亦即先連結起後來被稱為「太平洋工業帶」的路線,先不管日本海這頭。我們看一下明治三十九年的鐵道地圖,很明顯可以看到鐵軌幾乎全鋪設在太平洋這一側,至於日本海這頭,只有從新潟到直江津、富山到福井這幾段而已,可以說幾乎等於一片空白。相對於早早鋪設的山陽線,山陰線幾乎「晚了二十年」。
軍事設施、官立高等教育機關也主要設置在太平洋這一頭,可以說,資本主義在日本一步步形成的過程中,也逐漸形塑出了「裏日本」這個概念。
這個詞開始廣受使用,似乎是到了明治二十年左右。一開始,大家只是把它當成一個表現地理位置的字眼,但來到了明治三十年代,它開始隱喻了存在於表、裏日本之間的經濟與社會階層差異。
對於明治時代還沒有任何殖民地的日本而言,「與太平洋工業帶之間夾著脊梁山脈的裏日本,被當成了絕佳的後山地帶,於是人力、物資與金流的移轉體系,就這麼在呈現出明顯表裏差異的同時,逐漸形成了。」古廄先生在他的書裡這麼陳述。從那時候起,農家次男跟三男到太平洋這一側的大都市討生活,連帶地讓物資、金流也跟著積累在太平洋這頭的模式已經逐漸形成。
東日本大地震引發了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大家交相指責東北地方簡直被當成了自己國內的殖民地,但其實早從明治時代起,裏日本就一直扮演著日本國內殖民地的角色,讓資金得以被積聚在太平洋這頭的大都市中。
除了經濟差距外,還有一項是我們容易在去裏日本時感受到其「背後性」的,那就是氣候。冬天時從東京往北,明明東京這邊還在出太陽,過了個隧道,那頭卻完全是個雪國。每每我在冬日搭上從太平洋這邊前往日本海那邊的列車,一定會看到這種對比。
日本的國土細長,在這細長的國土中央坐落著山脈,於是造就了日本海側跟太平洋側明顯的氣候差異,然而表現出這種差異的「裏日本」與「表日本」這兩個詞,卻逐漸受到摒棄。似乎是在一九六○到一九七○年代之間,日本的電視台跟報紙公司覺得這兩個字眼是歧視用語,最好不要使用。
所以現在我們幾乎不會在媒體上看到「裏日本」這個用法。可是自從我在裏日本各地看過了那麼多夢幻美景之後,「裏日本」這三個字,之於我是愈來愈有魅力了──就算只是一個生長在表日本的人一廂情願的想法。
在這種情況下,有一次我有機會入住石川縣和倉溫泉的名旅館「加賀屋」,發現原來加賀屋第三代老闆小田禎彥會長與夫人居然是我以前大學的學長與學姊,而且他們兩個人就是在我念的觀光學科(現在改為學系)的前身觀光講座與旅館研討會上認識的,所以我們有了一些機會交談。
那時候小田會長說了一番話,令我到現在印象都還很深刻。他說,他在思考石川縣的觀光產業今後應該如何發展時:
「裏日本一定會變得愈來愈像表日本,這是沒辦法的事,但以前大家都想變成亮麗熱鬧的觀光區,今後卻不見得要往那個方向發展吧?」
這一番話讓我很意外,但也覺得真是說到了我心坎裡。一直以來,我以為裏日本的人可能不是那麼喜歡「裏日本」這個詞,還有它所影射的含意,沒想到原來有人覺得「裏」反而是一種可以發展的觀光特質,這麼說的,還是個像會長這樣的商界要人。
後來我又有機會去加賀屋請教小田會長夫婦關於「裏日本」的一些問題。加賀屋是間很大的旅館,我抵達時,除了大女將之外,連一幫女服務生也全出來門口迎接我,很親切。以加賀屋這麼巨型規模的傳統旅館來說,能到今天還維持著迥異於西式飯店的氣息,我相信一定是因為那裡的從業人員全都貫徹了「以客為尊」的精神。
「說到什麼是觀光,就是《易經》裡所謂的『觀國之光』,也就是『去看一國之光』。什麼是『光』呢?不見得一定要是燦爛眩眼的,而是那個土地上的特有文化或者我們去其他地方看不到、嚐不到的一些事物,那就是那個地方的『光』。我們從這個角度來想,北陸地區有什麼呢?我們北陸有的就是雪多、雨多,人家說『忘了帶便當也別忘了帶傘』,真的就是這樣。可是這種濕度與這種陰翳,也有些人喜歡哪!
有些觀光區是像夏威夷、拉斯維加斯那樣亮晃晃、熱熱鬧鬧地,但不是所有人都想要那些。我們人生裡會有悲傷、會有想要靜一點的時刻,在這種時刻,裏日本不正是我們最完美的去處嗎?裏日本能夠容受我們心境上的這種幽微變化,它具有這種特質。」
小田會長一開始就這麼講。
的確,我在日本海這頭旅行時常覺得大家都好親切,不是那種太熱情、太積極的,而是淡然包圍你整個人的那種溫柔。
「我們有句老話說:『能登連泥土都親切』。」
會長說古時候聽說有個武士跑來能登的山裡測量,載滿了測量儀器的馬匹在山坡上拐了腳,當地馬伕居然先衝著馬兒問:「還好嗎?沒關係嗎?」這種連對牲畜都關懷的親切之情讓武士很感動,於是有感而發講了這一句「能登連泥土都親切」。
「以客為尊的精神,我想也是從這種人文風土裡培養出來的吧。」
接著他又說:
「我覺得裏日本很可能會是『慢一圈的領先者』。我們跟表日本比起來,當然是開發得慢了一點,但也因此得以保留現今的表日本所沒有的魅力,大自然跟人文風俗都沒被破壞得太嚴重。二○一五年,通往金澤的北陸新幹線開通後,我想來來往往的人一定大量爆增,但我們到時候也不能忘了我們在『背後』特有的魅力。要是全日本到處都變成同一個模子打造出來的,不是很無聊嗎?我們這兒啊,冬天很漫長,天地一片灰白,要耙掉屋頂的雪、要做這做那,真的讓人很崩潰,但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忽然有一天,太陽嘩──地露臉了,大家心想春天終於來了!這種日子裡,我們北陸人心底那種歡欣喜悅大概是表日本的人絕對無法理解的(嘻嘻)。無所匱乏、欲求又多的時候,人很容易會看不見某些事情,但有些歡喜,真的要待在『背後』才懂得。」
另一方面,大女將真弓女士則是從東京遠嫁來能登。
「我那時從金澤過來還要三個多小時,也沒柏油路,一路上昏昏暗暗的,好像松本清張先生筆下《零的焦點》那種感覺。一到冬天就下大雪,三八豪雪(一九六三年)那時候,我真心懷疑自己到底來了什麼地方?」
「她是被我騙來的啦。」
會長說完又呵呵笑。大女將接著說:
「但習慣了以後就覺得這邊空氣好、東西好吃,看得見海又看得見綠意,心情很開闊。就連雪花紛飛或是吹來這兒特有的冷冽寒風時,都覺得別有滋味。說實在的,表面上看不見的地方,其實藏了很多剔透的美好。」
她說完後,會長接道:
「像我這種生意人就會想,要是把現在一些愈來愈不常見的日用品湊在一塊兒,弄間旅館擺些五右衛門浴缸跟蚊帳之類,名字就叫做『裏日本』,一定很有意思。」
我也覺得如果有這種旅館,我也想住。
要說「裏性」這種特質是顯眼或不顯眼的,當然不顯眼,但不顯眼就不能製造出經濟效益嗎?未必。尤其在經歷過東日本大地震後,整個社會上的風氣已然不再是「必須不斷追求發展」,在這樣的時機點上,「裏日本」做為商機的可能性,不也挺可觀嗎?
幸福或發展,不見得一定要光鮮亮麗,幸福也可能有別種樣貌。這一點,裏日本已經證明給我們看了。事實上眾所皆知,北陸三縣鰲居全日本人民幸福滿意度調查的前幾名,可見「背後的幸福」的確存在。
那一天,我也在加賀屋裡著著實實享受了一番能登精神風土中孕育出來的體貼好客。我泡在溫泉中,忍不住疑猜,「這邊的人該不會是想獨享這種背後的幸福,所以才這麼低調吧?」
譬如當我想起表、裏日本之間的差異時,我常會想到長嶋茂雄與野村克也這兩位棒球名人。棒球巨星長嶋茂雄出生於千葉縣,大學時代加入了東京六大學棒球聯盟大展身手後,長期活躍於巨人隊,最後晉升為教練。野村克野則出生在面朝日本海的京都府網野町(現京都丹後市),高中畢業後,以零簽約金練習生的不起眼身分進了南海鷹隊,後來成為太平洋聯盟的強打好手,最後以名教練的身分遊走於各大球團。
這兩位棒球明星的強烈對比非常有名,野村就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說:「如果長嶋跟王貞治是向日葵,我就像是不聲不響悶著開的月見草。」我覺得他這句話說得很漂亮、也說得夠堅毅。他把自己放在與向日葵截然不同的位置上,反而突出了自我的存在。
讓我們再進一步想想,我們有誰能夠決定向日葵跟月見草誰比較美、誰比較幸福呢?我們當然也無法去比較,罹病後又失去愛妻的長嶋先生,與有堅毅的妻子在背後撐持,一路擔任教練直至七十四歲高齡的野村先生誰比較幸福。
還有,我讀新潟出生的漫畫家柳澤公夫的散文集《人生到底怎麼回事》時,有個段落也讓我看得瞪大眼睛。他說:「其實我私心希望,我們新潟縣就一直當個陰影下的存在就好。」「大家都說我們是裏日本、裏日本,好像我們活得多謹小慎微一樣,其實這裡好吃的東西多得不得了。我們每天都『嘻嘻咿』地偷偷笑著吃好的,像這樣的地方,不反而很棒嗎?」我看到這段落時心想「嚇!這裡也躲了一個喜歡『裏日本』的!」而且果然,他們真的偷偷在那邊「嘻嘻咿」地自己享受美好生活耶!
有一天,我碰到了一位京都的茶人,他說;
「『裏』都是收藏寶物或身分高貴者所在的地方哪。妳看,皇帝在京城裡住的地方,不是就叫做『內裏』嗎?」
沒錯!我聽了恍然大悟。珍貴之物、高貴之人是絕不可能隨隨便便出現在別人面前的,這麼說來,在日本國內負責擔任鄙俗任務的,不反而是表日本了嗎?
悄悄揜藏著珍貴美好的地方──裏日本(我就是故意要在書裡這麼叫它)。它的魅力以及它那屬於內面的「裏性」,接下來就讓我們慢慢來探究。
後記
先前在書中也提過,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首相是田中角榮,再順帶一提,我是出生在經濟高度成長期(譯註:一九五四年底~一九七三年底)的孩子。
我生於一九九六年,出生前兩年,日本剛舉辦完東京奧林匹克,也開通了東海道新幹線。伴隨著公害等成長的傷痛,日本不斷往前發展,國民生產毛額(GNP)也超越了當時的西德,躍居全球第二。一九七○年,舉辦了大阪萬國博覽會,田中角榮憂心只有東京跟東海道路線通過的地區會受到矚目,因此提出了《日本列島改造論》。
高度經濟成長期結束後,迎來了泡沫經濟期,我剛好就是在泡沫經濟時期就業,也就是說,我年輕時的日本一直是往上發展的,景氣非常之好。
往上發展時的社會所追求的是「光鮮亮麗」,我還記得約莫八○年代左右,內向的人會被鄙視為「陰沈」的人,當時整個社會上,無論精神或物質方面要求的都是「光」。
我有這種印象,很可能是因為我出生於經濟高度成長期,要是問一個熟知二次大戰時情況的人,大概會跟你說「才不是咧,日本早從戰敗後就一直想像美國那樣強大了」。再問一個知道更早狀況的人,可能又會說「亂講!日本從明治維新後就一直想變得像歐美那麼強了」。所以如果我們把眼界放大一點來看,或許可以說,在這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時間裡,日本一直在追求物質與精神面向上的「光鮮亮麗」。
不過時代終於也走到了這個地步,最近風向好像開始有了轉變。泡沬經濟破滅後,面臨了景氣低迷、少子化情況無力回天,我們終於知道了,無論經濟或人口都不可能會「永遠攀升」。
如此一個時代裡,日本人──尤其是年輕人──似乎開始覺得「也不需要什麼東西都亮成那樣吧?」特別是在經歷了東日本大地震與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社會上開始重新審視物質上的光明。夜晚的街頭跟屋子裡,需要那麼亮嗎?為了消滅「黑暗」,我們花了多少電?
精神面向上,感覺也不再人人追求陽光。我還記得應該是在八○年代左右,「御宅」這個字開始夯了起來,這個原本是用來尊稱「你家」的字眼,在當時那個還只顧著往陽光狂奔的社會中,成了一個揶揄別人「總是窩在家」的字眼,但顯然泡沫經濟破滅後,我們都赫然發現,原來御宅族的內面性有時候也具有強大的爆發力,「超酷日本」這旋風有一大部分就是由御宅族掀起,而人們也注意到,比起要上不下的亮,暗有時反而更具能量。
我就是在那陣子開始對「裏日本」這個字眼很有感覺,也就是在社會上瀰漫著一股「繼續這樣追求亮麗發展下去,真的好嗎?」的氛圍中。夜晚暗一點、人口不會再繼續成長、錢不會像從前賺得那樣多,這些又有什麼關係呢?當社會上這樣想的人逐漸增多時,「裏日本」這個詞,以及從前被稱為「裏日本」的地區開始散發光芒。
臨接日本海的那一側跟臨接太平洋的這一側相比,經濟規模與人口數都小很多,感覺上好像有點落後。不是下雨就是在下雪,似乎永遠灰白白一片。可是實際上只要去那裡晃過一遍,你就會發現,那兒的人看起來好像都過得還挺不錯的。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為「亮眼」等於「幸福」。幸福的人不總是笑得很開心嗎?但終究也活了這麼些年了,我也了解到,一直笑著的人不見得真的過得那麼好。有多少人相信雜誌上「過得不開心,就要笑得更用力」的說法而勉強自己笑?又因為硬擠出笑容,而把自己擠得不成人形。
而那些看起來不是那麼開心的人,其實也不見得就有多不幸。有些人雖然不太愛笑,但內心世界充實滿足;有些人不太愛講話,但很容易一頭鑽進自己的世界裡,鑽研出一番成果……。
同樣地,有多少住在大都市或表日本地區的人被過度的明亮、過多的資訊與過雜的交談,給搞得筋疲力盡?又有多少住在雲多雪深、看似不繁榮的裏日本地區的人過得幸福而滿足呢?如我這樣一個從小在東京這種不夜城長大的人,也終於恍然大悟,原來亮麗、繁華從來都不見得會跟幸福成正比。
空氣新鮮、風景好、住起來又舒服、人人看起來好像都心滿意足,這樣的地方就存在於裏日本。而這種幸福,正是因為位居「背後」才得以擁有。裏日本的這種充實特質,或許也是我們今後日本所需要的。
我們從地球的角度來看,日本原本就是位於地球的「背面」。就算聚焦於亞洲地區,日本也一直是依附在中國這種先進國家的邊陲上。對於全球來講,東方之巔的島國日本,感覺上大概是一個位於地球背面的「裏地球」「裏世界」吧?
可是我們的祖先一直想「追上歐美、超越歐美」,一路看著前面往上衝,有時候不免走上歧路負了重傷,但咬咬牙,還是撂下去拚搏,所以才有今時今朝,可是為了站上世界的「前方」,我們祖先犧牲了多少、又吃盡多少苦頭?
來到今日,日本人卻心生疑惑,「站在『前方』『光明燦爛』真的很幸福嗎?」當然這種低吟,是站在祖先打落門牙和血吞所打下的基礎上才得以有的餘裕,但享慣了祖先福報的我們,終究也累了,不想再硬撐下去了。
裏日本那樣的幸福,之於此刻的我們,不正是我們所亟需的參考?
我的意思並不是:
「『裏』才是『表』。」
不是的。表裏不見得是上下關係,雖然很多人認為表為優、裏為劣,但我反倒認為表裏是一種橫向關係。只有在背後才看得到的幸福,應該是當前所有的日本人所需要。
換個話題吧。福井人一到冬天好像就會吃水羊羹的樣子。有個福井人告訴我,他一看見水羊羹的廣告,就想:
「啊──,冬天到了。」
水羊羹不像一般羊羹,由於含糖少,只有冬天時能保存得久一點,好像是因為這樣才會習慣在冬天吃。
整個盒子灌得滿滿的水羊羹,表面上已經切開一些縫了。一盒水羊羹的大小,差不多跟一盒都昆布(譯註:一種醋味昆布點心,創始者生於京都,因此以「都」為名,也是漫畫《銀魂》中神樂愛吃的零食)一樣。
「冬天跟家人擠在暖桌裡邊看電視邊吃,每個人都可以連吃好幾塊,真的太好吃了,一盒一下子就沒了。」
我聽見這件事時,真心覺得這大概就是所謂裏日本人的幸福吧?看起來不怎麼樣、吃起來也滋淡味薄的水羊羹,一跟家人一起擠在暖桌裡吃,那滋味之好,跟在表參道熱門的店家前排隊半天才終於吃到的鬆餅,哪有孰優孰劣呢?我也從福井買了些水羊羹回家,邊吃邊想「冬天吃水羊羹實在太讚了啦!」一口就吞掉了一個。
我在這書中,不斷細細探索裏日本的特質、裏日本的幸福,那不張揚而卓美逸群、滋味豐富的幸福中,肯定還有很多是我還沒有發現的,這樣的幸福,自然也會密密沁入早已喘不過氣來的全日本人乾涸的身心中吧。接下來的日子,我想我大概還是會繼續往「裏」跑。
最後,本書得以付梓,實在是託了太多人的好意。包括總是溫暖迎接我、悄悄告訴我許多裏日本點點滴滴幸福的裏日本的朋友、陪我穿梭於裏日本大街小巷的高橋亞彌子女士、小學館的岡靖司先生,當然,還要感謝各位讀者讀到最後,謹在此敬表由衷感激。
二○一五年 初春
酒井順子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66折$211
-
新書79折$252
-
新書79折$253
-
新書79折$253
-
新書79折$253
-
新書79折$253
-
新書85折$272
-
新書88折$282
-
新書93折$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