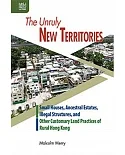《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重新出版序
自立報系要結束營業時,曾告知筆者其文化出版部1987年出版的《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族群變遷》一書已無庫存。一時間愣住,也不知如何是好。將來需要書的時候,怎辦?後來想要漸忘此事,卻也不得。為何?因為幾乎每一探討原住民當代課題的學術半學術非學術等大小著作,都必提到該書。本人一來發現到這本小小拙著似乎重要,另外則意外察覺自己後來大量新作竟無人聞問。於是開始大聲呼籲提醒重視同一作者的後續出版,唯幾多年下來,不理睬還是不理睬,受青睞終究就是受青睞。《認同的污名》繼續躋列大量專書文章參考引用書目行裡,其他如堆山高之謝世忠教授他著,到頭來不得不摸鼻承認不如小老弟謝世忠同學該本經典的份了。
一本書出版三十年過後,還要重新出版。這是什麼份量的書,有此價位?其實它就薄薄五萬字。本來不足七萬字,根本難以成書。當初自立的魏淑貞總編真是慧眼,破例也是魄力接受出版。她老是讚揚係因看到年輕貌美的李莎莉小姐捧著書稿來詢問,感動之餘,才同意出書,而並非那書有多棒哩!哈!無論如何,縱使學界同窗曾於標榜新潮臺灣研究之社會學刊物上狠批該書,還有資深學者論及當代人類學研究時,也不太認可此書,其他老輩人物不是質疑「只有聽過文化變遷,哪來族群變遷說法啊」,就是直指「認同的污名」一詞語意不通。種種指摘從不停止,然而,原住民讀者卻也連續世代都在讀它,一直到現在。現在是何時?就是作者已經從翩翩少男變成很有型的綠領帶亮頭額資深年紀人了!
一本書在特定領域上接近獨領風騷,是巧合,還是一切在作者掌握之中?關於《認同的污名》這本書的情況,我自己很難說明白。說是巧合,但,記得寫作概念形成之際,總似有一股衝動之氣在心底燃燒,一定要寫個什麼出來,才能點睛醒甦。換句話說,就是自己亟欲求個明白,弱弱塌塌的「山地人」,哪來突然借力高聲呼喚「我是原住民」啊!?那是一份神奇現象,但是,總有個道理。
在書中作了解釋。原運出現有根有據,道理十足。這份道理的提出,應該是打動到許多原住民讀者。會被打動,就是一種自然的體會。也就是說,作者書寫文筆不一定佳,整體章節結構也可能不是最理想,但是,少少的證據卻全被領受,有限幾個觀點也盡數成了族人共識結語。於是乎力量快速匯集,原運領袖們都說,憑藉著閱後心得,大家忽然間取得了自我行動的顯著學理支持基礎。
影響力還不只這些。90年代初的清大獨臺案事件中,涉事學生所閱讀的書籍,就有包括《認同的污名》。當時無疑是屬於前衛書冊之一。年輕人讀者增加,表示過去所陌生的山地社會,如今終於有了不是那種風花雪月或政治教條或學術規制類屬的入門書了。
在族人寫手尚未較大量現身之上個世紀最後十年,如欲認識原住民世界,到底應建議閱讀一般標準人類學民族誌呢?還是《認同的污名》?還真是拿不了準。理想上應是先前者,再後者,也就是先知傳統,再看看當下情形。但是,事實上,漸露頭角的原民知識領袖在推薦好書時,卻必有《認同的污名》,而學術認定下的優質多本,則多被直接忽略。小書的熱度,可見一斑。
筆者今年完成了《後「認同的污名」的喜淚時代—臺灣原住民前後臺三十年1987-2017》,就在《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族群變遷》出版三十年後。轉到玉山社繼續讓好書出版有聲有色的魏淑貞總編,除了全力支持新的前書出版之外,也建議舊的後書也可老瓶裝鮮酒,寫個新序,換個封面,美編加強,一起與新書套裝上市。多棒的高見,作者全心配合。這回又再度勞駕李莎莉小姐了。仍是由她捧書見人。老友相會,總編必定再提那年美如花姑娘為新婚不久夫婿抱書稿找出版的浪漫,只是二位都已屬資深美女系列,會心對笑,不在言中。
為何需要妻子捧著紙本書稿跑攤出版公司?新舊二書作者剛好人都在國外是理由一,另外就是莎莉總是比顧前瞻後的筆者勇往直前。筆者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受邀擔任美國奧瑞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傅爾布萊特禮訪教授(Fulbright Courtesy
Professor)。大學位於Eugene,是個小型城市,筆者譯之幽靜市。幽幽靜靜之處,重新想及過往生命史,翻閱單薄小本卻也是著名現代古書,有語無語和孤單熱情雙重效應,心底已然記上一筆。
再次感謝魏總編和她過去的自立團隊以及今日的玉山社眾位出版大將。莎莉三十載奔波加上日夜鞭策,同樣再謝。當然,《認同的污名》過去和未來的讀者是最為重要的一群。沒有她(他)們,作者不可能獲得鼓勵,也就不會有後續的發展。由衷感謝!新版趁此修潤幾處誤寫錯字,餘皆原封原樣。
力邀原住民老友新友還有所有人,大家一起重讀此書。雖然此時大教授觀看過時小同學的羞澀鈍拙文筆,多少有點想鴕鳥藏頭,躲起來自己訕笑,旦無論如何,那是三十年前的真情境真心境,或許仍繼續真有勁。總之,再看更閱,保證回神有味,而心頭依舊會波動。畢竟,縱有時代滾流,我們始終追求良知。
謝世忠 於奧瑞岡州幽靜市
為了妹河岸
(Willamette River, Eugene, Oregon)2017年5月22 日
序
族群(ethnic group)、族群意識(ethnicity)、及族群變遷(ethnic
change)等的課題,在西方社會科學之社會種族關係,社會生物學理論,文化與族群認同關係,政治與族群形成的關係,及多數與少數族群關係等的研究中,一直是很重要的。然而,在臺灣,包括人類學與社會學在內的當代研究中,無論是田野民族誌的材料蒐集,或是理論建立的方向,卻都尚未觸及該等課題。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這本小書所傳達的研究心得,或已象徵著一種新的嘗試與努力。
1984年秋季,透過了對當時所修之「當代族群意識討論」一課的濃厚興趣,我決定把族群關係、族群意識、及族群變遷等相關課題,當作在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學習的主要對象。除了純興趣的原因之外,上述之臺灣人類學界缺乏這類研究的事實,自然更是影響選擇的要因。就在我確立研究方向的同時,臺灣原住民也傳出了社會運動的訊息。很快地,我提出了研究計畫,並於1985年7月返回臺灣,一方面想在純學術的領域內注入點新血,另一方面,我則有一種把關懷原住民從僅止於報導、同情、或爭論的架構提升至理論層次的理想。
在我的看法裡,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群變遷的問題,目前應是一成熟的時刻。一來是因原住民本身在當今社會文化劇烈變動下,已被迫不得不作意識認同上的根本變遷。再者,近幾年來,他們的知識份子以主動的姿態,加上有組織的策畫,正企圖尋求一種具復振本質的新認同。前者就是原住民普遍地產生一種對自己族群的負面認同感,我稱之為「污名化的認同」(stigmatized
identity)。而後者則是一種透過各族群的聯合運動,冀使原住民超越原屬族群(如阿美或泰雅等)來正面地認同「原住民」這個範疇。我稱之為「泛臺灣原住民運動」(Pan-Taiwan aboriginalism)。
由於這項研究具有介紹一新研究取向的性質,因此,上述的兩個主導整個研究過程的概念,在翻譯和名詞定義上,都煞費了心機。其中又以對「stigmatize」的詞譯感到最為困難。我考慮過「恥感」、「辱名」、及「愧名」等名詞,但最後都或因它們已有約定俗成的意義,如恥感(一種以羞慚感來制裁自己的心理情結),或辱名(污辱名節之意);或因表達的意思未及原意的深度,如愧名(一種暫時的羞愧感),而未予以選定。
「stigmatized feeling」是一種負面感覺的最極致。我雖決定把它譯為「污名感」,但因「污」字的負面意思非常強烈,即使這項研究係一具客觀基礎的詮釋,為恐怕會在個人的價值系統上產生出直覺的反感或偏見,我仍願在該名詞上作整體的保留。
這項研究從設計研究綱要、申請經費、田野調查、以迄完稿,一共花了兩年的時間。以英文撰寫的一份,名為「Ethnic Contacts. Stigmatized Identity, and Pan-Taiwan Aboriginalism: A Study on Ethnic Change of Taiwan
Aborigines」,其摘要已於1986年7月7日在芝加哥大學主辦的「臺灣研究國際研討會」上宣讀(見本書157頁)。中文的一份在完稿後,曾先送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審核,並要求發表。後因全文過長,不合該所集刊規格,始轉送自立晚報以專書出版。
這兩年研究期間曾得Stevan Harrell教授,Charles F. Keyes教授,Simon Ottenberg教授,張桂生教授,劉斌雄教授,李莎莉女士,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玉山神學院,及包括原住民和漢人在內的所有報導人等的指導或協助,謹致最深的謝意。
謝世忠 1987年6月14日黃昏
於西雅圖至臺北的飛航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