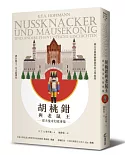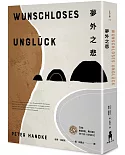譯注者序
翻譯德語藝術歌曲之歌詞,是筆者與台灣聲樂界結緣的橋梁。因為個人對歌曲音樂的興趣,既喜歡聽演唱會,也樂意幫國家音樂廳翻譯德語歌詞(自1989年),但僅限於節目單上演出曲目的零星歌詞。最早找我幫忙解釋歌詞,並希望我翻譯整套舒伯特和布拉姆斯歌曲各五十首的熱心聲樂家,是當年還在東吳音樂系執教的孟海蒂老師。由於筆者只顧忙於教學研究工作,翻譯大事一直未能如願以償,然而多年來,孟老師的倡議仍一直在我心裡盤旋。後來應林玉卿和唐鎮兩位教授的邀請,幾次到台北藝術大學演講,談德國古典和浪漫詩詞,讓我親身體會到演唱德語歌曲者面對歌詞語言的困境,瞭解掌握其中抒情語言,對於演唱者何其重要!江蕙的台語歌曲之所以唱得比歌后鄧麗君還傳神,因為她較能感受通俗語言的韻律和情感。同樣,在德語層面上,Fischer-Dieskau和Hermann
Prey唱起舒伯特和沃爾夫的Lieder之特別動聽,非世界三大男高音所能及。這讓我又想起Georgiades一再強調的理論:「歌德(的語言)點燃了舒伯特的歌曲創作精神,從這點我們再度認清,語言──不是文學──的力量凌駕音樂及任何藝術之上」(Georgiades 1992: 78)。
因此,我給自己許下一個任務,要將德語抒情詩和藝術歌歌詞一併納入翻譯和註解工作之列。於2001年向國科會提出譯注計畫,分成兩部:歌德詩歌(譯注I),浪漫時期德語詩歌(譯注II),各為期一年。除了要求文字翻譯的準確外,並詮釋抒情語言的格律、寓意、詩歌創作時代社會背景,甚至論及歌詞被譜曲入樂所表達的弦外之音。這個構想,有別於聲樂界有關《冬之旅》、《美麗的磨坊少女》等之以音樂曲式之分析為主題的詮釋方向。
如今譯注工作結束,筆者願將此譯注成果獻給聲樂界的朋友,感謝他們對本書的期待,並祈望音樂學界好友曾道雄、簡寬宏、孫清吉、彭廣林,及諸多音樂界賢達不吝指正。任何書寫,尤其是翻譯,不可能完美無瑕。從歷史化的眼光來看,任何書寫都屬於不斷改進的過程。
關於這兩部譯詩集容我稍作說明,這部譯注稿,包括「詩歌譯注導言」和兩部譯稿導讀,乃十年前所寫就。第二部:《德語抒情詩及藝術歌歌詞譯注II》也於2003年譯妥提交。最近應國科會的要求,希望將這兩部譯詩集整理出書。於是出版前再作一番增訂,修補更新,除增訂迄至2011年的文獻資料外,並加入詩人作家的生平年譜。第一部僅附歌德年譜於書末,第二部增附其他不同作者的生平事略,未收錄本書中。
本譯注計畫能夠順利完成,得歸功於國科會人文處提供經費支援。筆者在此表達誠摯的謝意。尤其感謝國科會魏念怡女士不間斷的支持,讓我能投入更多的時間與心力,完成此一多年的工作。
歌德詩歌:導讀
鄭芳雄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是德國人最崇拜的詩人和哲人偶像(Staiger 1981, Bd. 1: 7)。「只要歌德存在,德國就不會貧苦孤單。德國即使再顛沛、虛弱,也因為有歌德,精神依然偉大、富有、堅強。」歌德於1832年3月22日在威瑪逝世,當消息傳到慕尼黑時,德國著名的唯心派哲學家謝林(F.
Schelling)在科學研究院演講,作了上述的評論。1999年是歌德誕生兩百五十週年,德國各大出版社無不以精美的版本,重新出版歌德作品(威瑪版全集共143冊),紀念這位德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而歌德所以能傲視世界文壇、能與荷馬、但丁、莎士比亞等人並駕齊驅,乃基於他抒情詩、小說和戲劇的創作對德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之貢獻。他在83年生命中,集詩人、思想家、自然科學家於一身。霍珀(V.
Hopper)在《歐洲文學精要》譽之為文藝復興之後最博學的詩人。卡夫卡曾夢見歌德而絕筆,認為歌德的文學創作是一道無法跨越的尺度。文學上的偉大成就是歌德被偶像化的客觀條件。詩人海涅曾提到一個幽默的寓言:他邀請歐洲各國的詩人,一同到翠綠的森林中縱情歌唱,讓夜鶯來作裁判,他深信,歌德的歌曲在這場歌詠比賽中必將獲勝(張玉書 2002:10)。
歌德八歲時就會寫詩。十七歲進入大學時開始學詩、寫詩,直到晚年,在其長壽而又多彩的一生中,抒情之筆從未間斷過。他所留下為數二千五百多首的抒情詩,是詩人一生「自白之片段」(Dichtung und Wahrheit, HA Bd.9:
283),是生活智慧之結晶。其詩或歌詠愛情、讚頌自然,或宣洩狂飆之氣燄、描寫生活情景,題材與形式風格之廣泛,橫跨洛可可、狂飆、古典、浪漫諸時期,內容包羅萬象,道盡人生世相之悲情與歡樂。在歌德抒情詩的大花園裡開著各色各樣美學經驗的花朵,所表達思想之深邃、情感內涵之豐富,使得他優美之詩句,智慧的警語,迄今兩百多年來一直為後世人引述和傳頌,其影響層面,凌駕其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和詩劇《浮士德》等其他作品。
「德國人最崇拜的詩人和哲人偶像」,上面Staiger的說法只從德國國家文學的觀點立論。其實,歌德的詩早已跨越國家文學的界限。「世界文學」的概念是他首先提出,而且是他在談論中國小說的時候提出(Eckermann 1955:
211)的。他常運用希臘羅馬古典文學和義大利題材自不用說。他翻譯蘇格蘭古詩,研究莎士比亞,他翻譯印度古詩和波斯詩歌,並將後者融入其《西東詩集》(West-östlicher Divan)的情節,他翻譯中國詩,並仿作14首中國詩:他寫中國詩所表達中國味之濃,堪稱一位「說德語的中國詩人」(鄭芳雄 1999:1),而用詞之優美,曾令里爾克(R. M.
Rilke)驚嘆讚賞,這些詩部分由布拉姆斯作曲。以上列舉數例,不過藉以提示歌德與世界文學的關係,不便詳述。
歌德的詩之所以跨越時空,不僅因為它「乘著歌聲的羽翼」超越語言國界,而是因為他的詩,自史雷格(Friedrich Schlegel)、黑格爾、叔本華、尼采以降,到近代的海德格、班雅明、阿多諾,一直為哲人及文評家爭相引述,作為美學哲學和文學批評立論的依據,以致談到現代人文的演變,學界有人指出,歌德仍是現代不少「大作家和語言學家的標竿」(Schärf 1994:
5),一直廣被引述,因而形成詩人創造文本,哲人提出詮釋的美學傳統。換句話說,對於二十世紀人文的疑難雜症,這位德國古典詩人仍有話要說。
在歐洲,中晚年歌德既成為各方景仰的文學泰斗,其作品的影響力亦甚可觀,在法國首先透過史黛爾夫人(Mme. de
Stael)之評介,其他作家如紀德、羅曼.羅蘭、法拉利都翻譯及評述過歌德的作品。在英國,詩人拜倫(歌德之友,《浮士德》劇中浮士德與希臘美女海倫結合所生之子Euphorion升空墜地,即在影射拜倫)、雪萊、尤其是卡萊爾更是歌德的代言人。再則十九世紀俄國大作家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也都是歌德文學的崇拜者與發揚者。種種文學影響的例證,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