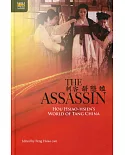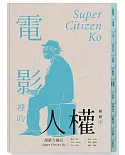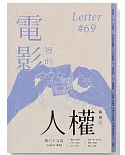自序
在電影中戀愛
所謂自序,大約是一份自供狀,交代我和電影那點不得不說的事兒。電影已經成了流行文化的入門標靶,人人說得,我又能說些什麼呢?沒有科班訓練的沖刷,自然不敢勾就一副地圖指點別人怎麼從碟影重重中突圍。想到一個關鍵字:愛,但是曠男怨女寫給電影的遺情書已然氾濫,我又能彈撥出什麼弦歌雅意?我能自信的,也許還有幾分東拉西扯的獨門功夫,沿著電影這枚葉片上縱橫交錯的脈絡,總能抵達一片水草豐美的迦南美地吧。
作為一個面目模糊的城中女人,情感、生活、履歷皆乏善可陳,生於現代,不知幸耶,或是不幸?我們得到了太多前人無法想像的,也缺失了很多,包括山重水複柳暗花明的驚喜,包括幾處早鶯爭暖樹的恬淡,包括兩情相悅山無稜天地絕的篤信,包括兩軍對壘冷兵器較量的勇氣……電影是我那點一直沒有進化的童話情結的城堡,我是盤踞其中的中世紀遺老,說不清有多少個夜晚,執拗於在光影傳奇中圓滿自己的初盟,如同光線找到了窗口般,一瀉磅礡。《開羅紫玫瑰》中,女主角愛上了影片中的男主角,天天到影院去看他,而他真的從銀幕上走了下來,與她相擁起舞……哪裡是幻象,哪裡是真實,一切彷彿觸手可及。
電影,是我愛情最初的出發地。
也許遭遇一個打倒偶像的時代並非幸事,但是對那些面孔,我是那樣真切地愛慕過。猶記那個髮不濃,唇不紅,齒非皓的青澀小女生,靜候午夜劇場,彷彿小獸,屏息捕捉那個男人的一舉一動。心被捏住似的,有點不能呼吸,又有點隱隱的絕望。那是什麼來臨了呢?我安撫唇齒,不教它們洩露菡萏心事。
初次邂逅《太陽浴血記》。
那個邪惡的壞牛仔,他叫派克。此後看過的《百萬英鎊》、《雪山盟》,乃至那部被引為女人必讀聖經的《羅馬假期》,卻始終滅不過那個牛仔的位次。那是派克最出位的一次演出,血性強悍,不擇手段追逐女人和金錢,沒有人倫王法,片尾這個惡徒的死卻讓我悲傷難以自抑。此後他出演的角色就是量身定做,就是在出演自己,怎能不隨性釋放魅力?怎能不攝人心魄?又怎能不在萬千女人愛慕的眼光中載浮載沉?
他的魅力自是櫥窗裡一件夢寐的華服,雖隔著玻璃也似清晰可得,仔細一看:卻是非賣品!這樣忠誠的姿態打擊過多少女人的覬覦之心,相守終生,如我輩凡人稍有蠢蠢欲動的念頭也是難以做到,何況他的傾城風華?我喜歡的保羅.紐曼,有次記者問他的妻子,在幾十年的原裝婚姻裡,總擔心會失去他,如何緩解這種壓力?七十多歲的紐曼一把牽過妻子的手,不容置疑地說,其實是我一直在擔心失去她,她一離開我的視線我就慌亂不安。好萊塢之王克拉克.蓋博,他塑造的瑞德是無數女人渴望遭遇的經驗,如鐵砂不可遏制衝向磁鐵。而他與卡洛兒.隆巴德的愛情更是人間絕響,愛人飛機失事後不久,蓋博也離世而去。
於是想,這些男人身邊的女人,也必非凡品,否則怎能讓他們一顧便是終生。塵囂中的劍膽男子必也有最清醒的琴心,明白所有的笙歌弦音終將收束於一個指勢。繁華落盡時,身邊有人如玉,目光如星輝彌漫他整個的天空,為識途浪子照亮回家的路,君心似我心。
腦海中定格的這些鏡頭從未消弭過:
《羅馬假期》裡那個矛盾不堪、深情、青澀而又佻達的派克;
《虎豹小霸王》裡一抹似有若無的譏誚微笑始終掛在嘴角的紐曼;
《Wild heart》裡擁有那樣一道灰飛煙滅的眼神的凱奇;
《刺激一九九五》雖囹圄繫獄卻似閒庭信步的提姆.羅賓斯……
女人的口味會因為間接的經驗而被寵壞,遭遇這些光年之外的男人,會讓我們對生活懷恨在心,這對我們,真的不公。這不是個天才巨鬥的時代,我拿自己託付給誰呢?
而對男人,這豈非更是一種不公?男人之愛夢露,愛她作一個極致的女人,溫香軟玉,我見猶憐。女人愛慕一個偶像,卻是仰望,執迷於在身邊尋找和他有一絲牽連的端倪,即使最終不過是拙劣的翻版;男人會愛一個女人的頭腦,但決不會視而不見她美好的身體,女人在心版上鐫刻一個男人,卻能把他抽象成一個符號,甚至把整個物質世界純粹化精神化,因遙遠而美麗,因美麗而痛苦,最終變成個美麗的圖騰;男人不會因遙遠的愛慕而放棄身邊的可能,法國大餐與速食麵可以得兼,而女人卻能進入一個催眠的精神隧道,在無眠亦無醒的夜裡無望地守節。
已非二八年華,愛過的人和走過的路,不仔細翻檢都會有點模糊,信馬游韁於飄搖的逆旅,識的途卻是光影交織的不老神話,閒來翻一卷出生不明的老片,看那些愛過的男人經過時光打磨雖霜染鬢髮,犁耕額頭,仍然顛倒眾生,捫心自安:還好,你沒有變!梅雨來時,鄰家那個鹵莽小子讓人臉紅心跳的情信都已爬滿了幽幽黴痕,但我電影中的戀人們,誓言依然鏗鏗鏘鏘,擲地有聲,或是孟浪登徒子,或是款款癡情男,抑或單騎遊俠兒,冷面鐵郎君……一二浮光掠影的片斷,最終會是流光溢彩的過往。
在電影中戀愛,一樁無法典當的因緣,一段不可變賣的情愫,一線洩露天機的月光,一衿抖落不掉的桃花。我的心會守口如瓶,等待有緣人的參悟。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