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難以成為歷史的人
史惟筑
人們死去後成為歷史;雕像死後成為藝術。
──《雕像也會死亡》
有沒有可能人們死去後沒能成為歷史?
如果有,是否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死去之後,在哪裡?
1953年,法國導演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與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接受人類博物館的邀請拍了《雕像也會死亡》(Les statues meurent
aussi)這部影片,拍攝動機源自一個看似簡單的提問:「為什麼古希臘與埃及藝術進了羅浮宮,而黑人藝術卻被放進人類博物館?」然而,用來回應這個問題的答案竟卻遭致長達十年的禁演。影片抨擊了法國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替文明劃分了位階,人們不以藝術作品的價值做為「去哪裡」的判準,而是單看它們的出身。「去哪裡」成為影片指向性的浮標,去與不去伴隨著層層疊疊的問題意識與政治判准,以及文化選擇的政治路徑及文明死亡過程。
《第六十九信》所欲處理的問題意識縱然與《雕像也會死亡》不盡相同,但後者的提問與觀點,特別是誰被決定去哪個博物館,以及用一種近似挖苦卻又一派正經的旁白口吻,在影片一開頭便註解歷史與藝術成形的法則,進而對照出《第六十九信》殘酷的真相:沒能成為歷史的人,哪也去不了。受難經驗的停滯形態需要「動詞」去跨越無法以歷史安魂的障礙,於是《第六十九信》提出了一則邀請與回應。
大部分台灣二二八、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歷史記憶工作,首先面臨的難題並不是他們該「去哪裡」(該被安置在哪一種空間、形式),而是被「在哪裡」這更為複雜的命題所制肘。如果我們把「在」作為抽象的動詞概念,放在空間與時間的軸線上,前者在受難者個人、與他者關聯兩種生命型態上取徑,後者則在過去與未來對生命進行兩次叩問。以空間來思考,「在」首先試圖探問個人生命路徑:他們曾在哪理工作、生活?曾在哪裡遇見誰?在哪裡被抓?在哪裡受難?我們得知這些故事後,才有辦法讓他們成為歷史,也才有條件思索歷史要以什麼樣的形態與目標「去哪裡」。其次,將受難者與他者關聯,則是希望「在」能勾勒不同圈層的地緣政治景觀:團體與社會、社會與國家、國家與國際。這是希望了解受難者所屬的(政治或非政治)團體身處何種社會氛圍?這個社會,又被何種國家體制形塑?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該國家在世界政治角力中,又分屬哪個陣營?
從時間維度來看,上述兩種生命形態的空間概念是立基於過去時間,而「在」也需要於生命結束之後進行第二次探問。政治受害的倖存者,得以親自建構「在哪裡」的歷史證言,也可以自身存在,牽引數道在歷史與當代社會間相互拉扯的觀察。然而被處以極刑的人,其經驗與記憶要如何在生命之後獲得延續,則面臨困難且困窘的雙重難題。「施水環」三個字便是一道讓人感到困窘的歷史難題。大部分的人不曾聽過她,誠如大部分缺少證言、歷史文件或「英雄式」受難經歷的大部分受難者一般,是死去後難以成為歷史的人,讓「在哪裡」成為歷史前後安置上的難處。
不似《雕像也會死亡》中人死後便能成為歷史這般理所當然,於是,原本在成為歷史或藝術之後該去哪裡的路線問題,在「是否成為歷史」都無法確定的前提下,路徑順序出現了差異,「去哪裡」反倒成為有能力解決難題的引線與動能。當代台灣人一肩扛起責任,決意將受難主體先置入人權與歷史正義的向度,再努力尋找歷史書寫與創作的方法。「在哪裡」也順勢成為指引記憶所能、所繫之所的座標,並從個人與他者的空間維度中另闢蹊徑。
六位作者所提出的十個關鍵字,拓鑿了通往施水環的生命路徑,提供個人生命「在哪裡」的歷史線索。《第六十九信》中的施水環除了是她自己,更作為其他受難魂的共同體,因此這些關鍵詞除了作為施水環遇難前的生命線索,也牽引出其他共同的受難經驗與狀態。「施水環」、「丁窈窕」、「郵電工作委員會」,令我們一窺曾出現在施水環身邊的人與事;「窩藏匪諜」、「獄中書信」、「辦事清明的法官」則在歷史書寫之中揭露無論是在實質(監獄、窩藏處)或抽象空間(戒嚴體制)中,身體囚禁的暴力經驗;「學生工作委員會」、「韓戰」則將國家暴力置入世界政治角力競逐的地緣政治脈絡,理解當時台人的理想與拼搏;而即便「女性政治受難者」與「六張犁墓區」代表生命的消逝,卻不駛向終結。至少,當代歷史與影像工作者努力不讓它們成為終結之所。
於是,生命在消逝之後得以續存,是這些書寫組成的樂譜,讓閱讀文字後敲響的樂音,讓原本無法成為歷史的存在,在一篇又一篇的章節中,停留、駐守、再啟程。生命終結後所進行的第二次叩問,是讓文字為受難者曾經「在哪裡」定錨,再藉由篇章之間所交錯的聲響音迴,讓過去成為未來;不只能成為記憶在永恆的當代中駐留,更能再度啟程,去到更遠的可能。如,《第六十九信》。
它是導演為施水環最後一封未完書信所勾勒的思念,也是向她道別的禮物。歷史縱仍留下諸多遺憾與悵然,道別的言語卻在想像與探索間,讓歷史的未竟之業開展出深邃無垠的記憶星河:該如何記憶你?是否這般記述他?在朝向你的模擬姿態中,伸手即能撫觸被掠奪自由的傷?藝術提供一處安置之所,照亮隱跡的溫柔與意念。歷史或許無法翻轉,但美學始終可以想像,讓曾失去黑夜白晝與我們的共在,至此成為影像上永恆綻放的光點,實現那則施水環交予丁窈窕的祝願,也是我們為所有受難者祝禱時的信念:「祝你就像無雲天空中的星星/永遠不會消失/並永遠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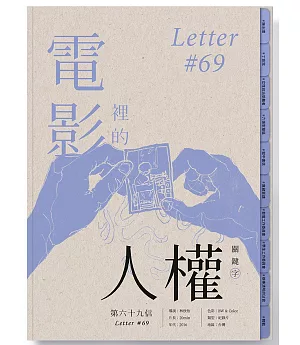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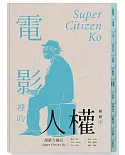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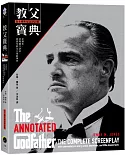



![法國電影新浪潮[最新圖文增訂版]](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85%2F78%2F0010857826.jpg&width=125&height=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