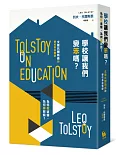序
這本小書是為對歷史感興趣的讀者而寫。
數十年的歷史學習和教研使我明白,歷史是一個無窮無盡的知識寶庫,它積累了前人(包括千百年前的古人,和數十年前、甚至數天前)的行為舉措,他(她)們的成敗得失和經驗教訓。歷史是人類文明長期延續的一部分,現代的一切,不是突然而來,沒有從前的探索、挫折和突破,就沒有現在的成果,因此歷史是認識現在、邁向未來的基本知識。正常的國民教育,必然重視歷史,使國家民族的盛衰教訓世代相傳。
然而,古人與往事早已逝去,即使是數年前的人和事,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處境的改變,細節逐漸消失,歷史的真相變得模糊,再加上傳述者據自己的立場和視野取捨改編,聽受者只接收一二重點,再加以想像發揮,隨意猜測,於是歷史事實被傳述得面目全非。這樣的歷史傳述十分普遍,甚至成為一般人的歷史常識。當然,以虛假的歷史作出判斷和評論,並且廣泛傳播,只會形成似是而非、自以為是、人云亦云的風氣。只有正確的歷史知識,才可以提升鑒往知來的價值,增進人們的認知和思考能力。
歷史是現代教育課程的一部分,原意是培養國民對國家民族發展的認知,但教育官僚只注重評核成績,把原本豐富多彩的歷史,在教科書中簡化為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份、事件名稱,和一些概括的敘述、分析。「秦始皇」、「武則天」、「五胡亂華」、「辛亥革命」等等,都只是一堆符號,這些與學生生活無關的詞句,教的學的都索然無味,老師、學生只憑一兩點資料,發揮想像。歷史被「教死」了。歷史課程失去了活力,變得可有可無,於是教育官僚們設計了甚麼「通識教育」,甚麼「國民教育」,取代歷史科的位置。殊不知,所有思考、評論、批判,必須建基於知識基礎之上,否則一切都是空談;本國的歷史、地理和語文,就是國民教育之母。捨棄了歷史知識,通識教育、國民教育都無從建立。
歷史既然是由前人的所作所為所構成,無可避免地,所有的歷史人物,都生活在他們的時空之中,他們的所作所為,需要考量他們的處境,而不是以我們現代的時空和處境為準則。然而,現代人對歷史的評論,對歷史人物的褒貶,卻往往以現代的價值標準、憑現代人的意願作批判,這是厚誣古人,有失公允。其中一例,就是古代婦女地位問題。現代強調女權,而古代是父權社會,女性從屬於男性之下,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當時人認為正常,但現代女權分子代古代婦女抱不平,對古代男性主導的社會強烈批判。其實這大可不必,古人自有他(她)們平衡社會利益的途徑,非我們現代人能越俎代庖。
歷史的主角是人,無論帝王將相、平民百姓、奴婢僕役、市井無賴、盜賊妓女,無論男女老幼,都是歷史的一部分,他(她)們可以是歷史的主導者、參與者、旁觀者,或許是歷史事件的襯托者,總之,沒有人物,就不可能發生歷史事件。試想,荊軻刺秦王一事,現場除了秦王和荊軻之外,還有多少其他人物!事件的過程,又有多少人牽涉其中?秦王、荊軻以至其他參與者的每個人背後,又有多少家人和朋友?他們形成一個歷史時空、聚合了一個處境、演繹了一起歷史事件。其他的歷史事件,何嘗不是如此?因此傳統中國史學,特別重視人物的記述,西漢武帝時太史令司馬遷編撰《太史公書》(即後世所稱的《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主體,自此之後,歷朝都以紀傳體為「正史」。
數千年的古代中國社會由男性主導,完全反映在「正史」之中。傳統中國的正史(即所謂「二十四史」),為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人物立傳,可以立傳的人物絕大部分是男性。傳統的女性,絕大多數一生相夫教子,操勞家務,有些婦女更擔當了農事、紡織等生計,卻無緣於政治、軍事、文化,因此甚少在正史中立傳,她們甚至連名字也沒有留下。這半邊的歷史,被歷史記述所隱沒,然而,她們的確存在,而且為中國的文明進步作出了沉默卻巨大的貢獻。事情總有例外,一些傑出的古代女姓,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爭取得一席之地,凸顯了歷史地位,因而記述於史冊,或者受到社會的傳誦。她們有些憑丈夫而顯貴,因而有機會挑戰男權;有些因糾纏在男性圈中而受注視,成為歷史的角色。
在男性主導的記述之中,無論對她們是讚揚還是責備,都是難能可貴的。數年前,香港電台文化教育組,邀請我主持一個為長者服務,名為《巾幗列傳》的廣播節目,並且編撰了一部簡單的教材,內容是介紹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女性。由於這節目的聽眾是老人和學生,不能太深奧,也不能太枯燥,所以文稿儘量寫得簡單,但並不偏離史實。節目完成之後,我累積了二十六則簡單的文稿,一直擱置。其後香港中華書局的李占領先生、黎耀強先生向我約稿,於是我修訂了《巾幗列傳》的文稿,並增加了隋唐的部分,完成這本小書。
這本小書是為了普及歷史而寫,對象是一般讀者和學生,所以儘量通俗,省卻繁瑣的考證和註釋。但史事的選取和記述,都以文獻為依據。《巾幗列傳》在播出和撰寫期間,得到香港電台的鄭啟明先生、何翠□女士,及香港公開大學的舊同事曾卓然先生的幫助和支持,謹此致謝。
張偉國 二0一一年七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