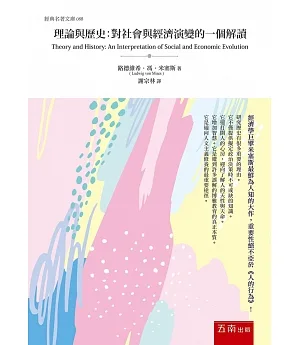序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這本首次出版於一九五七年的著作裡 ,論述人的行為科學中的歷史學部分,補足了他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 裡,特別是該書第二章〈人的行為科學在認識論層次的一些問題〉,受限於篇幅,未能充分闡釋歷史研究的缺憾。
例如,《人的行為》第二章一開始便提及「歷史本身不會提供可用來解決具體問題的知識與技巧」,同時又點到「研究歷史讓人變得比較明智與持重」;但,對於為什麼要研究歷史,以及研究歷史如何讓人變得比較明智與持重,當時並未有進一步的說明。對於這些問題,本書第十三章〈歷史研究的意義與用處〉有發人深省的觀察:「如果個人所面對的情況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充分加以描述,向歷史求助便不可避免」;「對於現在狀況的分析,沒有非歷史分析這種事。對現狀的審視與描述,必然是一個關於過去……的歷史記述」;「在人間世事的領域,要知道某一件事情,就必須熟悉它是如何發展而來的」
;「研究歷史,還有更多、更重要的理由。它不僅提供擬定政治決策時不可或缺的知識。它打開人的心房,迎向了解人的天性與天命。它增加智慧。它是遭到許多誤解的那個範疇──通識或博雅教育(a liberal education)──的真正本質。它是通向人文主義修養──傳統對於人性特有的、使人有別於其他生物的、人所特別關心的那些事項的認識──的最重要途徑」。
另外,對於歷史知識的性質和研究方法,本書核心的第三篇(第九至第十四章),相較於《人的行為》第二章,也有更為深入淺出、充分與精確的闡述。對於這一點,讀者如果細心比較兩書對於「理想類型」或「理念類型」(ideal type)的處理,當更能體會,《理論與歷史》已超越《人的行為》在相關論述上對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倚賴,而更契合行為學的邏輯脈絡。
米塞斯思想在美國的主要傳人和闡揚者,羅斯巴德教授(Murray N. Rothbard,1926-1995),為本書原著於一九八五年再版所寫的序裡,感嘆米塞斯劃時代的四本著作中,《理論與歷史》最為人所忽視。他說,米塞斯一九一二年發表的《貨幣與信用原理》(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一九二二年發表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以及一九四九年表的《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等三本著作,即便遭到偽經濟學界的抗拒,畢竟獲得回響、產生了一些衝擊效果,唯獨《理論與歷史》自問世以來一直乏人問津,即便是對奧國學派經濟思想感興趣的年輕學者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他認為,與其說因為《理論與歷史》富於哲理,而一般經濟學者,由於盲目學術專業化(blind academic
specialization)的緣故,對一切比較廣泛的哲理討論都退避三舍,不如說因為他們無法接受《理論與歷史》所論述的哲理內涵,也就是,他們無法接受本書一開頭便揭示的方法二元論(methodological dualism),而這又是因為他們相信,經濟學若要成為真正的科學,就必須以物理學為師,採用實證論(positivism)所闡述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
沒錯,實證論的確和歷史的觀點格格不入。自然科學預設與探索事物彼此之間「不變」的連結規律,而歷史的本質卻是「變化」,所以自然科學與相關的認識論(實證論)可以說是非歷史的(ahistorical)。但,非歷史的,或者說,否定歷史與人的行為領域存在的,並非只有實證論,還有形形色色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完美人類狀態的妄想等等,而對後面這些謬論的揭發,在本書所占的篇幅,還遠大於對實證論的批駁 。就此而言,羅斯巴德所寫的序,略過歷史主義的相關討論不提,對《理論與歷史》的評介未免美中不足。
其實,米塞斯對實證論的批駁,主要見諸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經濟學的終極基礎:經濟學方法論》(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在那裡,他說,「關於人的行為科學,目前在認識論層次有許多誤解。但,如果暗示所有這些誤解都應歸咎於不當採取了實證論的認識觀點,那就錯了。除了實證論,還有其他一些思想學派也混淆了行為學(praxeology)和歷史學(history)在認識論層次的差異,而且混淆的程度更為嚴重,例如,歷史主義(historicism)」。
就我個人來說,翻譯這本書的最大收穫,是當翻譯至第十六章第三節〈完美人類狀態的妄想〉時出現了頓悟:任何所謂均衡、或「最後」狀態與秩序等概念,充其量只是理論家用來分析現實的思想輔助工具,在現實世界中沒有它們的對照狀況;如果把握不住這一點,或者說,把這些概念實體化,它們就變成某種愚蠢的、否定歷史與行為的「完美社會新版本」。歷史與行為的本質是改變,所以歷史與行為沒有最終或完美,只有綿延不絕的過程。這個頓悟讓我發現,米塞斯和另一個通常也被歸類為奧國經濟學派大師的海耶克(F.
A. Hayek) ,兩者之間的根本差異就在於:後者仍然鍾情於探求自己所嚮往的社會秩序,而非專注於社會變遷過程的分析。在台灣與大陸,海耶克比米塞斯更為著名,所以把這一點記下來,謹供研究海耶克思想的學者參考。
本書關於術語的翻譯,大多採取網際網路上可查找到的通行譯名,除了Behaviorism一詞譯為「觸動主義」,可能會引起爭議。Behaviorism通常譯作「行為主義」,但由於不管是在《人的行為》或是在本書裡,「行為」一詞已保留給Action作為專屬的譯名,而米塞斯所闡釋的「science of human
action」(譯作「人的行為科學」)又和behaviorism根本不同,所以有必要改變Behaviorism的通行譯名,以免混淆。有人曾將Behaviorism譯為「唯動作論」,這裡所以未予沿用,只因「動作」出現一個站立的「人」,太有人味了。除了要除掉這個人味,將Behaviorism譯為「觸動主義」的另一個考量是:Behaviorism嘗試以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在刺激─反應的架構下,研究人的所謂「行為」(其實只能是人的無意義「反應」);我覺得「觸動」一詞比較能捕捉住「刺激─反應」的意思。
最後,我要感謝劉天祥先生,他的細心校訂讓本書更為可親可讀。
謝宗林
於台北
2019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