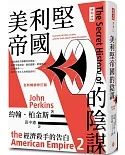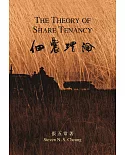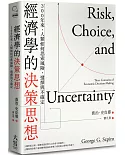制度的選擇是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範疇。個人之見,這是整個新制度經濟學的範疇了。幾年前美國創立了「新制度經濟學會」,今天舉世知名,而最近又加上「高斯學院」,並駕齊驅,好不熱鬧。然而,從經濟學分類中的比重看,新制度經濟學在美國不及在中國那樣受到重視。
中國的偏愛有三個原因。其一是雖然數學在今天的經濟學無處不在,但談到新制度經濟學,不懂數的也可以一抒己見,沒有誰會說你不懂數就不懂。制度是真實世界的事,是每個人的經驗,只要有洞察力就可以作出貢獻。那石破天驚的高斯定律是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有機會想出來的。
第二個原因,是今天在中國比較年長的人,在經驗上對制度的認識一般地超出西方的經濟學者。制度的不同對生活的差別有決定性,他們都知道而又相信,雖然可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對那所謂市場經濟還有存疑之心。不管怎樣,他們之中有不少人對不同制度的運作與效果好奇,提出質疑,希望多知一點。
第三當然是中國的開放與改革了。那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經濟革命,不管我們認為還有數之不盡的問題,貪污成市,法治糊塗,但制度的改革使生活的改進一日千里,有目共睹。同樣重要的是思想的開放。不是放得像香港或歐美那樣寬,但比十多年前是寬得多了。今天在國內大學的求學氣氛,我遇過的只有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可與之相比。
這幾年,我到大陸講學不下三十次,所到之處,學生與老師朋友所提出的,大都是關於制度或產權的問題。這些問題我答來容易。但我想,如果時光倒流四十年,以作研究生時的經濟學知識,我是不能回答他們大部分的問題的。當年的制度經濟學,主要是歷史與一些不知所謂的數字,加上幾張清單,說資本主義什麼好什麼壞,社會主義什麼好什麼壞之類的文字,又或是馬克思怎樣說,熊彼得怎樣說,等等。這樣的學問是一潭死水,不可能回應今天中國青年需要知道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R. H. Coase)到瑞典領獎,我到那裡與他相聚,大家談起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對我們數十年耕耘的所得很有點失望。我們還需要知道的多的是。認真研究的人永遠都覺得沒有寸進。但一分一分地進,日以繼夜,過了二三十年,驀然回首,在燈火闌珊處我們還是發現今非昔比,覺得世界是比昔日的簡單得多了。
好些人說我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其中一個始作俑者,那大概是對的吧。六十年代初期起全力參與其事的,只有四個人。一個是我的老師艾智仁(A. A. Alchian)。艾師後來被稱為產權經濟學之父,主要是他當年的口述傳統。第二個是德姆塞茨(H. Demsetz)。此君在洛杉磯加大任教時,我是他的改卷員,不覺得他怎樣。但六二年他轉到芝大,遇到了史德拉(G. J.
Stigler)及高斯,一下子變作天才。六三年艾智仁秘密地給我閱讀一篇隔行打字六十多頁長的、德姆塞茨寫的關於交易費用的文稿,清楚而又有說服力,對我的影響很大。
第三個應該最重要。那是高斯。他在五九年發表的《聯邦傳播委員會》與六○年(印遲了,六一年出版)發表的《社會耗費問題》,深不可測。這兩篇文章我反覆重讀,從六二年讀到六五年。高斯定律始於五九之文,定於六○之作,但定律之名是一九六六年,由史德拉再版他的《價格理論》一書時提出來的。高斯本人不認為他有什麼定律,我也是那樣看,但定律大名一起,要禁也禁不住。以人名為定律,經濟學從來沒有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那樣大名。此定律將會百世流芳是可以肯定的吧。
第四個輪到我。不是說我的功力如何,而是說早期全力研究產權及交易費用的,我是四個人之一。當時我是研究生,最年輕,可謂童子無知,躬逢勝餞。
六三年讀了德姆塞茨的長文稿,而更重要的是受到高斯及艾智仁的感染,我決定博士論文要在產權及交易費用那方面下注。艾師當時是反對的。他認為這些題材太困難,不是一個研究生要染指的。他說得清楚,要拿博士,找些比較肯定有收穫的下注,產權及交易費用是博士後才可以下賭注的。
堅持己見,轉了幾次論文題目我歸宿於佃農理論。影響這理論的有三部分。其一是洛杉磯加大三位老師傳授的價格理論;其二是以高斯的想法推理;其三是戴維德(A.
Director)的捆綁銷售口述傳統的啟發。於今回顧,雖然我在《佃農理論》中沒有感謝戴維德,但主要是他的影響使我後來被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始創人。戴老的捆綁銷售顯然是一種價格安排,是電腦租用合約中的一部分,而這安排是一個選擇。於是,考慮佃農分成,雖然沒有明顯的價格,一開始我就把分成作為一種價格安排,而佃農是一種合約,是選擇的結果。要是我不從合約與競爭的角度看佃農,其理論我可能永遠想不出來。
今天盛行的合約經濟學,是從佃農理論開始的。想不到,今天盛行的僱主與代辦(principal-agent)的分析,也是始於佃農理論。我從來沒有刻意地研究過僱主與代辦的問題。我的興趣是合約:六八年發表的《私產與佃農制度》,六九年發表的《合約的選擇》,七○年發表的《合約的結構》,七二年發表的《舊中國的婚姻合約》,七三年發表的《蜜蜂的神話》,七四年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九二年發表的《新制度經濟學》,九八年發表的《交易費用的範疇》等,是我自己比較滿意的作品,都是與合約有關,以合約為重心下筆的。
我是六七年到芝大去的。當時該校的經濟系如日方中,加上商學院與法律學院不分彼此的經濟學同事,其實力之強史無先例(當年的同事後來有八個拿得諾貝爾獎)。是緊張刺激的學術氣氛,研討會天天有,圖書館好得出奇。雖然是博士後而又轉為助理教授,我在芝大的意識是自己是學生。從早到晚疲於奔命,旁聽呀、研討呀、授課呀、評審呀、寫文章呀,跟著就是晚上的酒會,半醉回到國際學生宿舍,要工作到凌晨三時才睡覺。
在芝加哥的日子中,與我談得最投入的是高斯。我們的興趣相若,而他喜歡先假設一個答案才思考的方法,吸引著我。戴維德與德姆塞茨當時在芝大,六八年艾智仁到那裡造訪一年,而史德拉的研究興趣,有一部分是與今天的新制度經濟學有關的。我當時的研究,是集中於合約選擇與租值消散這兩個題材上。前者我認為是唯一可取的探索企業(或公司)的本質的途徑;後者是產權的問題,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高斯定律。時間沒有白費,我在芝大寫了關於合約的選擇與合約的結構兩篇文章,是比較重要的作品。但當時我日思夜想的關於企業的合約本質,卻要到十四年後才發表。
因為西雅圖的海,六九年我轉到那裡的華盛頓大學。該校的經濟系不知我是何方神聖,從來沒有讀過我的文章,只是聽說一個中國學生聽而不聞,思想怪異,就給我一個副教授,一張終生僱用合約。莫名其妙,只到了那裡三個月,同事們就投票一致通過升我為正教授。我可沒有提出要求。
麥基(J. S. McGee)是華大第一個認為我怪得有理。他是戴維德的嫡傳弟子,是首屈一指的反托拉斯專家。我知道他得到戴老的捆綁銷售的口述真傳,就求教於他。研討了個多小時,他就奔走相告。巴賽爾(Y. Barzel)是收到麥基的廣告才讀我的文章的。
華大的回顧,永遠是巴賽爾的影子。他和我共事十三年,互相影響,我欠他實在多。但他今天成為舉世知名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元老之一,我受聘於華大可能有點作用。我這個人不可救藥,自己有興趣的天天想,說個不停,沒有興趣的我不管。巴賽爾和我合得來,是因為他喜歡聽。我是看著他的臉部表情來衡量自己說的是對還是錯。巴賽爾的思想細緻緊密,不容易過得他那一關。
華大兩年後,我開了一個研討班,是為伸展自己的研究而開的。這班只有十多個學生,其中兩個天分奇高(J. Umbeck與C. Hall)。他們今天還不是大師人物,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在座的還有系主任諾斯(D. C.
North)。加上巴賽爾及麥基等人,華大當年在新制度經濟學上熱鬧過一段日子,使外人後來有間中稱為「華盛頓學派」的。但結果能殺出重圍而名滿天下的,只有諾斯一個。他以新制度經濟學搞歷史而獲得諾貝爾獎。
回頭說六八年在芝大寫好的關於合約選擇的文章內,我提出卸責(shirking)這個概念,是說合約簽訂後雙方都會有不履行或散漫或欺騙對方的意圖,而不同的合約安排會有不同卸責意圖的「邊際」。我不重視這概念,是因為不同的卸責意圖可用不同的交易費用角度來處理。二者只能選其一,二者皆用是重複了。我和高斯研討了好一陣,決定選交易費用而棄卸責。原因是交易費用在原則上比較容易觀察,可以量度,因而有機會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卸責呢?我想不出怎樣量度,想不出有什麼假說可以驗證。但跟著艾智仁與德姆塞茨本著卸責這概念,於一九七二年發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關於經濟組織的文章。是這篇文章觸發了後來以威廉遜(O.
Williamson)為首的機會主義(opportunism)理論及博弈理論的捲土重來。
我不是說人不會卸責,不會勒索、欺騙,或不會看風駛 ,識時務者為俊傑地爭取機會來增加自己的利益。我從來沒有說過人不會博弈。困難是我想不出怎樣可以把卸責或博弈作為理念,而推出一些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來。當年我認為不能;今天還如是看。事實上,我從來沒有見過在這些理念下有學者提供過有說服力的假說驗證。
因為上述的原因,本卷分析的新制度經濟學與他家所說的有好些地方不一樣。雖然這門學問在六十年代興起時,我算是個正選人物,但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我與他家分道揚鑣,一士諤諤,感到寂寞。我是頑固的。我的頑固是因為我堅持如果推不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說得天花亂墜也是白費心思。既然沒有證據經濟學可以改進社會,解釋世事是剩下來的唯一用途了。
究竟新制度經濟學是「新」在哪裡呢?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的。經濟學的傳統分析歷來有兩方面。其一是資源的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其二是收入的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加上貨幣,把一個經濟的整體加起來,就成了宏觀。傳統的制度分析也離不開這兩方面。很不幸,這傳統完全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產權、價格與合約的安排。這樣,不僅舊一套的制度分析與制度無關,而就是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方面,漠視了價格與合約的安排,行為或現象的解釋就不可能有大作為了。不同的產權界定與交易費用會導致不同的安排,而不同的安排會影響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安排就是制度了。選擇安排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全部。這裡說的制度選擇不是說應該怎樣選,而是要解釋不同制度的存在,我們以個人選擇的角度作解釋。
前兩卷對行為的解釋,或明或暗地我都以一些制度的安排為基礎。本卷是回到基礎那方面去。
張五常
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