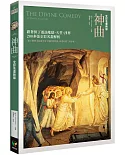英雄一怒為紅顏,沙場百戰萬骨枯:由死地到重生的旅航
劉雪珍
荷馬的兩部史詩《伊里亞德》與《奧德賽》流傳至今,幾乎已成了世界文化的共同遺產。一般讀者對這兩部史詩的名字,或許有些陌生,但如果講起「特洛伊」、「木馬屠城記」或「魔海神航記」,那知道的人,可能就多一些了。奧德修斯設木馬之計攻破特洛伊城,助阿伽門農
和米納雷亞士(Menelaos)的希臘聯軍奪回美人海倫的故事,已成為青少年讀物中不可缺少的材料。至於奧德修斯如何在十年特洛伊戰後,又在海上漂流,浪遊歷險於大小荒島之間;如何與獨眼巨人大戰,設計脫困於重重危險之外,種種航海奇遇,生動有趣,可謂老少咸宜,雅俗共賞,更是世上最佳的冒險故事,開旅行文學之先河。
二○○四年改編自荷馬史詩的電影《特洛伊:木馬屠城》(**Troy**),因有布萊德?彼特(Brad
Pitt)擔綱演出,聲名大噪,掀起一陣希臘神話熱。但是看過《伊里亞德》的豐富,再看《特洛伊:木馬屠城》的單調,任誰也會失落。因為在荷馬的史詩裡,主角不只一人,英雄更不止一個。荷馬史詩向以人神共存的描寫形態著稱於世,天神宙斯(Zeus)在雲端的雷霆,可以瞬間傳達為人間的殺戮征戰;而眾神的人欲,人性的神化,一直在交織中表現出荷馬清晰的人世觀。天神在荷馬的眼中,是力量的代表,是宇宙間冥冥中不可知的一股原動力,可以支配人世的一切。因此,他所創造的神,雖然具有人的形體,及七情六慾,但卻完全免除了人世間的痛苦。因為神不會死亡,所以肉體及精神的折磨與懲罰都變得微不足道,他們日夜宴飲,享樂無窮,絲毫不受倫理道德的束縛。因為一切對神的懲罰都是無關痛癢的,倫理道德的力量當然也就無從建立。
對荷馬來說,人只要小心謹慎地對神獻祭,向神祈禱,就應該得神護佑。如不盡心祭祀,則災禍難免,易遭天罰。除了神祇之外,還有一個介乎神人之間的「命運」在當中運行。對人來說,「命運」是神的一種;對神來說,有時連天神宙斯也要聽從命運的安排。人對未來的預測,要靠神諭、徵兆、夢、先知……等等方式,而且靈驗無比,鮮有失誤。人死之後,一律依照宗教儀式,喪葬掩埋,如不循禮入葬,則靈魂將無所歸,飄流於大地之上,這是絕對不可以的。荷馬的冥府觀念十分簡單,人死之後成為亡靈,鬼魂進入地府,成為一種近乎影子的存在,身材、衣服、面貌都和陽世無異,只是沒有實質,可以飄浮行動,如得飲黑羊之血,便可對人說話。惡人死後,會在冥地之中遭到處罰。
在描寫人物、刻畫個性方面,荷馬多半透過對話、獨白以及行動事件來表達,很少主動站出來做抽象或結論式的說明。因此,他筆下的人物,每個人都有其特殊的個人氣質,很少落入固定的模子或公式。此外,無論是神也好,人也罷,都非常的「人性化」,他們用語高貴、談吐文雅,與一般老百姓的方言俗語很不相同。
荷馬詩中的人物十分重視個人的榮譽,不惜以性命相許,如遭侮辱,必思報復。因此報仇也成為詩中相當重要的主題。阿基利斯為好友帕特洛克羅斯復仇,奧德修斯殺求婚者報仇,都成了兩部史詩中最重要的情節與內容。一個是為朋友,一個是為家人,可見復仇的範圍相當地大。兒子當然要為父母復仇,朋友之間也有替對方報仇雪恥的義務。這對以後的西方文化及文學,都有相當的影響。
《伊里亞德》全篇長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三行,主題在描寫希臘大將阿基利斯之「怒」;所謂英雄一怒為紅顏,沙場百戰萬骨枯,故事中的許多爭端,都是因為一些絕色美女所引起。《伊里亞德》是純粹屬於男人的,而男人在詩中主要的事業就是戰爭。女人在其中僅占從屬地位,命運要靠戰爭的結果而定。荷馬描寫戰爭的筆法冷肅而絕不濫情、準確而觸目驚心。荷馬深知人性深處常常潛藏著「暴力」的傾向,他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公正寫來,正好搔到癢處,十分引人入勝。阿基利斯是荷馬筆下的暴力之神,他不是與敵人作戰,便是與自己作戰,戰爭是他的一切。他拒絕出戰的結果,是朋友遭難,聯軍兵敗,而最後他自己也得賠上性命。
與阿基利斯相反的人物是特洛伊王子海克特。在《伊里亞德》裡,這兩位英雄體現不同的生命情態。海克特代表的是文明,他愛護妻子又效忠國家,嚮往和平但不畏懼戰爭。從某些方面看來,他與《奧德賽》中的奧德修斯在性格上十分相似。他知道戰爭打下去,他注定要犧牲,也必會陣亡,但他卻沒有逃避責任,苟且偷生。甚至對惹起戰爭的海倫,他也沒有惡言相向過。海克特出現時的背景,永遠是文明有禮的,不是神廟宮殿,便是城市家庭。而阿基利斯代表的是暴力,其出現的背景,總是海邊軍營,戰車槍馬。
海克特為了保衛國家、追求和平而犧牲。阿基利斯因喪友之痛,體會生之苦,為帕特洛克羅斯復仇,殺了海克特以後,海克特的父親老王普里阿摩斯(Priamos)不顧自身危險,夜行潛入阿基利斯營帳,乞求帶回海克特的屍體予以埋葬。阿基利斯想起自己的雙親,心中一軟,因而有悟道之舉,答應請求。這顯示出阿基利斯也有追求和平之心。在故事開始的時候,阿伽門農曾試探軍心,宣布願意回家的人可以請便。一時之間,軍中大亂,大家爭先恐後地起錨回航,弄得阿伽門農不得不收回成命。可見所有參戰的兵士骨子裡都是愛好和平、痛恨戰爭的。
這種和平與戰爭、創造與摧毀的兩極現象,在火神為阿基利斯打造的盾牌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在那面金屬鑄造的圓形盾牌上,繪有天、地、海洋、太陽、月亮以及星辰的圖案,還有兩座城市,一為戰爭、死亡、圍城的場面,而另一座城市則有辛勤工作的農人、歡樂跳舞的青年、攻城的兵士,還有打獵的獅子。「大海之河」(the Ocean
Stream)圍繞在盾牌的最外圍,這條河流是活人與死者、陽間與陰界、已知世界與未知世界的分界線。
這面盾牌其實是《伊里亞德》全詩主旨的具體象徵。阿基利斯「悲劇性的憤怒與暴力」在和平與戰爭之間來回擺動,造成了海克特、他自己以及無數生命由陽世轉入陰冥,使千載之後的世世代代,讀罷為之感慨不已。《伊里亞德》以葬禮結束整個故事,再貼切不過!
而《奧德賽》是個冒險故事,善償惡罰,結局圓滿。它講述希臘英雄奧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後回航時所經歷的冒險故事。奧氏的水手在啟程時,得罪了海神,因此全船被罰在海上漂流,將近十年之久,方得回到老家伊薩基(Ithaka)。途中他們經過許多奇異的島嶼,山精妖女、巨人海怪不斷出現,讓讀者目不暇給,過癮非常。論者以為,全詩敘事精整流暢,布局巧妙,行文?熟,可謂西方世界中第一部歷險文學。其中精彩的倒敘(flashback)、戲劇性的高潮、各種人物的穿插,都已達到相當高的藝術水準與控制,結構前後統一,筆法首尾一貫,確乎像是出於一人之口,成於一人之手。
若道《伊里亞德》是戲劇,是古典的悲劇,《奧德賽》則是小說,是浪漫的喜劇,兩者在氣氛、主題上大不相同。《伊里亞德》中的神話故事反映了邁錫尼文化的尾聲,充滿悲傷悼亡之情。《奧德賽》則是各式各樣民間故事的總集匯,充滿了浪漫傳奇,大約是把愛琴海沿岸及大小島嶼上的神話與傳說全都搜羅了過來,然後再由作者一一修正,並以奧德修斯為主角,統領全書。《奧德賽》似乎有意把《伊里亞德》結束後、《奧德賽》開始前這段時間內的重要情節穿插敘述出來。
況且,《伊里亞德》的氣氛肅殺凝重,真可謂達到風雲為之變色、草木為之含悲的地步。其中雖然偶爾穿插輕鬆場面,但全篇主旨在淚不在笑、在悲不在喜,整個故事好像發生在奧林帕斯山頂,冰雪一片,寒風陣陣。《奧德賽》則不然,所有的故事似乎發生在奧林帕斯山腳下,充滿了歷險浪遊氣氛及異國情調。其中雖有奧德修斯探訪地府以求預知未來的穿插,但卻絲毫沒有陰森恐怖之感。眾「死者」全來爭飲羊血,害得奧德修斯還要拔出劍來維持秩序。此時,阿基利斯與大將大埃阿斯(Ajax)也出現了,他們雜在眾「亡靈」當中,不再有領袖群倫的英雄氣概。阿基利斯甚至說出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話來,寧願在世為奴,也不願死為鬼雄或鬼王(King
of all these dead)。《伊里亞德》裡的蓋世英雄,在《奧德賽》變成了尋常戰士。可見前者是莊嚴肅穆的,後者是通俗趣味的。不過在筆法及態度上,兩部史詩都表現出相當一致的貴族觀點,平民在荷馬筆下是較無地位的。
《奧德賽》是西方文學傳統中,王子或英雄在海上陸上冒險浪遊的原型(Hero
archetype),這也就是所謂的「追尋冒險故事」(Quest),其目的在追求人生意義。該書前十二卷寫海上迷航的歷險,後十二卷寫陸上歷險,皆能極盡變化之能事,精彩生動,引人入勝。在希臘人觀念中,英雄要在各種冒險中,才能完成自我磨練,說明自己的能力膽識,贏得當世及後世的尊重與懷念。基本上,《奧德賽》中的英雄保有了《伊里亞德》中英雄的美德,諸如重視個人的光榮、名譽及面子,重視武力及勇氣之發揮,對朋友講道義,對部屬以寬厚,對將領則絕對效忠等等;但《奧德賽》同時還加上了武功以外的美德,例如對家庭及人民負責,對年長的人尊敬,對年輕的人愛護,對客旅、窮人及異邦人要友善接待等等。
在《伊里亞德》中,阿基利斯體魄健美,儀表出眾,氣質高貴,家世不凡。父親是國王,母親是女神,而他自己則是神人的結晶,武功蓋世,集眾美於一身,令人欣羨不已。奧德修斯則沒有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比較起來,他十分接近普通人,身材短小精壯,歲數已入中年,青春不再,貌不驚人。他站在人群中,毫不起眼,但一旦說起話來,卻又精采萬分,動人之至,思想敏銳,字句妥貼,舉座為之傾服,而忘卻其外貌上的短處。他遇事能忍則忍,但若是有關名譽榮辱之事,他也會挺身而出,無懼死亡。在各方面說來,奧德修斯與阿基利斯都代表著兩個極端,一個全力求生,一個視死如歸,一個以喜劇收場,一個以悲劇結束。前者顧家愛鄉,愛妻護子
荷馬開創「歷史小說」的敘事技巧,細節力求吻合故事的年代背景,以便營造「虛擬實境」,主題的呈現卻契合創作的年代,以便「與當代觀眾對話」。在兩部史詩中,荷馬多採客觀描寫的手法陳述事件,對人物的道德、英雄的條件、私行私德高尚清白、家庭生活嚴謹自律等等甚少品評。可是從兩部史詩看來,家庭生活之正常圓滿,實是天下太平的基礎,整個特洛伊戰爭,便是因為美女海倫(克呂泰涅斯特拉〔Klytamnestra〕之妹)不守婦道而引起的,千萬人頭於是落地,英雄豪傑死傷無計。荷馬看出了這一點,也寫出了這一點,不過他卻沒有借題發揮,生出一種「紅顏禍水」或「傾國傾城」的論調。
在《伊里亞德》全書之中,荷馬對海倫無一字褒貶。他只讓海倫在戰事方酣之時出現城頭,眾將士一見之下,驚為天人,大家相互嘆道,為如此美麗的女子打仗,死不足惜。可見在荷馬眼中,美是超乎道德的,為美而死,是正當而值得的。這就是為什麼在特洛伊城被夷為平地後,獨海倫得以安然無恙,隨夫君米納雷亞士安返老家斯巴達享受榮華富貴去了。這故事要發生在中國,一定會落入「宛轉蛾眉馬前死」的下場。由是可知,荷馬對女人、對美,都是既寬大又尊重的。
在《奧德賽》一開始,忒勒瑪科斯去拜訪米納雷亞士,探聽父親的下落,海倫知道了,出來歡迎他。眾人見了她,並無批評或咒罵之心,而她自己在言詞之間,亦無懺悔羞愧之意。凡此種種,都顯示出希臘人對個人道德的尺度與對美的態度。他們很能欣賞珀涅羅珀的貞潔,但卻沒有苛責克呂泰涅斯特拉與海倫姊妹的淫蕩,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愛寬容、對美崇拜的緣故。
談及女性角色,《伊里亞德》裡的女人,如海克特的母親赫卡柏(Hekabe)、其妻安德洛瑪刻(Andromache)、海倫等,都是為了要把戰士的形象烘托得更突出。但是在《奧德賽》裡,女人出現的次數多些,個性各不相同,角色也都舉足輕重,以致有人居然突發奇想,認為其作者為女性。例如諾西卡公主之天真無邪,爽朗大方;珀涅羅珀之貞潔賢淑,柔韌堅毅;卡呂普索之嬌媚誘人,善解人意,願意賜奧德修斯長生不老術;喀耳刻之放肆蠻橫,魔力懾人……等等,都躍然紙上,生動非常。從上述人物性格的刻畫中,我們可以發現,荷馬不但寫其外在的行動,同時也仔細描寫其心理之轉變,角色與角色之間,亦有?心鬥角的內心戲出現,精彩迭出,令後人嘆為觀止。
荷馬企圖把奧德修斯所遊歷的大宇宙與小宇宙相互對比並列。他在海外漫遊,可謂探索了大宇宙之中各種怪誕不經、奇異可怕的荒唐事件。當他回到伊薩基時,那屬於他自己的、現實而日常的生活小宇宙,便展現了出來。奧德修斯不斷地克服那些自然的(怪獸、荒島、大海)及人為的(求親者、無理的侍女)種種困難,最後終於找到了他所想要尋找的自己—─與他的家人重聚團圓。整個故事,象徵著一個漂泊靈魂如何追尋與自己肉體結合的過程。奧德修斯從名滿天下的英雄,一步步地隱藏身分,不單變成了默默無聞的異鄉人,而且還變成了一個人見人嫌的乞丐。他自己從高貴華麗的神話中,走入平凡卑賤的現實裡,而他的兒子忒勒瑪科斯,也從毫無社會經驗、涉世未深的青年,變成了成熟懂事的大人。凡此種種,都顯示出《奧德賽》中的人物性格塑造,是不斷隨環境及事件而發展的。
在《奧德賽》中,人生戰場取代了定點戰場,而「不朽」的意義不再是像阿基利斯那樣追求榮耀,供詩人傳唱,而是父系的承傳。《奧德賽》強調了一家不可無主、一國不可無君的思想。如果我們往深一層檢視,就可發現荷馬認為無主無君會帶來混亂,妻子得不到保護,兒子得不到教育,原有的社會秩序漸漸崩壞,亂臣遂起,整個社稷便要陷入災難,悲劇大禍接踵而至,一不留意,便會遭遇國破家亡之痛。因此,荷馬在此詩中特別強調正義公理,最後獎善罰惡,皆大歡喜。
在這樣的主題下,天上諸神的作用,也比《伊利亞德》裡來得清晰合理。宙斯成了正義公理的象徵,不再受命運女神的支配。波塞頓則代表自然非理性的力量,一再與奧德修斯作對,把他弄得四處漂流。赫耳墨斯(Hermes)只是宙斯的信差,同時也是地府的嚮導。代表智慧勇氣的雅典娜成為《奧德賽》中最重要的神祇,她保護奧德修斯,帶領他抵抗並征服自然力量,並象徵著理智、知識的可貴,她的勇敢、果斷、勤勞、智慧等美德,都一一在奧德修斯身上表現出來,彰顯了人必自助而後天助的真理。
像奧德修斯這樣的英雄,當然會受到無數讀者的歡迎。在西洋文學中,歷來不知有多少作家,以奧德修斯為材料,寫下動人的作品。以現代作家為例,利用奧德修斯神話創作,且能推陳出新名垂不朽的,便是愛爾蘭小說家喬艾斯(James Joyce)。在《尤利西斯》(**Ulysses**)(注1)一書中,他創造了一個主角布魯姆(Leopold
Bloom)作為奧德修斯的化身,寫他於一九○四年六月十六日一天之內在愛爾蘭首府都柏林市中的經歷,其中有幻想、有冥思、有對過去的回憶、有對未來的憧憬,各種外在的經驗,全都被作者融匯成一爐,生動有力地展現在小說之內。奧德修斯是古代英雄,布魯姆卻是現代人中的「反英雄」(anti-hero),他是個平凡的猶太人,是個胸無大志的守法公民,種種行徑,完全與古希臘的英雄相反,形成了古今強烈的對照與反諷,從而發掘出現代文明的缺失及本質。布魯姆與奧德修斯一樣,都是在進行「追尋」,只是前者在現代人生中瑣碎化罷了。
《奧德賽》書中神祇的所作所為,與《伊里亞德》書中的不同,表達出另一種英雄主義及道德觀念。《伊里亞德》則以經過嚴格選擇的場面來呈現詩人所經營的世界,包容性較大,涵蓋的趣味及探討的方向也較具多樣性。
荷馬史詩並沒有告訴世人這世界是為人創造的,也沒有說人在世界上就應該理所當然地快樂幸福,但卻告訴我們這世界可以用人類的方式理解,人類生命是有其尊嚴的,不僅僅是卑微無名地在黑暗中掙扎幾下而已。從兩部史詩中所反映的思想看來,荷馬是一個人本主義者。他對人物的性格描寫入微,對事件的發展刻畫生動;同時,更進一步探討行為的動機、感情的深淺、人物的七情六慾,喜怒哀樂,一一展現在讀者面前。他所創造出來的重要人物,共有四十多位,各有特色,毫無雷同,而這些人物後來都成了西方文學的共同遺產,不斷地在後世的文學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欲窺其中奧妙,就「吟遊一遍荷馬」罷!
注釋1:尤利西斯即奧德修斯,Odysseus 為希臘文,Ulysses 為拉丁文。
(本文作者為輔仁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永恆榮耀的荷馬史詩
翁嘉聲
人類有幸在文學開始之初便有荷馬史詩如此傑出的作品出現,立下文學永恆的典範。在古希臘世界,它的地位宛如基督教的聖經。市民城邦宗教節慶朗誦表演它,教育體制教授傳承它,人們交談時引用它,而史詩中對英雄的願景更塑造了古典社會的價值觀,這些事實使得荷馬史詩成為希臘文明中最具影響力的優勢論述。柏拉圖(Plato)在《理想國》(**Republic**)裡雖然稱讚荷馬是希臘人最早及最偉大的詩人,但荷馬史詩卻因為影響如此之大,所以得在他的理想國裡接受新聞檢查,刪去褻瀆神明或是英雄脆弱等不妥之處。對現代人而言,荷馬也立即呼喚出海倫(Helena)和特洛伊戰爭:「這是那張發動了一千條戰艦的臉嗎?」
欣賞荷馬史詩
許多觀光客從伊斯坦堡大費周章造訪特洛伊遺跡後,一定大失所望,因為除了可看性不高的考古基地外,便是一匹建造不甚精美的木馬。要捕捉荷馬史詩所描述的過往的雄偉及壯麗,閱讀史詩本身似乎是唯一途徑。但是荷馬史詩篇幅甚鉅,描寫細節甚多,特別是人名地名常阻礙瞭解,加上娓娓道來的優雅節奏,必須以悠閒的心態去聆聽欣賞,對想立即知道故事情節並一睹其風采的現代人,往往難以適應。另外,荷馬史詩是希臘神話最重要的根源,所以如果能系統性地預先知道神聖界的結構以及奧林帕斯神明的性質,將更能掌握希臘文化最精華且精采的部分。
萊依(Edgar
Rai)的荷馬史詩介紹對於想知道荷馬,並藉由史詩來接觸希臘文化的讀者,是相當合宜的導讀性作品。他對荷馬研究的立場基本上不脫傳統觀點,認為有荷馬其人,閱歷廣泛,或親自造訪,或訪談目擊人士,然後以優美詩歌唱出寫下。這種觀點是任何接觸荷馬史詩的初步立場,雖然隨著研究,可以進一步發展這些觀點。在介紹奧林帕斯諸神時,作者十分體貼地將希臘文的神名與其拉丁文神名羅列出來,並介紹其特質及事蹟,因為希臘諸神相當人性,一個神一個樣。
史詩的寫作通常是從故事中間插入(**in medias
res**),然後在進行中同時回溯過去及預期未來,往時間軸的兩端同時進行。但是讀者容易因事件的交織而感到困惑,所以萊依先交代特洛伊戰爭發生的原因:一顆刻有「獻給最美麗的女神」的金蘋果。作者交代遠征的前九年過程,直到《伊里亞德》(**Ilias**)中的主要情節「阿基利斯(Achilleus)的憤怒」。從這裡起,作者逐書並細分主題地介紹故事情節,讀來甚為清楚輕鬆,並且在行文之中穿插關鍵原文的翻譯,儘量忠實希臘原著的意義及節奏感,讓人可以感受史詩的氛圍。在「煙飛星散」一小節中,作者談及戰爭的後續發展及結果(《奧德賽》〔**Odyssee**〕中也會提及這些事情)以及英雄返家後的不同命運。後者影射到數個希臘悲劇,這讓人瞭解到由荷馬史詩起頭的希臘神話在古代是個不斷創新的傳統。
萊依所敘述的《奧德賽》在相較之下,相當強調神明對人世的干預,特別是對英雄奧德修斯不友善的海神波塞頓(Poseidon)以及關愛的雅典娜(Athene)。作者所瞭解的奧德修斯有點油腔滑調,但頗能突顯英雄求生存的本能。《奧德賽》與《伊里亞德》形成極大對比:前者在敘述技巧上十分複雜,常常多線發展,然後逐漸收線,而後者則是單線發展,逐漸累聚,終於到達高潮。基本上《奧德賽》是由奧德修斯(Odysseus)冒險返家、其子忒勒瑪科斯(Telemachos)外出詢訪父親下落,以及在家鄉兩人相逢為敘述基軸。作者於是先將奧德修斯的冒險集中起來處理,然後再處理如何返鄉復仇之事。這雖然得之於明確,卻也失去《奧德賽》在結構上的精巧,不過,讀者在閱讀完畢之後,對《奧德賽》的面貌應可有相當掌握。
萊依在處理這兩首史詩時,強調的是面面俱到,所以對一些可以更深入發展的主題往往點到為止。以下我將就作者沒有完全發揮的問題,即荷馬史詩是口述傳統的作品和史詩中的英雄典範及女性加以鋪陳。希望這些討論可以為接受《吟遊一遍荷馬》(**Homer fur Eilige**)的洗禮而轉而閱讀原著的讀者,提供一些思考問題的方向。
口述傳統下的史詩:荷馬是誰?
現在的荷馬研究強調這兩首史詩是口述傳統下的產品,像中古英國《貝爾沃夫》(**Beowulf**)或日爾曼《尼布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有別於羅馬魏吉爾(Virgil)《伊尼爾得》(Aeneid)、中古但丁(Dante)《神曲》(**Divina Commedia**)或密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等的文學史詩。口述傳統所具有的匿名性質使得「荷馬是誰?」的問題複雜許多,甚至令人質疑「作者荷馬」這概念究竟是否合宜。
荷馬史詩如果是口述傳統產物,則這傳統無需文字媒介來傳遞,而史詩的寫定也意謂著口述傳統逐漸消逝。在閱讀《伊里亞德》及《奧德賽》時,可以發現詩人描寫某些對象常有不斷重複的特定詞句。如《伊里亞德》有二十六個地方使用「他對他說出有翼的語言」這樣的「套句語言」,有些時候套句的單位甚至更大更長。傳統的美學一向避免重複、強調創新,但有關荷馬的詩學似乎異於如此。這是因為史詩的創造受到特別的機制所規範。詩人以長短短六音步的特殊詩律為節奏,伴隨樂器,組構這些固定套句來吟唱故事。這種即興吟唱至今仍然可以在一些地方見到。這種創作方式對荷馬史詩之形成及最終產品有強烈的影響。荷馬史詩由於希臘文字的再發明,在八世紀末寫定下來。但當史詩口述傳統仍然存在時,每位吟遊詩人在經過史詩創作機制的訓練及洗禮後,恐怕只需掌握故事輪廓,便可即興吟唱。好的吟遊詩人可以加進自己的潤飾及強調,創造說法獨特的故事。所以史詩的口述傳統意謂著沒有固定的文本,因為每一回表演,正意謂一個新作品的出現,但也僅存在於該場合之中,這使得「作者」的概念變得有些困難。如此的話,詩人的個人履歷便沒有意義。我們不知道荷馬是否為這傳統中最偉大之歌者,但如果是的話,他每一次的表演都將隨著他肉體的消失而消失。《伊里亞德》及《奧德賽》若皆是在口述傳統下的產物,那麼在某種意義上它們是無名、集體的作品。
「狐狸知道許多事,而刺蝟只知道一件」:史詩中不同的英雄典範
荷馬史詩在版本上有高度穩定性。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版本或許與寫定之時的相差不多。《伊里亞德》約有一萬五千六百多行,《奧德賽》約一萬兩千多行,皆分為二十四書。分為二十四書是希臘化時代亞歷山卓學者的貢獻,然而這些不同的書卻代表著獨立的故事情節,適合在晚宴或類似場合作為表演的單位。在主題上,《伊里亞德》環繞在阿基利斯因戰利品(象徵著他的價值及榮耀)被阿加門農剝奪而感到羞辱,憤而退出作戰,造成希臘人不敵等後果,主題十分凝聚。在時間上,《伊里亞德》二書到二十二書只記錄了四天的事情發生經過;加上頭尾,則整個時間僅是數禮拜,但藉由回溯過去以及預示未來而拉長了時間向面。
詩人一開始要求繆斯協助,因為他要吟唱阿基利斯的憤怒以及希臘人因此受苦受難的故事。從二書到四書及最後一書都不斷地預期偉大的阿基利斯終將在得到極大榮耀之後,結束他短暫的生命。在阿基利斯發怒拒戰之後,整個核心轉向希臘人及特洛伊人之間的戰爭;希臘人陸續挫敗,僅靠狄俄墨得斯(Diomedes)及大埃阿斯(Ajax)這些第二線英雄支撐場面。轉捩點出現在十六書:阿基利斯允許他最好的朋友帕特洛克羅斯(Patroklos)穿戴他的裝備武器代戰,導致至交的死亡,於是阿基利斯重回戰場,殺死特洛伊英雄海克特(Hektor)。最後海克特父親普里阿摩斯(Priamos)贖回海克特的屍體,史詩也隨之結束。整首史詩充滿一場又一場的戰役,但是英雄光榮卻短暫的命運正必須依賴戰爭來加以實現。
《伊里亞德》充滿對生命的熱愛;單純的行動及本能被充分地欣賞及享受。在這世界中,男人勇敢,彷彿神明;女人貞潔且美麗;大地豐饒,生生不息。荷馬讓他的英雄如神,而他的神明如人。但較之於神明,荷馬的英雄在兩方面卻有所缺憾:人類會死亡,神明卻永生;人類感受苦難,神明卻是快樂。因此稱呼英雄有如神明時,既真實但也詭弔。生命一方面充滿活力,另方面卻是短暫、必然終結,兩相形成強烈對比,是荷馬史詩中的人類悲劇。《伊里亞德》是首充滿活力的史詩,在其中生命如此充滿活力,所以生命幾乎是所有之事,死亡則一無所有。對曾經生存過的人,死後沒有可期待之事;生命可以十分精彩,並且充分地經驗,但卻必須冒著被殘酷終結的危險。這正是阿基利斯的兩難之處。預言說他的命運是要選擇沒有榮耀的長壽或是充滿光輝的短命,而這正是《伊里亞德》中所有英雄的處境。這種爭取榮耀的急切感與荷馬對人類在這宇宙中的地位及期盼的悲觀看法彼此呼應:
他們如同樹葉,你看那些綠葉,
靠吮吸大地養分片片圓潤壯實,
但一旦生命終止便會枯萎凋零。(二十一書 464-66)
《伊里亞德》大部分的內容都是殺戮,它的效果因詩人的形式主義及寫實主義而受到強化:所有的英雄皆死於戰爭,受戮於其他英雄,絕非由於其他士兵、流箭或傷口惡化而死;所有英雄皆有名有姓,有傑出家世。史詩全心專注於殺戮的事實,著迷於身體的解剖:骨骼被壓碎,軀體被剖開,內臟外流,矛槍由上或從下貫穿。荷馬的寫實及客觀已到達超然的境地,直視死亡而不畏懼,全然地接受它。但什麼是英雄?在十二書中,薩耳珀冬(Sarpedon)之所以冒著喪失所享有的一切的風險而來到特洛伊,只是為了戰鬥而已。他的行徑是位英雄應該有的行徑,而荷馬對他是誰,並不如對他該扮演何種角色來得有興趣。英雄的詭弔,是一個英雄的生命之所以有價值,乃是因為它無所用途,而只是種理想。戰爭所帶來的榮耀與死亡的悲慘醜陋,僅咫尺之遙。一旦選擇榮耀,則僅剩下短暫的生命,一切榮華富貴以及家人親屬已不在心中。
這種僅為個人榮耀及他人對自己觀感的英雄主義,在今天會引起我們的反感,與我們所強調的合作性的道德觀幾乎反其道而行。然而這種對某種理想原始但全心一意的投入,卻有其純粹性及深刻性:戰爭是光榮的,而一位英雄必須作戰來表達其為英雄之偉大。這並非是種自私的意圖,因為假如他能夠永生不朽的話,那他必然會停止戰爭;他作戰時,必須冒著犧牲自己家庭以及所有已取得之成就的風險。這是英雄的悲劇,因為他在表現英雄之偉大時,除了榮耀外,他無法獲得其他之安慰。這種原始及理想化的英雄主義看起來像是一件簡單而只求美感的藝術作品:藝術為藝術而藝術,英雄為英雄而英雄。同樣地,這樣的英雄主義乃根植於對凡人處於這世界之中的蒼涼悲悽看法,以及對來世的無所期望。何以荷馬《伊里亞德》的英雄會如此吸引人,正是由於身處如此充滿敵意的世界中,他們決心留下痕跡。這種對英雄主義的追求,正反映出英雄生命之短暫。就他們而言,所存者僅有「此地」以及「現在」。依如此定義,希臘神明是最「不英雄的」;因為他們永生不朽,所以不必像英雄一般地作為。唯有吟詠英雄榮耀的詩歌,才能將英雄從無名的凡人之中給拯救回來,讓他們永生。
相反地,《奧德賽》貫穿一個很明顯的主題:對「將日常英雄化」(heroization of the ordinary)的歌頌。阿基利斯決定選擇短暫但光榮的生存,可是奧德修斯卻據說在年邁時才安然過逝。為達到這樣的目的,奧德修斯必須展現自己是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