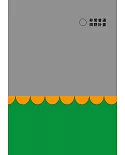前言
我成長於一種混著恐懼與望的奇特氣氛裡,這也是我這一代許多人共有的經驗。這種氣氛承自我們的父母?倖免於難,逃亡,或歐洲移民的猶太人。我們都必須在這兩極之間走出我們的成長之路,一方面設法克服恐懼,一方面為我自己的子女提供希望。本書設法探討的,就是這股奇特的混合情懷。今天,我相信那股混合情懷當時似顯得奇特,因為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確實置身何處:當時我們是否因為某件可怕的事曾經發生?或能發生?而感到害怕呢?當時我們可以期待較美好的事嗎?這兩種情感曾經?而且也許至今仍然?深深地織在我們的生活裡,以致於我們幾乎無法區分兩者。我懷疑這種現象與伴我們大家一起成長的,那種被根拔起的感覺有關。我們並不真的「屬於」新枝幹,但是老枝幹卻已經驟然被截斷。你可以阻止失根感表現得「若」無其事。你也可以接納並設法與之共存。我們是否已把這種失根的情懷延遞給我們自己的女?我們是否已成功地修通這種情懷,或至少已有所認知?這些問題就是本書的焦點。
在我成長期間,我很幸運地擁有祖父母以及一位舅舅和他的家庭。不過,我一直到多年後,在接受精神治療而回想自己的童年時,才知道自己多麼幸運。當時突然出現在腦海的景象是,我們那個德語區的祖輩們定期齊聚在海法喀麥耳山上的一家咖啡館玩牌時,他們所佔用的小桌不會超過兩張,也許只是三張而已。我們那個地區的小孩在成長期間,大都沒有祖父母。他們在六、七歲之前,就已沒有祖父母,或叔伯阿姨,堂表兄弟姊妹。留在納粹德國的那些人,都在所謂的「猶太大屠殺」中被殺害。我父母親那一代成長於一個沒有大屠殺的世界,但是對我們而言卻不可能有那種世界。是否因為有祖父母,才讓我沒有恐懼,讓我不覺得失根?也許在某種程度上真是如此,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沒有他種經驗可以相比較。
在我大約一歲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我最早的記憶之一,大約在三歲左右,我在半夜裡被拉下床,躲到我們在花園裡所挖掘的一個避難處。我如今還聞得到我祖母的灰皮手提袋(後來我聽說她總是把所有的珠寶都裝在這個提袋裡面)。她一定是把提袋拿得跟我的頭差不多高。多年之後,灰色總會讓我嗅到那股特殊的味道。聽人家說,在意大利空襲海法港的煉油廠期間,我總是興高采烈,而且是人人的開心果。但是我只記得每聽到遠方的炸彈爆炸,我就緊抓著祖母的手。
由於我父親當時不在家(他是英國軍隊的一名醫師,駐紮在埃及),因此我經常與祖父消磨時間。我尤其記得他的眼睛,眼神充滿溫暖與真誠。他雖然禿頭(我現在也禿了),但是稍蓄一點八字鬍,而且他還帶著一根美妙的舊手杖,這根手杖如今仍存放在閣樓的某處。我們總會一起散長步,他則邊散步邊說各種故事給我聽。當然是用德語說。我的祖父母都不懂希伯來文。他們在我出生的前兩年才來到海法,是我母親回去德國把他們帶出來的。如果當初她沒這麼做,他們一定像他們同輩的許多人一樣,留下來並慘遭同樣的命運。我祖父是道地的德國愛國者。他曾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認為沒有理由離開家鄉。因此,我是在美妙的德國文化中成長的?德國的語文,音樂,食物,衣著,和傢俱(在一九三三年時,我父母仍然可以帶著傢俱同行)。但是,我也記得我曾在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中聽到希特勒的聲音,他用那種我家人非常喜愛的語言吼叫,家人全聽得嚇呆了。
我想我在那個年紀是無法完全理解的:當德國人是好還是壞呢?是滿懷希望還是充滿恐懼呢?但是,我當時一定已稍微解事,因為數年後我常聽說,我總會在憤怒時刻(我的確偶而會心生憤怒)對著我父母和我哥哥大吼:「你們全都是德國人,我是家中唯一的猶太人」(意思是,我是唯一在以色列出生的人)。然而,在我生命的那個階段裡,幾乎整個社區都是這種猶太裔德國人。我父親從戰爭中回來之後,我們家人在晚餐桌上都用三種語言交談:我父母說德語(或不想讓我們知道時就說英語),我哥哥和我則說希伯來語。
我還聽說我總是獨自一個人在我們那一層狹小的公寓裡玩數個小時,那一棟公寓是德國進口的預鑄銅屋。我常學著我母親在晚上所做的那樣,把房間佈置成一個室內樂的演奏場所。我當時一定已經在她身上感受到對音樂的喜愛以及製造樂聲的強烈慾望,那是她在一個已瘋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方式。到我家來演奏的人,有些是英國人;我家花園的隔壁就是一處英軍營地。對我哥哥和我而言,這處營地一直都是恐懼之源,但是對我母親而言,這一定讓她有安全感。事實上,我父親說服我母親在一九三三年由德國移民至巴勒斯坦的理由,就是「這個地方畢竟是英國的管轄區」。然而,最後把我們趕出家門的,卻是英國人,當時是他們在撤退之前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期間,他們要設立一處集結所有兵力的安全地區。
我們被英國人遷移到德國(互濟會)殖民區中,一棟有大理石地板的石造大房子裡。當時這個地區的居民大都是阿拉伯人,而且就在獨立戰爭爆發之前,我們在那個相當有敵意的社區,是唯一裝有電話的猶太家庭。我記得我們客廳的一景:我母親端茶給英國士兵喝,這些兵都荷著布朗式輕機槍,在我家門外的大街上維持秩序,而在我父親的診所裡,一組「哈佳那」(就是猶太人的自衛隊,當時還是非法組織)則正在開祕密會議並打電話。
我還記得我父母之間的一次討論:我母親想要隨英軍離開。她不信任沒有英國人的中東。我父親因為比較融入新興的以色列社會,所以想留下來。我們也想留下來。這是一個可怕的回憶。只有在回想時,這事才有正面的意義,而且之所以有正面意義,也只是因為他們在我們面前公開談論這些問題。如果他們曾試圖向我們隱瞞他們的情感,疑慮,及對立的意見,事情一定變得很糟。這是當時許多較有「以色列」形象的家庭所發生的現象。但是,由於我當時還是個小孩,因此,這種討論只會讓我更害怕:我們會留下來嗎?我們會離開嗎?置身於那些較「融入」,且全心相信整個現況的人之間,我們到底是誰?在這次討論之後不久,我哥哥和我必須再度疏散,因為阿拉伯的狙擊兵正在射擊我們的房子。不過,這一次在幾天之內,我們就得以重返家門。
在一九四八年的踰越節那一週,海法被解放了。我們可以感受到這次解放所付出的代價。當時有個名叫雅蜜拉的阿拉伯婦女在我家照顧我們並幫我母親操持家事。由於我們當時沒有拿到補給品,因此她總會帶來糖和麵粉。她很親切,我們也都非常愛她。有一天,當我哥哥和我不在時,她含著淚水來到我父母面前,說她的家人即將前往黎巴嫩,因為「他們已打了敗仗」。我父親設法勸她留下,說她會照顧她的家人並讓他們在這個新興的猶太國家裡平安無事。但是,她無法自作決定,而她丈夫不想留下。當時她有六個孩子。他們最後可能就是在南黎巴嫩的難民營裡落腳。數年之後,當我在服役期間被派往北部邊境實行夜間巡邏時,我常想像她的某些孩子也許設法回來從事破壞活動……。
我哥哥當時十六歲,年紀太小而不能參加獨立戰爭。不過,他仍然會把一些與戰爭有關的以色列故事或哥曲帶回家來,而且他還參加童子軍的青年運動,並在服役期間考慮前往某一處集體農場。他在這些事情上為我舖了路,因為我母親一想到以色列文化中那些「尚武的傾向」,就恐懼多過希望。等到他去英國的劍橋攻讀數學之後,她才安下心來;他後來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我則用較認真的態度修習以色列的拓荒課程。我在十六歲時離家,改用一個聽起來像希伯來文的姓,並進入一所農業中學。卡度利農校在早期曾因培養以色列突擊部隊「帕馬克」的領袖人才而頗具聲望。我在生命的那個階段所想要做的,就是擺脫我家那複雜的歐洲傳統,一種我在當時的以色列架構中仍無法找出意義的傳統。我只想變成一個「撒布拉」(就是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我父母早就明說他們不贊成我在謀得一技之長之前就進入集體農場,因此我以智取勝:我變成一個農夫。
那幾年真是美妙的時光。我在一個大都是男孩的青年社會中享受自力更生的自由。我們幾乎在每個空閒的週末都去遠足,而且在徒步中認識加利利地區的每一個角落。這所學校還有一項「榮譽制度」的傳統:老師在考試中並不監考;如果有人企圖作弊而被我們逮個正著,我們就會把他驅逐出校。我們根據一種複雜,但卻人人平等的制度分派工作。我們本來想與附近一所大都是女孩的農業學校聯手,共同在沙漠中建立一座新的集體農場。不過,我們最後卻進入瑞維維姆集體農場;這一座已設立完成的集體農場遠在沙漠之中,當時才剛剛成功地設置一條管線,使加利利海的鮮水可以引流到納格夫?乾旱的南方。這個集體農場為了讓水能做為工業之用,因此需要專業的農夫,我們學校大約有十二個人加入。
我在服完兵役之後,隨即加入。我們在沙漠中栽種一些從來不見於當地的果樹:桃,梨,杏,葡萄,後來還種梨。我們運用鄰近一座集體農場發明並製造的滴水系統,以節省水源。我們設計一種疏開桃樹時可以節省人力的方法。我們還從美國的佛羅里達州及加州走私一些新種果樹。我全神貫注在我的各種活動裡,完全認同正在這行的事:努力工作並期待一個較好,較美的未來。我完全抑制我家庭的過去及其懸而未決的兩難狀況和恐懼。
也許不能算是完全抑制,因為我不管到學校或集體農場,總隨身拖著一把大提琴。我設法繼續學習並演練;這項消遣在當時所瀰漫的拓荒精神裡,雖然引起嘲弄,但卻是我在意識上,唯一能與父母的傳統相互聯繫之處。然而,我在肉體和精神兩方面,都離我父母和哥哥非常遙遠。而我的恐懼已不復存在。至少,我並沒有感受到恐懼,而且我當它已消失了似的。
到了六日戰爭(發生於一九六七年六月?譯註)爆發時,我已結婚並育有一女一子。接著我被徵入一個裝甲師的探路部隊,這個師一路打到蘇伊士運河。其間我喪失一位好朋友,他在同一師的次單位,我們兩人曾在之前的兩年裡共同培植我們的果樹。這場戰爭雖在歡欣的凱旋聲中結束,但是我卻滿懷恐懼地回來。那是我第一次的戰鬥經驗,而且親睹身邊的人被殺死。在那些時刻,生與死純粹訴諸機運。雖然我四周的言論仍然理直氣壯,但是我自己的護盾卻從此開始出現裂痕。我想讀書。我曾考慮讀生物學或心理學,最後選擇後者,但並不完全瞭解何以如此(我們永遠可以知其然,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也知其所以然)。
我個人的全面危機出現在數年後,贖罪日戰爭(發生於一九七三年十月?譯註)爆發之後。我還是在探路部隊,這次是在敘利亞前線,我們試圖解放敘利亞軍隊在此之前所佔領的以色列據點。我記得我曾看到幾名年輕俊美的士兵死在壕溝裡,也記得極度震驚地把一些兵拉出地堡。這一次真的是吃苦受難。當我在六個月的軍旅之後回到家時,整個人變了個樣。我無法適應規律的集體農場生活。我無法與人談論我的戰爭經驗。雖然我被選為集體農場的祕書而且應該設法助人,但是,真正能讓我繼續度日的,卻是我的子女和我極力想完成的碩士學位。在那艱困的幾年之間,處處是恐懼。
我的家庭生活跟著瓦解。於是我進入陸軍待一年,擔任戰地心理學家並開始接受心理治療。這年年底,我父母病了,我哥哥和我就照顧他們。這是我頭一次經歷人生的那個轉捩點?父母無法再照顧你而且你必須開始照顧他們。我父母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接受德國的賠償,自此以後,每年夏天他們都會前往瑞士的則馬特。他們不喜歡在德國旅遊,但是在以色列正當炎夏之際,瑞士的阿爾卑斯山令他們既清爽又輕鬆。也許那是他們「歸根」幻想的實現。那年夏天,由於我們覺得他們無法獨力旅行,因此決定由我和我女兒同行。
我們搭乘一艘豪華的郵輪前往歐洲。我母親在整個航程中,一直極度沮喪;然而,在我們抵達日內瓦的那天晚上,當我父親和女兒都上床之後,她要我陪她沿著湖邊散步。那好像看到花朵在我眼前綻放似的。優雅的瑞士商店,照亮湖邊的老房子,歐洲語言的聲音?我母親突然之間又充滿了生命力。直到那個時候,我才完全領會她那幾年在以色列過日子是怎麼個樣子?歐洲是她的家園,而她隨時都熱心地等待下一次的歐遊。
我們一起度過兩個星期,那對我並不容易。我突然覺得我的某部分感受到我母親所感受的。特別是我們在樹林裡漫步時,我更有這種體認。見識到那些樹林,樹林的氣味和成分時,我有一種最奇怪的感覺;這些東西我在以前雖然一無所知,但並不覺得陌生。
那時候我仍然在接受心理治療,仍然頗受恐懼的支配,但是,漸漸的,希望回來了。我再婚,並且在父親過世不久就添了個兒子。父親是某一年夏天的瑞士之旅中因二度心臟病發而去世。在他逝世之前的兩年裡,我們曾有幾次愉快的交談,我們的談話打破他常有的沉默。我體認到我已繼承了父母親對他們家鄉文化的渴望(父親閉口不談,母親卻明示這種渴望),那種文化早就驟然被截斷。我從反覆的試驗中得知,分離是涉及許多個離去與歸來的一種過程。我開始在歐洲擴展專業領域上的接觸,並且開始定期地前往那裡。一九八五年,我在德國著手進行一項研究計劃:訪問猶太大屠殺納粹執行者的子女(巴旺【D.
Bar-On】,(一九八九)。
在某次研究旅行期間,我母親和我約好在漢堡碰面並帶我去看她的「家鄉」。我們花了兩天的時間沿著幾條運河散步,我們家族有一百多位成員曾在這些運河的所在區域住過。她用一種她論人時所用的譏刺性幽默,不斷地述說多位成員的故事。但是,這對她也是很痛苦的。沒有一扇門可以讓她敲了之後說「嗨,我回來了」,只留下已永遠不再的昔日回憶。一九九二年,我母親以八十五歲之齡逝世於海法。我在醫院陪她度過她生命的最後一個星期。她用英語(生氣時就用此種語言),希伯來語,和德語混著說話。我要安慰她時,就跟她說德語。她去世之後,我就動身前往特拉維夫孩子的住處,臨行前當我鎖上她的公寓房子時,我用淚眼看了那些空房間最後一眼。我覺得我是在為一個永遠不復返的年代關門。
***
七○年代中期,我開始在我們那個地區的集體農場診所當心理治療師,當時的第一位病人是個具有深棕色美目的十三歲男孩,他就是坐在椅子上,一語不發。我不知道做些什麼,於是提議一起散步。我跟我的小兒子就是這麼做:我們邊走邊說話,就像多年前我與我祖父的交談一樣。這個男孩,尼泰,因為父母親不久前的離婚而感到煩惱。我們有數度美好的散步與談話,他的情況「有所改善」,因此我和他的老師都認為他不需要進一步的治療。
數年之後,他的弟弟艾隆也被送到我這裡。他在學校、在家裡都難以管束,而他母親也很擔心他的「情況」。然而,在我跟他談過兩次之後,我覺得他不過是個典型的青少年。由於她母親德芙拉仍然憂心,我就建議她來接受精神治療(也許早在大男孩來找我時,我就該這麼做)。到那時候,我才知道她原來是個猶太大屠殺的生還兒童。她在五歲時,就與母親和哥哥躲到淪陷的法國南方。在德軍佔領後不久,當他們還在巴黎時,她父親「消失」了。
在治療期間,德芙拉才首次試圖澄清她父親到底在何時被帶到奧希維茲並死於毒氣。她父親和母親是在戰爭爆發之前不久離婚的。如此說來,德芙拉小時候曾兩度「失去」父親,先是在離婚,然後又在大屠殺時。初到以色列時,她與一群倖存的法國兒童住在一處以色列集體農場裡,在那幾年之間,她曾企圖自殺,並在第二次自殺未遂之後不久,被送進醫院,但是在醫院作心理治療期間,她幾乎不曾提到猶太大屠殺的事。她的母親和哥哥當時仍住在巴黎,她也偶而去看他們,但是她與他們,尤其是她母親,並沒有維持良好的關係。
我自問,德芙拉在那些年裡?身兼少婦,人妻(至少有那麼幾年),人母,地方上很有能力的化學家,女兒和妹妹,而且從未反省那個過去,以及那個過去與眼前的情感和行為之間的關聯?如何設法讓自己的創傷經驗「正常化」,並在一個非常苛求的社會裡(尤其是在集體農場那種氛圍裡)走出自己的路?我請她就記憶所及,告訴我她小時候避難以及後來初到集體農場那幾年的經歷。在兩年半的時間裡,我們每個星期都會碰面。我們之間的對話非常不尋常,是我從未經歷過的一種對話。她總是努力在找出一個可以談論許多議題的方式,而我則在尋找一個在我自己的參考標架內可以瞭解她的說話內容的方式。我必須依賴她的理路和反應,從而引導她把那些反應化為明確的敘述。
在初期的某一次會面中,德芙拉告訴我一個她所做的夢:夢中,她是個四歲的小孩,穿著一件繡花的白衣,正在聽她父親彈鋼琴(他真的會彈琴)。突然之間,德國兵破門而入,抓走她父親,把她一個人留在那裡。德芙拉此時認為她的悲情與這個夢有關。她想念她父親,他是她孩提時代非常喜愛的人,她希望他有一天會回來,而且她從不放棄這個希望。此時的她充滿恐懼,而且仍然對母親和哥哥深懷內疚(在避難期間他們曾打她,因為她是個調皮且不體諒的女孩,而她不小心的舉動可能會暴露他們的藏匿地點)。
一年之後,德芙拉又做了同樣的夢。然而,這一次,她是從她父親的觀點看到相同的事件?他彈琴取樂,而小女兒就坐在身邊。我注意到這個夢的第二種說法與她當時的狀況有某種關聯。她當時的狀況正穩定地在改善。她比較不那麼擔心她的兒子們,而他們也自在成長。過了不久,我們決定結束治療。
然而,數個月之後,德芙拉又回來了:她第三度做這個夢。這一次,她自己是來帶走她父親的德國士兵之一。依她的看法,這是她頭一次能自覺地對父親生氣,那個離婚時「離她而去」的父親。依據她所說的,她想「在夢中殺死他。」
除此之外,她覺得很好,已決定前往集體農場去追求自己的職業生涯。數天之後,她打電話給我,說她剛記起她與父親的最後一面:他來到母親的住家,但是由於父母之間的緊張關係,他沒說再見就匆匆離去。這通電話之後幾個月,德芙拉又來了,既顫抖又揮淚:她哥哥在毫無先兆的情況下自殺了。在她看來,他一直是理性,沉著一型的人。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完全不知所措。德芙拉本人雖然因他的死而很難度日,但是卻能應付有成?她說,這都是由於她在我們的會面當中有所領悟所致。
如今,我不時總會遇見德芙拉,因為我們住在同一個鎮上。她那個夢已不再出現。我把她那三個夢收錄在《沉默的遺產》(一九八九年)一書裡,出版之前,我把文章拿給她看,她回我一個很大的微笑,用那一口仍然稍帶法語腔的希伯來語說:「丹,事情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的。」
我為德芙拉做心理治療的經驗,促使我開始瞭解一個人要在過去與現在,恐懼與希望之間找出一條路,是何等困難,尤其這個過去如果還包括痛苦的事件或事實時?這些事件或事實雖然永遠無法徹底被驗證,但卻已永遠改變一個人對世間仁義的基本信念以及處世的價值觀(雅諾夫布爾曼︹R.
Janoff-Bulman︺,一九九二)?這條路更難找。一個人在日日夜夜仍受迫於這種心靈創傷之下,如何獨力扶養孩子呢?德芙拉顯然已經盡力而為,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期待她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處理此事。一旦她的孩子開始出現問題,她就需要幫助,以區分她自己的問題和孩子們的問題。她需要再恢復信心,再度相信即使她自己的生活已經被生活歷史中極端艱難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已屬「反常」的情況所扭曲(費爾曼[S.
Felman]與勞伯[D. Laub],一九九二),但是她依然可以為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建立一種正常的生活。我自問,「其他具有類似的生活歷史,而且還沒有一套驗證方法的人,他們如何處理他們的生活(及生活的故事)呢?」
德芙拉那個一再出現的夢促使我在聆聽別人的生活故事時,會更仔細地檢驗「什麼是事實?」這個問題。一個事件當然都有一個「歷史性的」事實(已發生的事),但是還有若干個「敘述性的」事實(一個人述說已發生之事的方式)(司本斯[D.P.
Spence],一九八○)。隨著德芙拉那個夢而產生的各種敘述性事實,可能都關乎她在夢境出現當時的生活實況。當她不再做這個夢時,是否因為「正確的解答」?某一個特殊的記憶?已然浮現?弗里蘭德(Sh.
Friedlander,一九八○)引用馬里內克(Marinek)的話,「有所認知之後,記憶就隨之而來。」將來我們是否「知道」曾經有一個「解答」呢?最後,還有一項後續的證據,那就是數年之後,德芙拉笑著說,「事情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的」。她是什麼意思?她為什麼笑呢?
這些問題的答案在我們聆聽大屠殺生還者的故事時,變得更為複雜。一方面,我們覺得我們沒有領會某種東西:事實上,我們沒經歷過他們之所經歷。另一方面,他們也覺得某種東西遺漏了:很難用日常言語描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思想和語言的實際結構非常脆弱,如果我們試圖在記憶和感覺,以及目前的現況(包括聽者的在場)之間?其間的矛盾常常不只是一方面?搭起一座橋樑,那些結構可以輕易就瓦解。他們怎麼能把自己的恐怖的經驗「翻譯」成普通的話呢?沒經歷過那些事的人,又能從這些敘述裡找出什麼意義呢?他們把這種敘述中的哪部分?如果有的話?延遞給下一代呢?他們因為有新的生活經驗而得以修通什麼呢?
***
我在班古里昂大學所教的一門課是「猶太大屠殺在社會心理上對後代所造成的後作用」。在課程之初,我都要學生先去採訪一位大屠殺生還者的生平,然後寫下來並帶到課堂上。在某一個學期裡,艾拉帶來她祖父的故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不久,就已是波蘭的醫師。當德軍直驅他的鎮內並圍捕猶太人時,他和妻子就把剛生下的女兒交給他以前的一位非猶太病人,自己則躲到游擊隊裡。他擔任游擊隊的醫生,直到戰爭結束。在他們回家之後,那位非猶太婦女不願交還他們的女兒。他們不得不上法庭解決。這個孩子就是艾拉的母親。
在這門課的第二學期剛開始時,我會要求學生去訪問大屠殺生還者的子女。艾拉決定訪問她母親。最後,在課程快結束,而學生也必須完成一項獨立的研究企劃時,她和一位同學訪問了整個家庭:她母親的三位手足,她自己的弟弟(十六歲),以及每一位阿姨和舅舅的長子或長女。這在她來說,不論是訪問內容或針對內容的分析,都是驚人的成就。艾拉和她同學呈現出她祖父的子孫們述說家族歷史的各種方式,有的強調過去的英勇面,有的則著重較痛苦的部分,但是每一個人都從自己目前的觀點去說話。
艾拉的訪問內容激發一個更大的企劃:訪問大屠殺生還者的家族並與每個家族的三代談話。若干年前,我的一群學生曾運用蘿森朵(Gabriele
Rosenthal)所教的一門課的架構,進行這項研究,那門課專門處理傳記與敘述的分析。在針對大屠殺執行者的子女做研究的期間,我就已在德國與蘿森朵碰過面。我在那裡所見過的非猶太人之中,只有少數人馬上就瞭解我正試圖尋找的東西,她就是其中的一位。當時她已發展出一套方法,用以分析她的研究對象;這套方法我雖不熟悉,但我隨即認為非常適用於我的學生極欲瞭解的複雜議題。我們的合作關係就這樣開始。她來到以色列,在我那所大學的行為科學系教授敘述與傳記的分析,並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期間以及一九九三年,針對說德語的大屠殺生還者進行訪問。
我那門課衍出一項團隊工作,而此書就是這項工作的成果。諾嘉吉拉德(Noga Gil\’ad),茱莉夏汀(Julie Chaitin),波絲瑪德維莫卡(Bosmat Dvir-Malka),和艾那懷思(Einat Weiss)全程參與這項企劃。在訪問及初步分析方面,娥瑪莉亞蓋恩(Amaliya Gaon),黛娜瓦第(Dina Vardi),多娃米蘿(Tova
Milo),和雅德娜李懷(Yardena Levi)也加入我們。我要感謝這些人的協助,好奇心,啟發,及助益良多的意見。我還想向蘿森朵教授致謝,她鼓勵我們做下去,並在我們艱難的旅途中一路陪伴我們。蜜莉安凱倫(Miriam Keren)盛情可感,只要我們需要從德文翻譯什麼,她就隨時自願付出時間。
有些讀者也慷慨提供意見和想法;我特別要感謝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利布利克教授(Amiya Lieblich)和洛何美賀蓋托(這個集體農場位於以色列西北亞克港以北四公里處,是二次大戰期間歐洲猶太社區暴動的生還者在一九四九年建立的?譯註)「猶太社區戰士博物館」的茲維德若先生(Zvi Dror)。在編輯階段,班古里昂大學行為科學系的雅奈博士(Nitaza
Yanai)曾提供無可取代的意見和建議。後來,麥克林醫院的阿爾貝克醫師(Joseph Albeck),哈佛大學的賽門教授(Bennett Simon),以及康乃爾大學的佛斯特教授(John Foster)也對本書的初期版本提出深知卓見,是我們在修訂上的一大助力。此外,我還要感謝以德基金會(GIF),特別是會長巴拉克博士(Amnon
Barak),他們提供研究資金,使我們得以進行訪問並處理內容。我也要感謝來自烏林集體農場的茱莉夏汀,她為我們做出優美周到的英文翻譯。最後,我要謝謝我小兒子哈隆和我妻子泰咪的耐心。我常常在他們的故事中缺席,因為我早就深深捲入別的家庭的故事。
在我們的討論即將開始之際,不能不提到撰寫本書的那段期間:波斯灣戰爭。記得有一天,我正設法專心去做某一篇訪問的分析,但卻始終無法從腦海驅除前一天晚上我那九歲兒子的形象:我們坐在密閉的房間裡,他那雙藏在防毒面具後面的驚恐眼睛先看看我,然後看看他母親。那會兒,我不禁要問,我們還要經過多少驚恐的年輕眼睛,才能抵達安全的岸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