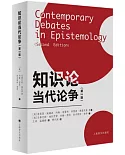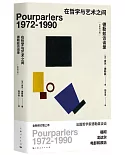尼采是德國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西方許多著名學者如海德格爾、福柯、德勒茲等都曾經對尼采的思想進行過解讀。德里達是法國解構主義大師,當代重要亦受爭議的哲學家之一。
德里達非常重視和欣賞尼采,本書是德里達研究尼采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德里達以其突出的具有原創性的敏銳風格將女性問題與尼采遺留給現代世界的挑戰結合起來,並對之進行了深刻分析,對於我們理解尼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介紹
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國著名哲學家,西方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德里達的思想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掀起了巨大波瀾,成為歐美知識界有爭議性的人物。他的理論動搖了整個傳統人文科學的基礎,也是整個後現代思潮重要的理論源泉之一。主要代表作有《論文字學》(1967)、《聲音與現象》(1967)、《書寫與差異》(1967年)等。
目錄
譯序 /1
弁言:接二連三(Coup Sur Coup) /1
1風格的問題 /21
2距離 /25
3面紗/船帆(Voiles) /37
4真理們 /47
5裝飾 /57
6偽裝 /65
7“謬誤的歷史” /73
8女性生命 /85
9諸立場(Positions) /99
10俄狄浦斯的凝視 /109
11饋贈 /117
12真理的深淵 /129
13“我忘了我的雨傘” /137
14還有一步 /151
附一 /159
附二 /163
弁言:接二連三(Coup Sur Coup) /1
1風格的問題 /21
2距離 /25
3面紗/船帆(Voiles) /37
4真理們 /47
5裝飾 /57
6偽裝 /65
7“謬誤的歷史” /73
8女性生命 /85
9諸立場(Positions) /99
10俄狄浦斯的凝視 /109
11饋贈 /117
12真理的深淵 /129
13“我忘了我的雨傘” /137
14還有一步 /151
附一 /159
附二 /163
序
譯序
正如阿格斯蒂(Agosti)為《馬刺》所寫的導論裡暗示的那樣,應該將德里達的文本保持在分裂、繁殖、解體、交疊的狀態之中,這個狀態通往友誼之未來……
這即是說,德里達與尼采,展開與閉合,我們對此無話可說,但有無盡的書寫,因為他們都交織在當代法國思想之中——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相互回應,我們似乎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試著追蹤德里達論尼采的痕跡。
早在二戰期間的四十年代,巴塔耶就寫作《論尼采》(Sur Nietzsche),並將其置於自己的無神學大全之中。不過,他對尼采的閱讀則始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一同的還有克羅梭夫斯基——他的作品《尼采與惡的迴圈》(Nietzsche et le cercle vicieux)一直要到1969年才出版,比德勒茲的《尼采與哲學》(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晚了整整七年。同一年,布朗肖出版了其理論文集《無盡的談話》(Lentretien infini),在談及虛無主義的反思時討論了尼采。
德里達緊跟其後,從1972年關於尼采的研討會的發言中發展出了《馬刺》這一文本。這是法國人閱讀尼采的歷史,是法國思想家們關於尼采的寫作的歷史。但是,這是何種歷史?德里達的尼采又處於其中什麼樣的位置呢?這是我們追蹤《馬刺》的關鍵,而為了這個關鍵,有必要去繞一下遠路。
在巴塔耶那裡,尼采總是和普遍經濟學因而和耗費、生命、出神(extase)、冒險/賭博(mise en jeu)有著潛在的聯繫。永恆輪回意味著一種永遠求機運(chance)的意志,這個機運處在由人的理性製作的必然性的對面。這個對立同樣出現在巴塔耶闡明其宇宙論的《天體》(Corps célestes)一文中:人類與宇宙的對立。另一方面——而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巴塔耶在討論黑格爾的時候將他放置在了人類知識的那一邊。在巴塔耶看來,黑格爾描述的絕對精神之運動的辯證法不過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是一個通過作為死亡的否定性而達到的歷史之終結。然而,在宏大的宇宙運動中,人類這一渺小的封閉性將會顯得可笑。尼采的意義就此凸顯了出來,雖然他自己並沒有怎麼關注過黑格爾的思想,而馬克思也僅僅只是在他談論末人的時候以社會主義的例子一筆帶過。
也就是說,尼采的意義正在於他提供了一種有別于黑格爾的思想,他提供了無限遊戲、永恆生成和不可能性等維度。究其根本,這一維度建基於尼采對於上帝的判斷(我們此處無需再重複這個著名的判定了)。換言之,上帝的死亡解放了生存的遊戲,我們也就因此可以理解巴塔耶將查拉圖斯特拉看作一個嬉戲者的觀點。同時,這一嬉戲恰恰又應和了巴塔耶自己關於無神的神聖這個觀念。總之,巴塔耶將尼采呈現為一個在虛無主義背景中談論生存問題的思想家。然而,德里達的尼采則是巴塔耶超越黑格爾的那一部分的尼采,即巴塔耶在書寫的狂暴中體驗到的尼采(這一點在下文會再次被觸及)。
克羅梭夫斯基則從另一個角度觸及了巴塔耶的命題,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同德里達產生了聯繫。在區分兩種經濟學的地方,克羅梭夫斯基和巴塔耶十分相似,只不過前者將之命名為宇宙經濟學(léconomie universel)。不同之處在於,在《尼采與惡的迴圈》中,克羅梭夫斯基將尼采早年那種文化類型學式的批判(列出了阿波羅、狄奧尼索斯和蘇格拉底這三種文化本質特徵)劃到一邊,而突出了尼采在希爾斯瑪利亞期間由身體病痛引出的永恆輪回之思想——思想的思想。身體不過只是諸多衝動(impulsion)之偶然彙聚的場所(如《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所言,大腦、意識甚至靈魂不過是身體上的一個部件),因此,作為統一性單元的身體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力量,而力量就是永恆輪回。一切要保存自我的東西在這無限的過程中必然被打破,而只有放棄一切目的(but)與方法(moyen)的宇宙經濟學才是可取的。(這在邏輯上似乎和德里達的延異擁有相似之處:無盡的力量的輪回與碰撞、能指的不斷浮動……)
德勒茲在談論尼采的身體觀時和克羅梭夫斯基是如此接近,但在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接過了巴塔耶的思路。《尼采與哲學》中最引人關注的就是黑格爾和尼采的直接對立。前者的辯證法成了一元論的、靜止的、封閉的形而上學體系,而後者的思想則意味著永恆的生成與遊戲。也就是說,在黑格爾那裡,辯證法的否定性只是為了一個固定的目的、一個終結、一個神,而它的肯定性僅僅是對這一終結的肯定。但是,對於德勒茲來說,尼采的永恆輪回就是生成,其否定性僅在於從它而來的價值重估——用錘子從事哲學,而其肯定性則在於對生成這一無限過程的肯定,是阿裡阿德涅和狄奧尼索斯的愛情。至此,我們發現,德里達的尼采與德勒茲的尼采(雖然二者的理論進路不同),一個通過文本的自我解構,一個通過生成,都向著未來而敞開自己,從而指向了不可能性的維度。
布朗肖則從其寫作觀談論了尼采那個超出形而上學的地方。在他看來,尼采那裡有著兩種策略:第一,將虛無主義的力量發展至極端,那是進行價值設定的超人;第二個策略,則是在這個虛無主義隨著生命的自我克服而終結的系統之外,繼續展開一種碎片的、斷裂的、不斷轉向的書寫。簡言之,尼采之所以不是虛無主義者,是因為他通過被自己稱作思想之頂峰的格言的形式來寫作。這寫作是無盡的、無限的,因而是極端的,因而是將臨的(venir)。德里達肯定了這一寫作觀,也是在這點上,德里達和布朗肖變得極為相似——尼采在這一寫作策略中開始舞蹈、變得輕盈、克服重力。
於是,我們發現,一方面,在閱讀尼采、談論尼采的歷史中,德里達在論及尼采時總是和這一脈絡中的思想家們或多或少有著相似的理論取向,這無疑能夠為《馬刺》中不那麼好把握的內容(文本的拼接、同音異義的語言遊戲等等)有所定向;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在巴塔耶、克羅梭夫斯基、德勒茲、布朗肖談論尼采時,背後總藏著黑格爾,這當然也構成了德里達之尼采的潛在的物件(尤其在德里達討論巴塔耶與黑格爾的那個著名文本中揭露出的一樣)。但問題在於,這是哪個黑格爾?答曰:科耶夫的黑格爾——一種以主奴關係中的死亡與勞作為核心的黑格爾辯證法,伊波利特的黑格爾——一種集中於苦惱意識因而陷入異化困境的悲觀主義的黑格爾辯證法。
二戰過後,法國人將目光投向了黑格爾,以獲得對再次恢復歷史中理性的信心,就像是大革命過後,法國史學將目光投向了歷史本身一樣。而這正是德里達所不贊同的東西。早在《胡塞爾哲學中的發生問題》中,德里達就已經旁敲側擊地質疑了現象學、辯證法與發生之間的關係:他認為,胡塞爾的現象學中實際上只存在一個不斷後撤因而始終隱蔽自身的發生。換言之,黑格爾也是如此,辯證法的綜合總是依賴於對於絕對精神之總體性的預先把握。
因此,值得深思的就是德里達在《書寫與差異》中對巴塔耶提出的命運般的問題——這問題本身也可以看作是德里達對戰後法國哲學提出的問題——黑格爾究竟能否被超越?畢竟,按德里達所言,巴塔耶是一個比他本人所認為的更深刻的黑格爾主義者。
這個問題來自于巴塔耶自己對於僭越的看法:僭越不是虛無主義,而是逼近虛無的極限(《論尼采》),它是反復地在界限上來回,它和界限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神聖(sacré)是異質因素打破日常法則的結果,但不意味著僭越之神聖可以不需要法則。這正是巴塔耶表現出黑格爾主義的地方。但是,德里達依然肯定了巴塔耶關於沉思的方法所提出的那一系列遊戲、舞蹈、迷狂——正是無神學(athéologie)提供了一個溢出封閉性的無限過程。不過,二者的分歧似乎也就在此:巴塔耶認為,僭越和法則的悖論性關係恰恰是笑的可能性,它無時無刻不在敲打日常的邊界,這是嘲笑,這是淚水;德里達則會認為,僭越和法則無非是延異的痕跡,黑格爾的體系也服從於延異本身。但是,無論如何,德里達看到了巴塔耶的無神學那深淵般的否定性,這否定性連否定神學中的那個不斷隱匿自身的神也否定了。這說的是:沒有終結。
而尼采,就因此成了德里達的書寫物件。因為尼采的風格就像一根馬刺(éperon),它是一種擊打(coup),它像匕首一樣鋒利,像羽毛一樣輕盈。不要忘記:尖尖的船頭和馬刺在法語裡是同一個詞——éperon。於是,作為風格的馬刺又是一個深深紮入海洋而破浪的帆船。而風帆(la voile),也是面紗(le voile)。所以,德里達會說,具有馬刺的風格是多變的,它是尖銳的,它是纖長的,它既能穿刺又能格擋,它有時又像一把雨傘。
這一風格就在尼采對女人的討論中得到展現。可以說,尼采的女人,柏拉圖的藥。藥(pharmakon)既是毒藥,也是解藥;女人既是被動的、被征服的物件——真理,也是給予孩子以生命的具有創生力的母親(尼采寫過,一個隻知道戀愛的女人,還有一個則是創造作為創造者的孩子的女人)。換言之,女人自身就蘊含著爆破掉尼采之文本整體(如果說有這麼一個整體性的話)的力量。真理不存在,實際上,女人也不存在。在我們一層層揭開其面紗的時候才發現,遮蔽之下並無面龐。這是獨屬於女人的誘惑與威力,用尼采在《快樂的知識》中的話說,“女性,以及她們在遠處的效果(ihre Wirkung in die Ferne)”。
而困難之處正在於此:女人總是遠離我們。就在我們將其稱作真理的時候,女人以一種更遙遠的方式拒絕了我們,她們壓根就不在形而上學體系之中,哪怕現在,這個形而上學將女人放在一個超驗的位置。因此,德里達才會說“哲學家們既不懂真理也不懂女人”。因為女人實際上根本就不是真理,在她那裡也沒有任何東西被隱藏、被遮蔽。女人只是尼采的風格,是馬刺。或者反過來說更恰當:尼采只是女人的自我書寫,是延異與生成,他向著未來而去……
總而言之,文本崩潰了,但它也因此而獲得其生命。請想一下德里達在和伽達默爾的爭論中提到的東西吧:尼采作為一個簽名意味著什麼?坦白來說,德里達順著內在于尼采文本中的不是概念的概念(如“女人”、“真理”),解構了尼采。於是,尼采不再是海德格爾所判定的西方最後的形而上學家,或者什麼形而上學的終結。情況反倒是這樣:尼采輕輕一躍,他不再是一個談論存在與本質的哲學家,而是分裂為複數的書寫,其中既有批判基督教道德、批判瓦格納的內容,也有在一張褶皺的便條上寫有“我忘了我的雨傘”這樣的碎片。這便是德里達除了尼采本人的文本之外還多次引用了海德格爾的原因,後者基於其存在歷史,將尼采劃歸為從屬於存在論問題的西方思想家(正如在解讀康得和黑格爾的時候一樣,海德格爾認為每個思想家都是基於某種對於存在的理解而開啟自己的思考,尼采也不例外)。
實際上,相反的是,存在(Sein)恰恰要服從於延異,它只是一條痕跡。亦即說,形而上學的話語在馬刺般的風格中破碎。
作者是誰?譯者何人?這並不重要。它並不能中斷無盡的書寫。就讓這一切僅以純粹文本的形式保持、流傳。於是,文本、尼采、德里達,成為一個傷口,一個寫作的黑夜,我們黑夜中的星空。
2018年5月28日
滬上同濟
正如阿格斯蒂(Agosti)為《馬刺》所寫的導論裡暗示的那樣,應該將德里達的文本保持在分裂、繁殖、解體、交疊的狀態之中,這個狀態通往友誼之未來……
這即是說,德里達與尼采,展開與閉合,我們對此無話可說,但有無盡的書寫,因為他們都交織在當代法國思想之中——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相互回應,我們似乎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試著追蹤德里達論尼采的痕跡。
早在二戰期間的四十年代,巴塔耶就寫作《論尼采》(Sur Nietzsche),並將其置於自己的無神學大全之中。不過,他對尼采的閱讀則始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一同的還有克羅梭夫斯基——他的作品《尼采與惡的迴圈》(Nietzsche et le cercle vicieux)一直要到1969年才出版,比德勒茲的《尼采與哲學》(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晚了整整七年。同一年,布朗肖出版了其理論文集《無盡的談話》(Lentretien infini),在談及虛無主義的反思時討論了尼采。
德里達緊跟其後,從1972年關於尼采的研討會的發言中發展出了《馬刺》這一文本。這是法國人閱讀尼采的歷史,是法國思想家們關於尼采的寫作的歷史。但是,這是何種歷史?德里達的尼采又處於其中什麼樣的位置呢?這是我們追蹤《馬刺》的關鍵,而為了這個關鍵,有必要去繞一下遠路。
在巴塔耶那裡,尼采總是和普遍經濟學因而和耗費、生命、出神(extase)、冒險/賭博(mise en jeu)有著潛在的聯繫。永恆輪回意味著一種永遠求機運(chance)的意志,這個機運處在由人的理性製作的必然性的對面。這個對立同樣出現在巴塔耶闡明其宇宙論的《天體》(Corps célestes)一文中:人類與宇宙的對立。另一方面——而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巴塔耶在討論黑格爾的時候將他放置在了人類知識的那一邊。在巴塔耶看來,黑格爾描述的絕對精神之運動的辯證法不過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是一個通過作為死亡的否定性而達到的歷史之終結。然而,在宏大的宇宙運動中,人類這一渺小的封閉性將會顯得可笑。尼采的意義就此凸顯了出來,雖然他自己並沒有怎麼關注過黑格爾的思想,而馬克思也僅僅只是在他談論末人的時候以社會主義的例子一筆帶過。
也就是說,尼采的意義正在於他提供了一種有別于黑格爾的思想,他提供了無限遊戲、永恆生成和不可能性等維度。究其根本,這一維度建基於尼采對於上帝的判斷(我們此處無需再重複這個著名的判定了)。換言之,上帝的死亡解放了生存的遊戲,我們也就因此可以理解巴塔耶將查拉圖斯特拉看作一個嬉戲者的觀點。同時,這一嬉戲恰恰又應和了巴塔耶自己關於無神的神聖這個觀念。總之,巴塔耶將尼采呈現為一個在虛無主義背景中談論生存問題的思想家。然而,德里達的尼采則是巴塔耶超越黑格爾的那一部分的尼采,即巴塔耶在書寫的狂暴中體驗到的尼采(這一點在下文會再次被觸及)。
克羅梭夫斯基則從另一個角度觸及了巴塔耶的命題,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同德里達產生了聯繫。在區分兩種經濟學的地方,克羅梭夫斯基和巴塔耶十分相似,只不過前者將之命名為宇宙經濟學(léconomie universel)。不同之處在於,在《尼采與惡的迴圈》中,克羅梭夫斯基將尼采早年那種文化類型學式的批判(列出了阿波羅、狄奧尼索斯和蘇格拉底這三種文化本質特徵)劃到一邊,而突出了尼采在希爾斯瑪利亞期間由身體病痛引出的永恆輪回之思想——思想的思想。身體不過只是諸多衝動(impulsion)之偶然彙聚的場所(如《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所言,大腦、意識甚至靈魂不過是身體上的一個部件),因此,作為統一性單元的身體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力量,而力量就是永恆輪回。一切要保存自我的東西在這無限的過程中必然被打破,而只有放棄一切目的(but)與方法(moyen)的宇宙經濟學才是可取的。(這在邏輯上似乎和德里達的延異擁有相似之處:無盡的力量的輪回與碰撞、能指的不斷浮動……)
德勒茲在談論尼采的身體觀時和克羅梭夫斯基是如此接近,但在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接過了巴塔耶的思路。《尼采與哲學》中最引人關注的就是黑格爾和尼采的直接對立。前者的辯證法成了一元論的、靜止的、封閉的形而上學體系,而後者的思想則意味著永恆的生成與遊戲。也就是說,在黑格爾那裡,辯證法的否定性只是為了一個固定的目的、一個終結、一個神,而它的肯定性僅僅是對這一終結的肯定。但是,對於德勒茲來說,尼采的永恆輪回就是生成,其否定性僅在於從它而來的價值重估——用錘子從事哲學,而其肯定性則在於對生成這一無限過程的肯定,是阿裡阿德涅和狄奧尼索斯的愛情。至此,我們發現,德里達的尼采與德勒茲的尼采(雖然二者的理論進路不同),一個通過文本的自我解構,一個通過生成,都向著未來而敞開自己,從而指向了不可能性的維度。
布朗肖則從其寫作觀談論了尼采那個超出形而上學的地方。在他看來,尼采那裡有著兩種策略:第一,將虛無主義的力量發展至極端,那是進行價值設定的超人;第二個策略,則是在這個虛無主義隨著生命的自我克服而終結的系統之外,繼續展開一種碎片的、斷裂的、不斷轉向的書寫。簡言之,尼采之所以不是虛無主義者,是因為他通過被自己稱作思想之頂峰的格言的形式來寫作。這寫作是無盡的、無限的,因而是極端的,因而是將臨的(venir)。德里達肯定了這一寫作觀,也是在這點上,德里達和布朗肖變得極為相似——尼采在這一寫作策略中開始舞蹈、變得輕盈、克服重力。
於是,我們發現,一方面,在閱讀尼采、談論尼采的歷史中,德里達在論及尼采時總是和這一脈絡中的思想家們或多或少有著相似的理論取向,這無疑能夠為《馬刺》中不那麼好把握的內容(文本的拼接、同音異義的語言遊戲等等)有所定向;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在巴塔耶、克羅梭夫斯基、德勒茲、布朗肖談論尼采時,背後總藏著黑格爾,這當然也構成了德里達之尼采的潛在的物件(尤其在德里達討論巴塔耶與黑格爾的那個著名文本中揭露出的一樣)。但問題在於,這是哪個黑格爾?答曰:科耶夫的黑格爾——一種以主奴關係中的死亡與勞作為核心的黑格爾辯證法,伊波利特的黑格爾——一種集中於苦惱意識因而陷入異化困境的悲觀主義的黑格爾辯證法。
二戰過後,法國人將目光投向了黑格爾,以獲得對再次恢復歷史中理性的信心,就像是大革命過後,法國史學將目光投向了歷史本身一樣。而這正是德里達所不贊同的東西。早在《胡塞爾哲學中的發生問題》中,德里達就已經旁敲側擊地質疑了現象學、辯證法與發生之間的關係:他認為,胡塞爾的現象學中實際上只存在一個不斷後撤因而始終隱蔽自身的發生。換言之,黑格爾也是如此,辯證法的綜合總是依賴於對於絕對精神之總體性的預先把握。
因此,值得深思的就是德里達在《書寫與差異》中對巴塔耶提出的命運般的問題——這問題本身也可以看作是德里達對戰後法國哲學提出的問題——黑格爾究竟能否被超越?畢竟,按德里達所言,巴塔耶是一個比他本人所認為的更深刻的黑格爾主義者。
這個問題來自于巴塔耶自己對於僭越的看法:僭越不是虛無主義,而是逼近虛無的極限(《論尼采》),它是反復地在界限上來回,它和界限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神聖(sacré)是異質因素打破日常法則的結果,但不意味著僭越之神聖可以不需要法則。這正是巴塔耶表現出黑格爾主義的地方。但是,德里達依然肯定了巴塔耶關於沉思的方法所提出的那一系列遊戲、舞蹈、迷狂——正是無神學(athéologie)提供了一個溢出封閉性的無限過程。不過,二者的分歧似乎也就在此:巴塔耶認為,僭越和法則的悖論性關係恰恰是笑的可能性,它無時無刻不在敲打日常的邊界,這是嘲笑,這是淚水;德里達則會認為,僭越和法則無非是延異的痕跡,黑格爾的體系也服從於延異本身。但是,無論如何,德里達看到了巴塔耶的無神學那深淵般的否定性,這否定性連否定神學中的那個不斷隱匿自身的神也否定了。這說的是:沒有終結。
而尼采,就因此成了德里達的書寫物件。因為尼采的風格就像一根馬刺(éperon),它是一種擊打(coup),它像匕首一樣鋒利,像羽毛一樣輕盈。不要忘記:尖尖的船頭和馬刺在法語裡是同一個詞——éperon。於是,作為風格的馬刺又是一個深深紮入海洋而破浪的帆船。而風帆(la voile),也是面紗(le voile)。所以,德里達會說,具有馬刺的風格是多變的,它是尖銳的,它是纖長的,它既能穿刺又能格擋,它有時又像一把雨傘。
這一風格就在尼采對女人的討論中得到展現。可以說,尼采的女人,柏拉圖的藥。藥(pharmakon)既是毒藥,也是解藥;女人既是被動的、被征服的物件——真理,也是給予孩子以生命的具有創生力的母親(尼采寫過,一個隻知道戀愛的女人,還有一個則是創造作為創造者的孩子的女人)。換言之,女人自身就蘊含著爆破掉尼采之文本整體(如果說有這麼一個整體性的話)的力量。真理不存在,實際上,女人也不存在。在我們一層層揭開其面紗的時候才發現,遮蔽之下並無面龐。這是獨屬於女人的誘惑與威力,用尼采在《快樂的知識》中的話說,“女性,以及她們在遠處的效果(ihre Wirkung in die Ferne)”。
而困難之處正在於此:女人總是遠離我們。就在我們將其稱作真理的時候,女人以一種更遙遠的方式拒絕了我們,她們壓根就不在形而上學體系之中,哪怕現在,這個形而上學將女人放在一個超驗的位置。因此,德里達才會說“哲學家們既不懂真理也不懂女人”。因為女人實際上根本就不是真理,在她那裡也沒有任何東西被隱藏、被遮蔽。女人只是尼采的風格,是馬刺。或者反過來說更恰當:尼采只是女人的自我書寫,是延異與生成,他向著未來而去……
總而言之,文本崩潰了,但它也因此而獲得其生命。請想一下德里達在和伽達默爾的爭論中提到的東西吧:尼采作為一個簽名意味著什麼?坦白來說,德里達順著內在于尼采文本中的不是概念的概念(如“女人”、“真理”),解構了尼采。於是,尼采不再是海德格爾所判定的西方最後的形而上學家,或者什麼形而上學的終結。情況反倒是這樣:尼采輕輕一躍,他不再是一個談論存在與本質的哲學家,而是分裂為複數的書寫,其中既有批判基督教道德、批判瓦格納的內容,也有在一張褶皺的便條上寫有“我忘了我的雨傘”這樣的碎片。這便是德里達除了尼采本人的文本之外還多次引用了海德格爾的原因,後者基於其存在歷史,將尼采劃歸為從屬於存在論問題的西方思想家(正如在解讀康得和黑格爾的時候一樣,海德格爾認為每個思想家都是基於某種對於存在的理解而開啟自己的思考,尼采也不例外)。
實際上,相反的是,存在(Sein)恰恰要服從於延異,它只是一條痕跡。亦即說,形而上學的話語在馬刺般的風格中破碎。
作者是誰?譯者何人?這並不重要。它並不能中斷無盡的書寫。就讓這一切僅以純粹文本的形式保持、流傳。於是,文本、尼采、德里達,成為一個傷口,一個寫作的黑夜,我們黑夜中的星空。
2018年5月28日
滬上同濟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