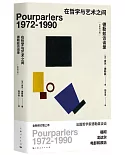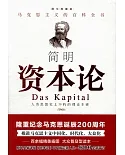北歐、肥腴月灣、愛琴海沿岸、尼羅河畔……凡是神話發達的地方都流傳著一則類似的神話故事,雖然情節各依地理風貌和民族想像變化多致——有一位神,死了,卻又復活;他的死給大地帶來新的生機。
C.S.路易士借用“丘比特和賽姬”故事演繹的神話小說,其中不但有與基督信仰基石相合的寓意,更在於把教義化了的信仰還原為耐人尋味、需要人用心靈加以體會的神話。
作者介紹
C.S.路易士(1898-1963),是20世紀英國的天才作家。他26歲即登牛津大學教席,被當代人譽為“最偉大的牛津人”。1954年,他被劍橋大學聘為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英語文學教授,這個頭銜保持到他退休。
他的一生完成了三類很不相同的事業,被稱為“三個C.S.路易士”:一是傑出的牛津劍橋大學文學史家和批評家,代表作包括《牛津英國文學史?16世紀卷》。二是深受歡迎的科幻作家和兒童文學作家,代表作包括“《太空》三部曲”和“《納尼亞傳奇》七部曲”。三是通俗的基督教神學家和演說家,代表作包括《返璞歸真》、《四種愛》、《天路回歸》、《魔鬼家書》(亦作《地獄來信》)等。
他的一生完成了三類很不相同的事業,被稱為“三個C.S.路易士”:一是傑出的牛津劍橋大學文學史家和批評家,代表作包括《牛津英國文學史?16世紀卷》。二是深受歡迎的科幻作家和兒童文學作家,代表作包括“《太空》三部曲”和“《納尼亞傳奇》七部曲”。三是通俗的基督教神學家和演說家,代表作包括《返璞歸真》、《四種愛》、《天路回歸》、《魔鬼家書》(亦作《地獄來信》)等。
序
托夢--夢覺邊緣的啟示
囡囡
我的星星
你靜靜凝視著群星
多麼希望我就是那夜空
也凝視你,以千萬顆眼睛
--柏拉圖情詩
北歐、肥腴月灣、愛琴海沿岸、尼羅河畔……凡是神話發達的地方都流傳著一則類似的故事,雖然情節各異,地理風貌和民族想像變化多致--有一位神,他死了,卻又再生復活;他的死給大地帶來新的生機。在牛津教授古典文學的年輕學者C.S.路易士,將這些神話玩味再三,仿佛聽見上帝要傳遞給人類“道成肉身”的中心資訊,亙古以來,反復沿著人類意識的幽峽不斷回蕩。他得出一個結論:原來,神借著各族神話,托夢給人類,作為信仰奧義的先聲。換句話說,當基督從死裡復活時,許多民族共有的神話成了事實,人的夢境成真了。面對這樣偉大的神跡,路易士以擲地有聲的文字,為我們揭示出這一神跡的歷史意義,給歐美知識界造成很大震撼。
基督教的核心是一則變成事實的神話,那則關於一位死去了的神的古老神話,從傳說和想像的天國裡,下降到地上的歷史中來(卻仍保留著神話的色彩)。這件事發生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並在歷史中造成清晰可辨的影響,使我們超越了無人知道死於何時何地的……異教神話,臻入一位在彼拉多手裡被釘死的歷史人物。見於“神話變成事實”(1944)一文。
的確,基督從死裡復活,顯明他是神進入人類的歷史,為要完成人的救贖--這“道成肉身”的神跡,超越了神話,使神話變成事實;但是,另一方面,路易士提醒我們:
這則神話變成事實之後,並非就不再成其為神話,這就是一種奇跡了。……若想做個真正的基督徒,我們就必須一方面同意上述的歷史事實,一方面用欣賞一切神話所需要的想像力,接受其中所含的神話成分(雖然它已成為事實);這兩者同等重要。……基督教神學中閃耀著神話的光輝……見於“神話變成事實”(1944)一文。
正因“道成肉身”擁有神話的特質,對其中所蘊含的啟示要能充分領悟,人必須在理性的認知之外,馳騁想像,深入體會,讓終極真理具象地映現在知感全域。這項努力,單靠神學的演繹、教義的講述,容易流於空疏。或許基於這種認識,路易士在寫完一系列成功的思想作品,並以犀利的言論、深刻的文化省思,向崇尚理性思考的20世紀人透徹剖析基督教的可信之後,便專心致力於虛構文學的創作,成果包括三本幻遊小說、童話故事集《納尼亞傳奇》和取材自希臘神話的《裸顏》。如果說路易士的思想作品拭除了人的“理性障蔽”,讓人能透過清晰的思考,賞識基督教適應人心需要又與真理相合的本質,那麼,他的虛構作品則可以進一步蕩滌人的情性,激發神思、想像,藉著具體的情節,引導讀者入窺救贖的境界。其中又以《裸顏》這一部恰以“死而重生”為主題的神話小說,最能全面反映他的救贖神學、宗教視野和藝術成就。
他的摯友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認為《裸顏》與《人的絕滅》(The Abolition of Men)堪稱路作雙璧;歐文·巴菲爾德是路易士在牛津時的前期學長,路氏稱他為“在我非正式的師長中,最睿智、傑出的一位”。自牛津畢業後,巴氏續承父業,在倫敦從事圖書代理業務,後來替路氏處理與版稅有關的法律事務。退休後應聘往美國大學講授英國文學,有關詩歌用語及文學想像的論述頗受學界推崇。他與路易士的友誼被譽為20世紀文學交遊中的典範之一。所指譽詞見於《光照路易士》(Light on C. S. Lewis)之序,收錄於1989年出版之《歐文·巴菲爾德論路易士》(Owen Barfield on C. S. Lewis)一書第29頁。批評家也大致同意路氏自己的看法:在他所有的虛構作品中,《裸顏》寫得最精湛、細膩。更有學者以專書說明《裸顏》如何解開理性與想像的糾結,為西方讀者提供睿智的指引。見彼得·薛柯(Peter J. Schakel)所著《路易士作品理性和想像的關係:〈裸顏〉析讀》(Reason and Imagination:On C. S. Lewis - A Study of Till We Have Faces,1984)。許多人從《裸顏》中見識到路氏直追現代小說經典的敘事藝術,紛紛為他的早逝(65歲)歎惋不已,甚至說:“他應該早點寫小說。”
那麼,面對路易士這部寓意深刻的神話小說《裸顏》,我們應該怎樣讀它呢?1936年,38歲的路易士出版《愛的寓言》(The Allegory of Love),探討中古俠義愛情的源流,旁徵博引,立論精闢,奠定了他對寓言研究的學術地位。拉丁詩人筆下的賽姬,被父王遵照阿波羅神諭,“暴陳山巔,供龍攫食”,與初民社會“代罪羔羊”式的獻祭,並無關涉;但是,路易士借用古典神話,刻意把賽姬(伊思陀)塑造成一位“基督型”的人物。由於她超凡的美麗和善良,當國中遭遇瘟疫時,人們交口相傳:經她的手一觸摸,癘疾可得痊癒。於是,民眾把她當作女神膜拜。
這一風潮觸怒了當地主神安姬的祭司,藉口她是引發“天譴”的因由,認為若要拔除饑饉、瘟疫、兵燹的多重禍害,必須將她獻祭,綁在陰山頂的一株聖樹上,作為山神的新娘。對這一犧牲的角色,賽姬坦然接受,一方面固然有“一人死萬人活”替百姓受難的壯烈情懷,另一方面更為了因此便能實現自己多年來的憧憬--與陰山所象徵的生命本源合而為一--內心欣喜莫名。外表看來,整樁獻祭的事件原是一出政教鬥爭的荒謬劇,對她而言,卻宛似一趟歸程,帶她回到那自己靈魂久已嚮往的“宮堡”。就這樣,借著“故事新詮”,路易士賦予賽姬的神話一道與基督教信仰遙相呼應的寓言含義,儼然以實際的神話擬構宣示他的前述理念--神話傳說原是神向人類托夢,其中隱含真實信仰的影子。循著這條線索讀《裸顏》,它簡直就是一部扎實的啟示性著作。
萬象紛呈,人世無常,任何時空的人類,為了認知及求生,往往需要信靠宗教。同樣的需求投射在不同的祭典和信仰中(“安姬有一千種面目”)。路易士透過葛羅人的信仰(崇奉性愛與生殖的女神安姬--與希臘的阿芙洛狄忒、羅馬的維納斯同屬地母型神祇),刻畫了一切宗教共有的現象,包括儀式的意義、獻祭的動機、神話的形成、政教的衝突、信仰給人性帶來的昇華等等,甚至不避諱初民用以禱求豐收的淫祀。此外,更重要的,他為葛羅這個蠻荒小國設計了獨特的時空背景,把它放置在小亞細亞邊陲,黑海附近,未受古典文明薰陶的地域;又讓故事發生在蘇格拉底亡故和耶穌基督誕生之間,也就是希臘理性文明逐漸往周圍世界傳佈的時候。
路易士發揮歷史的想像,塑造了這個半開化的國度,既合史實又富於象徵。他用這樣一個正逢野蠻與文明交接的社會為背景,借著當地原始信仰與理性主義間的彼此激蕩(大祭司和“狐”之間的辯論),化衝突為和諧,經由故事講述者奧璐兒女王終其畢生上下求索,把比這兩者更充分的啟示勾勒了出來--也就是一個既能滿足古代宗教信仰的獻祭要求,又能符合希臘理性主義竭智追求之倫理目標的宗教。從“漸進啟示”的史觀看,這樣的宗教正是最純全的宗教,它包含了一切信仰追尋的JIZHI。當然,它遙遙指向那不久即將進入人類歷史,由道成肉身的神,替人流血犧牲,又從死裡復活,把得贖重生的生命境界向人開啟。路易士稱這為真實的信仰,並在一篇論述文字中,辨析如下:
它完全合乎倫理,卻又超越倫理;古代宗教共有的那種獻祭與重生的主題,以不違逆--甚至超越--良知與理性的方式再度出現。在這當中,WEIYI的真神自顯為永活的造物者,超絕於萬物之外,卻又居攝其中。這樣的一位神不僅是哲學家的神,也是奧秘派和野蠻人的神,他不僅滿足人的理智和情感,更且照顧了各樣原始的衝動,以及超拔在這些衝動之外卓犖如山的一切屬靈憧憬。
《裸顏》可說是上述識見的戲劇化呈現,特別落筆從懵懂進入醒悟之前,所謂夢覺邊緣(half awakening)的信仰追求。
但是,《裸顏》之撼人心弦,並不僅在於隨情節的進展,披露在讀者眼前那逐漸開闊、深邃、清朗的神聖視野。真正令人感動的,是奧璐兒女王這個容貌奇醜、智慧超群、身手矯健,不讓鬚眉的女人--她的情感起伏,她對生命真相鍥而不捨的尋索,及至暮年的覺悟和蛻變--換句話說,她個人靈魂的掙扎、自剖與重生,才是這部小說的主題。賽姬的神話原本就是一則人神相戀的故事,更因賽姬(Psyche)意為“靈魂”,自古以來,這則神話始終發人深省,人們反復推敲其中的寓意,覺得它所反映的正是靈魂對神性(divine nature)的嚮往與渴慕,而賽姬被逐出神宮後的受難過程,恰好象徵靈魂與神合一之前必需經歷的重重考驗。其中,知性的磨煉(穀種分類的寓喻)只算是最初步的功課。
路易士套用這則神話作為《裸顏》的基本情節,所要刻畫的正是靈魂與神複合的經過。這當然是基督教信仰的主要內容之一,而仔細端詳奧璐兒的悟道過程--從驚覺自己原來也是安姬(不只容顏,連靈魂也一樣醜陋--貪婪、自私、善妒……),繼而體會出道德修養對改善安姬似的靈魂其實毫無作用,至終於蛻變成賽姬(當賽姬通過考驗與神複合的刹那,也就是奧璐兒變顏得榮的時刻,因為多年來,在現實世界,奧璐兒挨忍著對賽姬的思念,焚膏繼晷攝理國政,包括最後的著書申訴,其艱巨程度與考驗性質,絕不亞于賽姬為要贖回神的眷愛所需完成的各樣超凡任務。女王奧璐兒的生活與被逐的賽姬其實沒有兩樣,等於在替賽姬分勞。原來,神對奧璐兒所說的預言--“你也將成為賽姬”--背後隱藏著一道屬靈的奧秘:根據“替代”的原理,生命在愛中融匯交流,能夠彼此分擔痛苦、共用成果,在真實的人生中,路易士本人曾經具體地經歷“替代”的奧秘。
不忍見所愛的妻子受骨癌折磨,他禱告神讓自己承擔她的痛苦。果然,“喬伊”(路夫人名為Joy)痛苦減輕,路氏自己卻罹腳疾,醫生診斷病因:“缺乏鈣質。”就像狐所說的,是奧璐兒承擔苦楚,而由賽姬完成工作)--這樣的悟道過程隱約含有基督教信仰的痕跡,尤其吻合原罪與靠十架救恩使靈魂得贖(神“替”人死,“代”人償付罪責),而人得救之後應與基督同背十字架的奧義。
路易士刻畫奧璐兒個人的悟道所採用的筆法仍是先前所提到的:透過古代神話勾勒在夢覺邊緣呼之欲出的啟示。書中的這段句子“在未來遙遠的那一天,當諸神變得全然美麗,或者,當我們終於悟覺,原來,他們一向如此美麗……”讀來恰似舊約中的預言“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耶利米書》31∶31)、“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以西結書》36∶26)。從釋經學的角度看,路易士對古典神話“故事新詮”的寓喻讀法,十分近似基督教傳統的“預表”解經法。依一般解釋學的說法,這種舊文衍生新義的現象,其實便是“先前發生的事件,事後看來,會產生比事發當時所能領悟的更為充分的義理”見雅歌出版社出版路氏論《詩篇》的中譯《詩篇擷思》(Reflection on the Psalms)第10章。
狐的幽靈在異象中對奧璐兒所說的“神聖的大自然能改變過去,尚無一事物是以它真實的面目存在著”,指的就是類似的事。當充分啟示的亮光一出現,許多事物真實的面貌便顯現出來,這是《裸顏》的中心思想,也是《裸顏》的敘事技巧。就奧璐兒而言,這件事發生在她透過理性與神抗辯到底,卻不知不覺揭開自己靈魂面紗的刹那。真切的自我認識與認識神是同時發生的。這樣看來,形式與內容的有機結合在這本小說中可說達到極圓融的地步,所以,對這本小說非常激賞的歐文·巴菲爾德特別提醒讀者,千萬別把它當作純粹的寓言讀,它其實是“一部把創作神話的想像發揮到JIZHI所寫成的作品”。的確,讀《裸顏》若僅止于從中捕捉與教義相合的寓意,進而揣摩大師如何移花接木,巧借賽姬神話架構“現代福音”,這種寓喻式的讀法雖然有趣,卻辜負了路易士的創作原旨,因為他的目的不在於把賽姬神話淡化為教義,而在把被教義化了的信仰還原為耐人尋味、需要人用心靈加以體會的神話。
路易士在《文藝評論的實驗》--一本討論如何辨別好書、壞書的著作中,這樣推許閱讀的功能:
文學經驗療治傷口,卻不會剝奪個人擁有個體性的權利。有些在聚會中感染到的群體情緒也可以療傷,但往往會使個體性遭到破壞。在群體情緒中,不同個體原本分隔的自我融匯合流,我們全都沉浸回到無我(自我未產生前)的境界中。但在閱讀偉大的文學作品時,我則變成一千個人,卻仍然保有我的自己。這就像希臘詩中所描寫的夜空,我以千萬顆眼睛覽照萬象,但那用心諦視的仍是我這個人。在這裡面,就像在崇拜中、在戀愛中、在將道德付諸行動中和在認知中一樣,我超越了自己,卻也從未這樣實現自己。
但願讀者在閱讀《裸顏》時,有同樣的感受。
--曾珍珍
囡囡
我的星星
你靜靜凝視著群星
多麼希望我就是那夜空
也凝視你,以千萬顆眼睛
--柏拉圖情詩
北歐、肥腴月灣、愛琴海沿岸、尼羅河畔……凡是神話發達的地方都流傳著一則類似的故事,雖然情節各異,地理風貌和民族想像變化多致--有一位神,他死了,卻又再生復活;他的死給大地帶來新的生機。在牛津教授古典文學的年輕學者C.S.路易士,將這些神話玩味再三,仿佛聽見上帝要傳遞給人類“道成肉身”的中心資訊,亙古以來,反復沿著人類意識的幽峽不斷回蕩。他得出一個結論:原來,神借著各族神話,托夢給人類,作為信仰奧義的先聲。換句話說,當基督從死裡復活時,許多民族共有的神話成了事實,人的夢境成真了。面對這樣偉大的神跡,路易士以擲地有聲的文字,為我們揭示出這一神跡的歷史意義,給歐美知識界造成很大震撼。
基督教的核心是一則變成事實的神話,那則關於一位死去了的神的古老神話,從傳說和想像的天國裡,下降到地上的歷史中來(卻仍保留著神話的色彩)。這件事發生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並在歷史中造成清晰可辨的影響,使我們超越了無人知道死於何時何地的……異教神話,臻入一位在彼拉多手裡被釘死的歷史人物。見於“神話變成事實”(1944)一文。
的確,基督從死裡復活,顯明他是神進入人類的歷史,為要完成人的救贖--這“道成肉身”的神跡,超越了神話,使神話變成事實;但是,另一方面,路易士提醒我們:
這則神話變成事實之後,並非就不再成其為神話,這就是一種奇跡了。……若想做個真正的基督徒,我們就必須一方面同意上述的歷史事實,一方面用欣賞一切神話所需要的想像力,接受其中所含的神話成分(雖然它已成為事實);這兩者同等重要。……基督教神學中閃耀著神話的光輝……見於“神話變成事實”(1944)一文。
正因“道成肉身”擁有神話的特質,對其中所蘊含的啟示要能充分領悟,人必須在理性的認知之外,馳騁想像,深入體會,讓終極真理具象地映現在知感全域。這項努力,單靠神學的演繹、教義的講述,容易流於空疏。或許基於這種認識,路易士在寫完一系列成功的思想作品,並以犀利的言論、深刻的文化省思,向崇尚理性思考的20世紀人透徹剖析基督教的可信之後,便專心致力於虛構文學的創作,成果包括三本幻遊小說、童話故事集《納尼亞傳奇》和取材自希臘神話的《裸顏》。如果說路易士的思想作品拭除了人的“理性障蔽”,讓人能透過清晰的思考,賞識基督教適應人心需要又與真理相合的本質,那麼,他的虛構作品則可以進一步蕩滌人的情性,激發神思、想像,藉著具體的情節,引導讀者入窺救贖的境界。其中又以《裸顏》這一部恰以“死而重生”為主題的神話小說,最能全面反映他的救贖神學、宗教視野和藝術成就。
他的摯友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認為《裸顏》與《人的絕滅》(The Abolition of Men)堪稱路作雙璧;歐文·巴菲爾德是路易士在牛津時的前期學長,路氏稱他為“在我非正式的師長中,最睿智、傑出的一位”。自牛津畢業後,巴氏續承父業,在倫敦從事圖書代理業務,後來替路氏處理與版稅有關的法律事務。退休後應聘往美國大學講授英國文學,有關詩歌用語及文學想像的論述頗受學界推崇。他與路易士的友誼被譽為20世紀文學交遊中的典範之一。所指譽詞見於《光照路易士》(Light on C. S. Lewis)之序,收錄於1989年出版之《歐文·巴菲爾德論路易士》(Owen Barfield on C. S. Lewis)一書第29頁。批評家也大致同意路氏自己的看法:在他所有的虛構作品中,《裸顏》寫得最精湛、細膩。更有學者以專書說明《裸顏》如何解開理性與想像的糾結,為西方讀者提供睿智的指引。見彼得·薛柯(Peter J. Schakel)所著《路易士作品理性和想像的關係:〈裸顏〉析讀》(Reason and Imagination:On C. S. Lewis - A Study of Till We Have Faces,1984)。許多人從《裸顏》中見識到路氏直追現代小說經典的敘事藝術,紛紛為他的早逝(65歲)歎惋不已,甚至說:“他應該早點寫小說。”
那麼,面對路易士這部寓意深刻的神話小說《裸顏》,我們應該怎樣讀它呢?1936年,38歲的路易士出版《愛的寓言》(The Allegory of Love),探討中古俠義愛情的源流,旁徵博引,立論精闢,奠定了他對寓言研究的學術地位。拉丁詩人筆下的賽姬,被父王遵照阿波羅神諭,“暴陳山巔,供龍攫食”,與初民社會“代罪羔羊”式的獻祭,並無關涉;但是,路易士借用古典神話,刻意把賽姬(伊思陀)塑造成一位“基督型”的人物。由於她超凡的美麗和善良,當國中遭遇瘟疫時,人們交口相傳:經她的手一觸摸,癘疾可得痊癒。於是,民眾把她當作女神膜拜。
這一風潮觸怒了當地主神安姬的祭司,藉口她是引發“天譴”的因由,認為若要拔除饑饉、瘟疫、兵燹的多重禍害,必須將她獻祭,綁在陰山頂的一株聖樹上,作為山神的新娘。對這一犧牲的角色,賽姬坦然接受,一方面固然有“一人死萬人活”替百姓受難的壯烈情懷,另一方面更為了因此便能實現自己多年來的憧憬--與陰山所象徵的生命本源合而為一--內心欣喜莫名。外表看來,整樁獻祭的事件原是一出政教鬥爭的荒謬劇,對她而言,卻宛似一趟歸程,帶她回到那自己靈魂久已嚮往的“宮堡”。就這樣,借著“故事新詮”,路易士賦予賽姬的神話一道與基督教信仰遙相呼應的寓言含義,儼然以實際的神話擬構宣示他的前述理念--神話傳說原是神向人類托夢,其中隱含真實信仰的影子。循著這條線索讀《裸顏》,它簡直就是一部扎實的啟示性著作。
萬象紛呈,人世無常,任何時空的人類,為了認知及求生,往往需要信靠宗教。同樣的需求投射在不同的祭典和信仰中(“安姬有一千種面目”)。路易士透過葛羅人的信仰(崇奉性愛與生殖的女神安姬--與希臘的阿芙洛狄忒、羅馬的維納斯同屬地母型神祇),刻畫了一切宗教共有的現象,包括儀式的意義、獻祭的動機、神話的形成、政教的衝突、信仰給人性帶來的昇華等等,甚至不避諱初民用以禱求豐收的淫祀。此外,更重要的,他為葛羅這個蠻荒小國設計了獨特的時空背景,把它放置在小亞細亞邊陲,黑海附近,未受古典文明薰陶的地域;又讓故事發生在蘇格拉底亡故和耶穌基督誕生之間,也就是希臘理性文明逐漸往周圍世界傳佈的時候。
路易士發揮歷史的想像,塑造了這個半開化的國度,既合史實又富於象徵。他用這樣一個正逢野蠻與文明交接的社會為背景,借著當地原始信仰與理性主義間的彼此激蕩(大祭司和“狐”之間的辯論),化衝突為和諧,經由故事講述者奧璐兒女王終其畢生上下求索,把比這兩者更充分的啟示勾勒了出來--也就是一個既能滿足古代宗教信仰的獻祭要求,又能符合希臘理性主義竭智追求之倫理目標的宗教。從“漸進啟示”的史觀看,這樣的宗教正是最純全的宗教,它包含了一切信仰追尋的JIZHI。當然,它遙遙指向那不久即將進入人類歷史,由道成肉身的神,替人流血犧牲,又從死裡復活,把得贖重生的生命境界向人開啟。路易士稱這為真實的信仰,並在一篇論述文字中,辨析如下:
它完全合乎倫理,卻又超越倫理;古代宗教共有的那種獻祭與重生的主題,以不違逆--甚至超越--良知與理性的方式再度出現。在這當中,WEIYI的真神自顯為永活的造物者,超絕於萬物之外,卻又居攝其中。這樣的一位神不僅是哲學家的神,也是奧秘派和野蠻人的神,他不僅滿足人的理智和情感,更且照顧了各樣原始的衝動,以及超拔在這些衝動之外卓犖如山的一切屬靈憧憬。
《裸顏》可說是上述識見的戲劇化呈現,特別落筆從懵懂進入醒悟之前,所謂夢覺邊緣(half awakening)的信仰追求。
但是,《裸顏》之撼人心弦,並不僅在於隨情節的進展,披露在讀者眼前那逐漸開闊、深邃、清朗的神聖視野。真正令人感動的,是奧璐兒女王這個容貌奇醜、智慧超群、身手矯健,不讓鬚眉的女人--她的情感起伏,她對生命真相鍥而不捨的尋索,及至暮年的覺悟和蛻變--換句話說,她個人靈魂的掙扎、自剖與重生,才是這部小說的主題。賽姬的神話原本就是一則人神相戀的故事,更因賽姬(Psyche)意為“靈魂”,自古以來,這則神話始終發人深省,人們反復推敲其中的寓意,覺得它所反映的正是靈魂對神性(divine nature)的嚮往與渴慕,而賽姬被逐出神宮後的受難過程,恰好象徵靈魂與神合一之前必需經歷的重重考驗。其中,知性的磨煉(穀種分類的寓喻)只算是最初步的功課。
路易士套用這則神話作為《裸顏》的基本情節,所要刻畫的正是靈魂與神複合的經過。這當然是基督教信仰的主要內容之一,而仔細端詳奧璐兒的悟道過程--從驚覺自己原來也是安姬(不只容顏,連靈魂也一樣醜陋--貪婪、自私、善妒……),繼而體會出道德修養對改善安姬似的靈魂其實毫無作用,至終於蛻變成賽姬(當賽姬通過考驗與神複合的刹那,也就是奧璐兒變顏得榮的時刻,因為多年來,在現實世界,奧璐兒挨忍著對賽姬的思念,焚膏繼晷攝理國政,包括最後的著書申訴,其艱巨程度與考驗性質,絕不亞于賽姬為要贖回神的眷愛所需完成的各樣超凡任務。女王奧璐兒的生活與被逐的賽姬其實沒有兩樣,等於在替賽姬分勞。原來,神對奧璐兒所說的預言--“你也將成為賽姬”--背後隱藏著一道屬靈的奧秘:根據“替代”的原理,生命在愛中融匯交流,能夠彼此分擔痛苦、共用成果,在真實的人生中,路易士本人曾經具體地經歷“替代”的奧秘。
不忍見所愛的妻子受骨癌折磨,他禱告神讓自己承擔她的痛苦。果然,“喬伊”(路夫人名為Joy)痛苦減輕,路氏自己卻罹腳疾,醫生診斷病因:“缺乏鈣質。”就像狐所說的,是奧璐兒承擔苦楚,而由賽姬完成工作)--這樣的悟道過程隱約含有基督教信仰的痕跡,尤其吻合原罪與靠十架救恩使靈魂得贖(神“替”人死,“代”人償付罪責),而人得救之後應與基督同背十字架的奧義。
路易士刻畫奧璐兒個人的悟道所採用的筆法仍是先前所提到的:透過古代神話勾勒在夢覺邊緣呼之欲出的啟示。書中的這段句子“在未來遙遠的那一天,當諸神變得全然美麗,或者,當我們終於悟覺,原來,他們一向如此美麗……”讀來恰似舊約中的預言“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耶利米書》31∶31)、“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以西結書》36∶26)。從釋經學的角度看,路易士對古典神話“故事新詮”的寓喻讀法,十分近似基督教傳統的“預表”解經法。依一般解釋學的說法,這種舊文衍生新義的現象,其實便是“先前發生的事件,事後看來,會產生比事發當時所能領悟的更為充分的義理”見雅歌出版社出版路氏論《詩篇》的中譯《詩篇擷思》(Reflection on the Psalms)第10章。
狐的幽靈在異象中對奧璐兒所說的“神聖的大自然能改變過去,尚無一事物是以它真實的面目存在著”,指的就是類似的事。當充分啟示的亮光一出現,許多事物真實的面貌便顯現出來,這是《裸顏》的中心思想,也是《裸顏》的敘事技巧。就奧璐兒而言,這件事發生在她透過理性與神抗辯到底,卻不知不覺揭開自己靈魂面紗的刹那。真切的自我認識與認識神是同時發生的。這樣看來,形式與內容的有機結合在這本小說中可說達到極圓融的地步,所以,對這本小說非常激賞的歐文·巴菲爾德特別提醒讀者,千萬別把它當作純粹的寓言讀,它其實是“一部把創作神話的想像發揮到JIZHI所寫成的作品”。的確,讀《裸顏》若僅止于從中捕捉與教義相合的寓意,進而揣摩大師如何移花接木,巧借賽姬神話架構“現代福音”,這種寓喻式的讀法雖然有趣,卻辜負了路易士的創作原旨,因為他的目的不在於把賽姬神話淡化為教義,而在把被教義化了的信仰還原為耐人尋味、需要人用心靈加以體會的神話。
路易士在《文藝評論的實驗》--一本討論如何辨別好書、壞書的著作中,這樣推許閱讀的功能:
文學經驗療治傷口,卻不會剝奪個人擁有個體性的權利。有些在聚會中感染到的群體情緒也可以療傷,但往往會使個體性遭到破壞。在群體情緒中,不同個體原本分隔的自我融匯合流,我們全都沉浸回到無我(自我未產生前)的境界中。但在閱讀偉大的文學作品時,我則變成一千個人,卻仍然保有我的自己。這就像希臘詩中所描寫的夜空,我以千萬顆眼睛覽照萬象,但那用心諦視的仍是我這個人。在這裡面,就像在崇拜中、在戀愛中、在將道德付諸行動中和在認知中一樣,我超越了自己,卻也從未這樣實現自己。
但願讀者在閱讀《裸顏》時,有同樣的感受。
--曾珍珍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