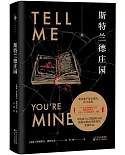如果有人問我,我的祖國通過什麼在我的美學基因里留下深遠影響,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通過雅納切克的音樂。
身世的巧合在這里也扮演了它的角色,因為雅納紉克一輩子都在布爾諾生活,我父親也是。
父親還是年輕鋼琴家的時候,在這里曾經是一個對雅納切克著迷的(孤立的)音樂社團的成員,這些人是雅納切克最早的行家與捍衛者。
我在雅納切克辭世之後一年來到人間,從小,我就每天听父親或是他的學生們彈奏他的音樂。一九七一年,在我父親的葬禮上,在被佔領的陰暗年代,我不讓任何人致辭;只有四個音樂家,在火化時,演奏雅納切克的《第二號弦樂四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