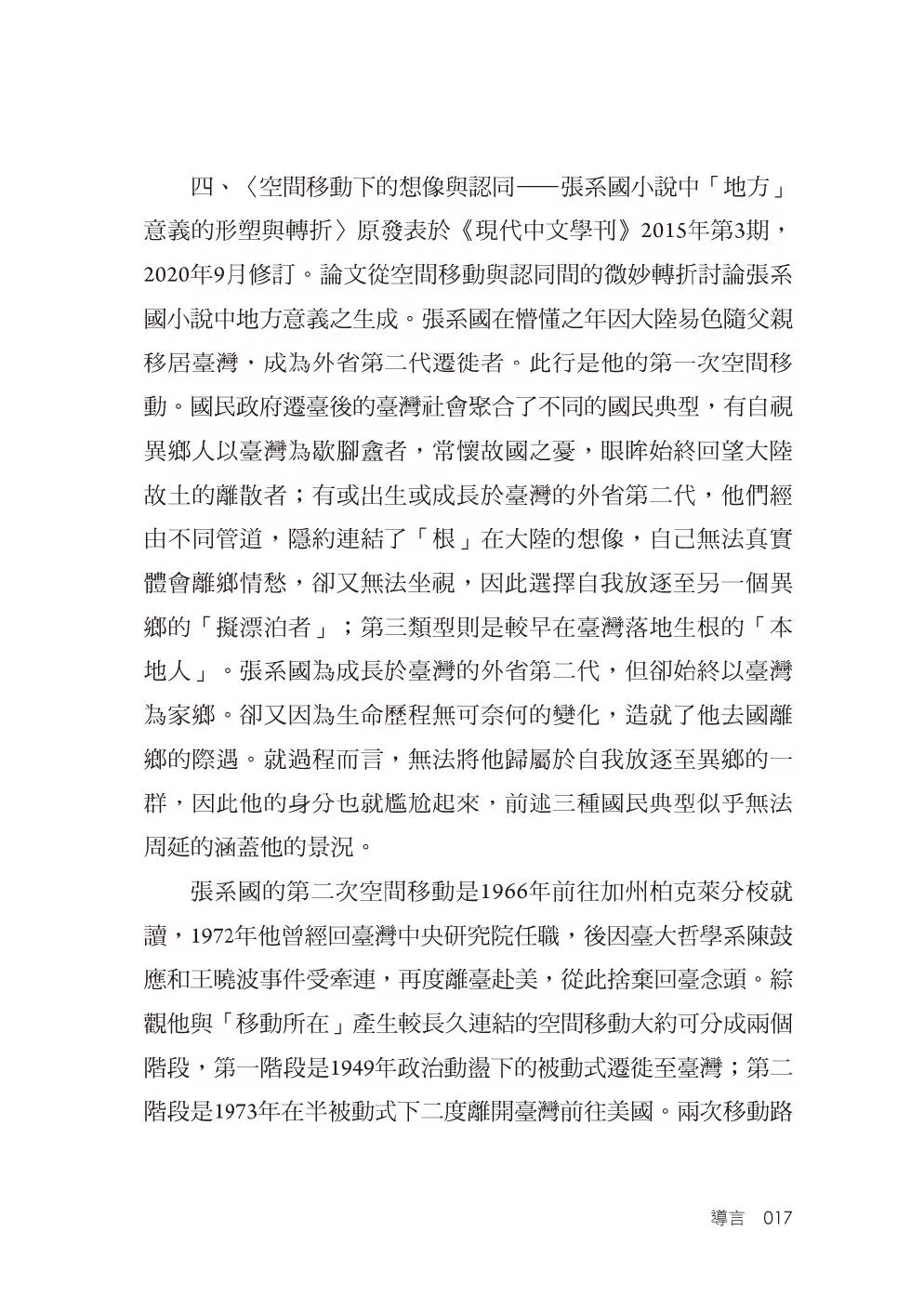《土地的詩意想像》以當代華語文學為座標點,討論土地書寫的綿延轉折,空間想像的合縱連橫,以及土地與空間的彼此律動如何進入時間流變的長河,形成地方或區域歷史意識。
本書共七章,由三項主題相互貫穿。第一至三章聚焦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近年的發展,分別處理排灣族女性經由西藏轉山覓得歸鄉之路的過程;日治時代賽德克亞族相互歧出的溯源敘事;卑南族重組及虛構斯卡羅遺事的得失。第四、五章焦點轉向臺灣與中國大陸及海外華語社群的離散經驗。
張系國生於大陸,長於臺灣,赴美留學後回臺又離臺,終於定居異鄉。謝裕民為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作家,卻在「重構南洋圖像」的寫作中勾勒出無比繁複的家族歷史,從明鄭臺灣到印尼香料群島,外省「第十代」的尋根之旅引發出始/史料未及的發現。
本書最後兩章則以花蓮及香港九龍城寨為個案,探討「城」作為「地方」的意義。花蓮位處「後山」,居民來自四方,城鄉定位一直模糊不清。九龍城寨則是歷史夾縫中擠兌而出的空間,三不管的「飛地」。兩者在近年面臨重新定位的挑戰,花蓮變身為觀光勝地,杜撰的「幸福空間」,九龍城寨則在拆毀後轉為公園以及影視電玩的主題。
本書特色
★ 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劉秀美以當代華語文學為座標點,探討地方或區域歷史意識形成的歷程。
★ 捕捉、描寫、想像文字意象、藝術造作、身體行動所投射的靈光,再一次認知土地所深藏的神秘性,言說土地的難以言說性,以及土地面向歷史敞開的多重媒介性。
各界推薦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德威.專文推薦 |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劉秀美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中國現代文學》主編
著有《五十年來的台灣通俗小說》、《宜蘭縣大同鄉口傳文學》、《火神眷顧的光明未來—撒奇萊雅族口傳故事》、《山海的召喚—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從口頭傳統到文字書寫—臺灣原住民族敘事文學的精神蛻變與返本開新》等書。
劉秀美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中國現代文學》主編
著有《五十年來的台灣通俗小說》、《宜蘭縣大同鄉口傳文學》、《火神眷顧的光明未來—撒奇萊雅族口傳故事》、《山海的召喚—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從口頭傳統到文字書寫—臺灣原住民族敘事文學的精神蛻變與返本開新》等書。
目錄
序--土地、空間、拓撲/王德威
導言
壹、幸福空間:從《老鷹,再見》看移動的聖山象徵
一、前言
二、移動/神山之「聖性」象徵
三、死亡/再尋幸福空間
四、結語
貳、日治時期臺灣賽德克亞族祖源敘事中的根莖流轉脈絡
一、前言
二、時間流轉中的祖源敘事
三、地理空間移動脈絡下「根」的流轉
四、結語
附錄
叁、歷史的詩意想像--記斯卡羅遺事
一、前言
二、口述歷史傳說文本的生成語境
三、時序交錯的口頭敘事文本
四、部落歷史的選擇、詮釋與綴補
五、結語
肆、空間移動下的想像與認同--張系國小說中「地方」意義的形塑與轉折
一、前言
二、遠離母體的想像
三、浪遊者的美國夢
四、文化鄉愁的歸宿
五、混雜、融合與創新的「臺客」
六、結語
伍、「異」鄉「原」位--〈安汶假期〉、《老鷹,再見》中移位、易位與錯位的鄉愁
一、前言
二、藏在歷史的鄉愁
三、兩地鄉愁
四、結語
陸、從地方到無地方性--「邊城」敘事中的人與時空
一、前言
二、邊城中的邊城
三、邊城軼事
四、消失的淨土
五、結語
柒、從圍城到失城--九龍城寨的前世今生
導言
壹、幸福空間:從《老鷹,再見》看移動的聖山象徵
一、前言
二、移動/神山之「聖性」象徵
三、死亡/再尋幸福空間
四、結語
貳、日治時期臺灣賽德克亞族祖源敘事中的根莖流轉脈絡
一、前言
二、時間流轉中的祖源敘事
三、地理空間移動脈絡下「根」的流轉
四、結語
附錄
叁、歷史的詩意想像--記斯卡羅遺事
一、前言
二、口述歷史傳說文本的生成語境
三、時序交錯的口頭敘事文本
四、部落歷史的選擇、詮釋與綴補
五、結語
肆、空間移動下的想像與認同--張系國小說中「地方」意義的形塑與轉折
一、前言
二、遠離母體的想像
三、浪遊者的美國夢
四、文化鄉愁的歸宿
五、混雜、融合與創新的「臺客」
六、結語
伍、「異」鄉「原」位--〈安汶假期〉、《老鷹,再見》中移位、易位與錯位的鄉愁
一、前言
二、藏在歷史的鄉愁
三、兩地鄉愁
四、結語
陸、從地方到無地方性--「邊城」敘事中的人與時空
一、前言
二、邊城中的邊城
三、邊城軼事
四、消失的淨土
五、結語
柒、從圍城到失城--九龍城寨的前世今生
一、前言
二、殖民地之中的「自由」之城
三、圍城內/外
四、失城之後
五、結語
引用書目
後記
序
序
土地、空間、拓撲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德威
土地與文學的關聯可以上溯至史前神話。希臘神話的Gaea打破混沌,創造日月星辰山川;埃及神話的Geb頭頂蒼鵝,主理萬物生長。中國的女媧摶土造人,后稷教民稼穡,肇始華夏文明。千百年來東西方有關土地象徵的創作與論述不絕如縷。十八世紀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號召國族文學,更視土地為文學表述的第一要素:有斯土而有斯文。時至現代,由召喚土地所形成的「感覺結構」—從鄉土到本土,從領土到故土,從淨土到惡土—不但體現在各種文藝形式上,也成為意識形態的一種。土地引申出繁複的喻象系統,是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是根深蒂固的寄託。
然而現代又是一個解構土地的時代。「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共產主義宣言〉如是說。大規模的人口移動遷徙,改天換地的熱戰冷戰,還有工業化、「人類紀」對自然生態帶來的龐大衝擊……。土地不再是「在那裡」的亙古存在,而成為族群、地理政治、環境以及認知領域一再辯駁的焦點。一九三○年代以後空間研究興起不是偶然。李非博(Henri Lefebvre)探問意識形態、生產模式如何左右我們「居之不疑」的方寸之地,傅科(Michel Foucault)描述社會總已經是權力監控和知識構造下的空間,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投射眾聲喧嘩的時空交匯,只是最明顯的例子。到了後現代,空間研究更因為數位文化和虛擬媒介的快速發展,產生層層虛實論證。
正是在土地與空間這兩大命題間,劉秀美教授的《土地的詩意想像》提出她的研究心得。她以當代華語文學為座標點,討論土地書寫的綿延轉折,空間想像的合縱連橫,還有最重要的,土地與空間的彼此律動如何進入時間流變的長河,形成地方或區域歷史意識。本書共有七章,由三項主題相互貫穿。第一至三章聚焦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近年的發展,分別處理排灣族女性經由西藏轉山覓得歸鄉之路的過程;日治時代賽德克亞族相互歧出的溯源敘事;卑南族重組及虛構斯卡羅遺事的得失。第四、五章則將焦點轉向臺灣與中國大陸及海外華語社群的離散經驗。張系國生於大陸,長於臺灣,赴美留學後回臺又離臺,最終定居異鄉。謝裕民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作家,卻在「重構南洋圖像」的寫作中勾勒出無比繁複的家族歷史,從明鄭臺灣到印尼香料群島,外省「第十代」的尋根之旅引發出始/史料未及的發現。本書最後兩章則以花蓮及香港九龍城寨為案例,探討「城」作為「地方」的意義。花蓮位處「後山」,居民來自四方,城鄉定位一直模糊不清。九龍城寨則是歷史夾縫中擠兌而出的空間,三不管的「飛地」。兩者在近年面臨重新定位的挑戰,花蓮變身為觀光勝地,杜撰的「幸福空間」,九龍城寨則在拆毀後轉為公園以及影視電玩的世界。
從臺灣大武山到西藏岡仁布欽山,從花蓮到香港九龍城寨,從新加坡、印尼到北美,從巴代到張愛玲,《土地的詩意想像》涵蓋一系列不同的空間座標及書寫範疇,在在可以看出劉教授用心所在。她一方面肯定在地、原鄉經驗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對當下以模擬論為前提的研究提出修正。寫實主義、鄉土文學每每強調文字及藝術媒介模仿、再現現實的威力,彷彿掌握某種信念或描述訣竅就能掌握時空,為土地定位。與此相對,她介紹「時空流轉」觀念,提醒我們空間—由三個線性維度所構造的座標場域—的物理性、歷史性和權宜性必須付諸不斷檢視。而如果將「空間」中文二字拆開解讀,我們理解「空」不是空空如也,而是虛位以待;「間」意味處所、地方、時候,還有最重要的,兩者之中的縫隙以及關聯。
本書前三章立刻導入正題:再沒有比原住民敘事更能凸顯臺灣的土地情結了。劉教授關心的是,在標榜原住民族土地敘事與國家、族群正義同時,我們可曾挖掘他們信仰與記憶的曲折線索,以及漢語敘事規範所加諸的軟性暴力?更何況原住民族所曾固守的土地其實早已成為國家領土的一部分,與土地息息相關的生活和信仰體系也因現代化的無所不在而節節敗退。面對這樣的難題,當代原住民族土地述寫必須另闢蹊徑。排灣族女子伊苞在眼前無路之際,踏上西藏轉山之旅。她的紀實之作《老鷹,再見》敘述異鄉朝聖的體驗如何讓她心有靈犀,重燃對故鄉祖靈的信念。排灣族與藏族的地緣差異何止千里,但兩者對「幸福空間」的追求如出一轍。聖山—不論是臺灣南部的大武山或是西藏深處的岡仁布欽、阿尼瑪卿山—跳脫了俗世的土地框架,真正有了超越意義。
賽德克族近年因為影視媒介廣受注意,但在大歷史主導的敘述下,這一族群內部的恩怨和分合,還有因此衍生的錯綜記憶幾乎已被遮蔽。劉教授重探日本殖民時期人類學研究報告,呈現賽德克亞族的遷徙路徑以及祖述起源的方式竟是如此混雜,一如他們遷居的途徑。重建這些族群的譜系重建也正是理解其間的分叉。同樣的,卑南族一支卡日卡蘭部落1633年的南遷始末歷來眾「說」紛紜。因為部落沒有文字記錄傳統,一切歷史憑靠世代口傳接力,莫衷一是。當代卑南族作家巴代憑藉人類學考察資料以及祖輩口傳寫出小說《斯卡羅人》。小說裡的歷史、記憶、虛構交相為用,所構造的族裔譜系不僅是尋根溯本的努力,更是一種詩意的召喚。
捍衛臺灣本土立場的學者企圖建立島上原生性(indigeneity)理想,當然值得尊重。但在強烈的尋根焦慮下,他們不知不覺形成原鄉、原道、原住民,原教旨的連鎖。一方面將原住民族化為正本清源的島嶼象徵,另一方面又亟亟還原原住民族的絕對本體性。前者將原住民族寓言化,後者將原住民族始原/絕緣化,兩者誠意十足,卻都忽略原住民在地的、歷史的處境與時俱變。在劉教授的研究下,原住民族不是株守部落的樣板存在,他們的征伐墾殖、生老病死形成複雜而不斷變動的生態網絡,難以由簡化的土地標籤定位。原住民族為我們上了一課:千百年的土地經驗不僅止於根深蒂固,而是根莖流轉。錯位的聖山,抵觸的記憶,以虛代實的歷史,族群的輾轉記憶與遺忘、遷徙與定居,離散與回歸,神聖與褻瀆間,不斷將古老的話題賦予新意。
本書的第四、五章處理土地/空間辯證另一組議題:離散與反離散。場景由臺灣擴大到東南亞與北美。近年華語語系統研究興起,史書美教授提出「反離散」論,要求移居他鄉者不再眷戀故土,而應落地生根,融入在地文化。如此理論有其政治正確性,卻極易陷入簡化邏輯,成為前述土地迷思的倒影。離散在任何社會形態裡都不應是常態,但離散作為生存的選項之一,卻攸關主體的能動性與自決權。劉教授以美國的張系國、新加坡的謝裕民、臺灣的伊苞作為實例。
張系國生於大陸,1949國共裂變,隨家人來臺,完成大學教育後赴美。張學成之後本擬回臺就業,因為政治原因再度決定返美定居至今。但張對臺灣未嘗或忘。從早期的《地》、《黃河之水》到後期的《帝國與臺客》,他不斷思考身份認同的種種選項,而臺灣成為他的論述槓桿最重要的支點。以往部分學者以外省第二代或旅美華人的標籤定義張的身份或作品,殊不知他筆下的中國人、臺灣人或華裔不斷游走,認同指標因此變化多端。中國也許是揮之不去的原鄉,但這原鄉也可能是弔詭的海市蜃樓,以「他者」形象作為主體思辨一己存在的方法,不論是否定還是肯定。
我在他處曾提及的華語語系的「後三民主義」:後移民,後夷民,後遺民。這當然和當代華語世界空間快速流轉現象息息相關。儘管長居美國,張系國的書寫與對話對象是臺灣,彷彿他並未離開自己的第二故鄉。儘管心懷中國,張的敘事卻總影射那「中國」的失落或可望而不可及。但張只是遺民作家麼?如果遺民總已暗示時空的消逝錯置,正統的替換遞嬗,「後」遺民則更錯置那已然錯置的時空,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這樣的姿態可以是耽溺的,但更不乏其中批判和解脫的契機。張的作品正可以如是觀。
而「後遺民」遇上「原住民」問題更引人思辨。本書第五章介紹新加坡作家謝裕民的中篇《安汶假期》,並以之與前述伊苞的《老鷹,再見》作為對照。小說中的新加坡華人父親與兒子前往印尼馬魯古群島首府安汶尋根,偶然間得知他們原籍安徽鳳陽朱姓。1662年,明亡以後十八年,十世祖欲赴臺灣投靠鄭成功,卻為颶風吹到安汶。直至十九世紀中,偶有粵人闕名來到島上,遇見土著,發現竟是朱氏後人。闕受託攜其子回到中國,即為新加坡青年的曾祖。曾祖日後自中國移民印尼,1960年代又因印尼排華返回中國,卻將一個兒子(即青年的父親)留下隨託付者前往新加坡。故事高潮,父子兩人在安汶似乎找到家族後人,但他們看來就(像)是土著……。
如果不是那場颶風,《安汶假期》主人翁可能是臺灣人,明代遺民,唐山過客,印尼土著,新加坡公民,還有缺席的「臺灣主體」,儼然就是一則後移/遺/夷民譜系寓言。劉教授又以《老鷹,再見》中的返根故事作為對照,提出「移位、易位、錯位」的觀察。「我們的血統到底要追溯到哪裏?三代前有印尼土著血統,再往前原來還是明朝的貴族。誰知道再往前追溯,會不會不是漢人?」、(謝裕民)「你在家,卻是個陌生人。」(伊苞)當新加坡的謝裕民回望自己家族的移民史,終於寫下一則華變為夷的後移民寓言,而在台灣生活在漢人霸權下的伊苞遙想祖靈,何嘗不是咀嚼另類後遺民的滋味?
本書最後兩章將焦點定位於城市想像空間的營造。並以兩個看似截然不同的案例作為討論起點。花蓮位於臺灣東部山海之間,歷來多為原住民族居住出入的區域。清代閩、客移民漸多,形成聚落,1949之後又有外省族群遷入。這四大族群有如花東海岸下的板塊般起伏互動。花蓮因為開發較遲,交通不便,因此每每為西部平原住民視為落後地區。但所謂「落後」又如何定義?近年臺灣東岸時來運轉,成為臺灣及海外遊客嚮往的景點,消費想像的始原鄉愁所在。花蓮以其「地方」風土成為觀光經濟的資本。早在六十年代初,張愛玲應該是懷著這樣曖昧的心情來到花蓮。當時她已自香港移居美國,但冷戰的世界前景難測,於是有了重回亞洲投石問路之行。花蓮是張行程裡意外的一站,而她筆下的花蓮—她所謂的「邊城」(frontier city)—也成為她搬演異國情調的場景。但張如此描繪營造的邊城艷異荒涼,又似乎投射了她個人的曖昧心境。花蓮透露了似曾相識,既近且遠的詭秘感(uncanny)。
另一方面,花蓮在地作家筆下的故鄉其實也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當年陪同張愛玲訪問花蓮的王禎和曾有不少作品描寫地方人事,嬉笑怒罵,不脫寫實風格。到了八十年代的《玫瑰玫瑰我愛你》,他放手寫六十年代一群花蓮妓女勤學英語,「為國捐軀」,娛樂度假美軍的瘋狂鬧劇。而在陳雨航筆下,也是六十年代的花蓮卻如此歲月靜好,成為臺灣永遠的抒情鄉愁所在。然而對長期徜徉花蓮山水的吳明益而言,新世紀的花蓮屢經人工整治—或複製,已漸失去原來面貌。俱往矣,不論是詭異的花蓮,傖俗的花蓮,還是抒情的花蓮。在經濟誘因的催動下,以往的山風海雨已經被馴化成規矩的觀光景點。何為地方丰采已經是難以聞問的話題。
另一案例是九龍城寨的前世今生。九龍城寨建築始於1847年,原為清廷駐軍所在在,1899年成為英屬香港殖民地的法外地區,一處無政府的城中「圍城」。城寨藏污納垢,一直被視為殖民政府統治下的一大毒瘤。然而當城寨1993年拆除改建為公園後,卻竟然成為「香港不再」的象徵。那驚人的人口密度、櫛次鱗比的屋宇建設、各式非法店家、你死我活的黑社會活動,有如末世奇觀,不僅投射香港記憶圖景「痛而且快」的刺點(punctum),也提供全球建築、社會、生態研究無數話題。有關九龍城寨的影視甚至電玩電競遊戲層出不窮,在異次元空間裡延續甚至發展了城寨的生命。城寨如幽靈般的存在、拆毀、與復返,無疑是後現代空間絕佳的例子了。
《土地的詩意想像》文本與理論涵蓋廣闊。綜述劉教授的研究方法,我們可以稱之拓撲學(topography)的實驗。最基本的拓撲意指脫離點線面三維座標空間,指向多維度的動態空間。由此產生的疊景聯動的樣式,或以主體自身標記,或以主體與社會脈絡的替代性詞語,隨時空的轉圜不斷挪移變換取代。拓撲學的功能在於偵測每一表意發聲體系的底層範式,及其張弛、隱顯的力度。以此,劉教授將目前學界鄉土或本土研究的格局陡然放開。從南台灣排灣族的聖山回歸到九龍城寨起死回生,從印尼小島的明末遺民到花蓮風月場的露水因緣,無數的空間層層在書中交織,述說一則又一則人間故事。
我們再次回到此書標題—土地的詩意想像—的意涵。從哲學層次而言,大地深邃而豐饒,何能由國族論述,族裔譜系,田野報告,個人記憶、身體經驗所能盡詳?比諸同樣生長在大地之上、之下的萬物,人類僅佔一席之地,曾幾何時,卻號稱為土地的主人。海德格(Martin Heiddger)論「世界」與「大地」的關係,得出「遮蔽」和「無蔽」,「敞開」和「封閉」的辯證循環。如果世界向光天化日敞開,大地則指向「在本質上將自己封閉在自身中的東西」;「唯有在那些被保護著,並作為一種本質上不可揭示的東西保存下來的地方,大地才能出現。」(《藝術製作的起源》)所謂「詩意」就是折衝在「敞開」與「遮蔽」之間,最重要的生發與結晶。據此,土地詩學的意義即在於捕捉、描寫、想像文字意象、藝術造作、身體行動所投射的靈光,再一次認知土地所深藏的神秘性,言說土地的難以言說性,以及土地面向歷史敞開的多重媒介性。也在這一意義上,土地詩學的論述重新規劃了我們對世界,對空間的有限與無限的認知。
土地、空間、拓撲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德威
土地與文學的關聯可以上溯至史前神話。希臘神話的Gaea打破混沌,創造日月星辰山川;埃及神話的Geb頭頂蒼鵝,主理萬物生長。中國的女媧摶土造人,后稷教民稼穡,肇始華夏文明。千百年來東西方有關土地象徵的創作與論述不絕如縷。十八世紀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號召國族文學,更視土地為文學表述的第一要素:有斯土而有斯文。時至現代,由召喚土地所形成的「感覺結構」—從鄉土到本土,從領土到故土,從淨土到惡土—不但體現在各種文藝形式上,也成為意識形態的一種。土地引申出繁複的喻象系統,是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是根深蒂固的寄託。
然而現代又是一個解構土地的時代。「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共產主義宣言〉如是說。大規模的人口移動遷徙,改天換地的熱戰冷戰,還有工業化、「人類紀」對自然生態帶來的龐大衝擊……。土地不再是「在那裡」的亙古存在,而成為族群、地理政治、環境以及認知領域一再辯駁的焦點。一九三○年代以後空間研究興起不是偶然。李非博(Henri Lefebvre)探問意識形態、生產模式如何左右我們「居之不疑」的方寸之地,傅科(Michel Foucault)描述社會總已經是權力監控和知識構造下的空間,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投射眾聲喧嘩的時空交匯,只是最明顯的例子。到了後現代,空間研究更因為數位文化和虛擬媒介的快速發展,產生層層虛實論證。
正是在土地與空間這兩大命題間,劉秀美教授的《土地的詩意想像》提出她的研究心得。她以當代華語文學為座標點,討論土地書寫的綿延轉折,空間想像的合縱連橫,還有最重要的,土地與空間的彼此律動如何進入時間流變的長河,形成地方或區域歷史意識。本書共有七章,由三項主題相互貫穿。第一至三章聚焦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近年的發展,分別處理排灣族女性經由西藏轉山覓得歸鄉之路的過程;日治時代賽德克亞族相互歧出的溯源敘事;卑南族重組及虛構斯卡羅遺事的得失。第四、五章則將焦點轉向臺灣與中國大陸及海外華語社群的離散經驗。張系國生於大陸,長於臺灣,赴美留學後回臺又離臺,最終定居異鄉。謝裕民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作家,卻在「重構南洋圖像」的寫作中勾勒出無比繁複的家族歷史,從明鄭臺灣到印尼香料群島,外省「第十代」的尋根之旅引發出始/史料未及的發現。本書最後兩章則以花蓮及香港九龍城寨為案例,探討「城」作為「地方」的意義。花蓮位處「後山」,居民來自四方,城鄉定位一直模糊不清。九龍城寨則是歷史夾縫中擠兌而出的空間,三不管的「飛地」。兩者在近年面臨重新定位的挑戰,花蓮變身為觀光勝地,杜撰的「幸福空間」,九龍城寨則在拆毀後轉為公園以及影視電玩的世界。
從臺灣大武山到西藏岡仁布欽山,從花蓮到香港九龍城寨,從新加坡、印尼到北美,從巴代到張愛玲,《土地的詩意想像》涵蓋一系列不同的空間座標及書寫範疇,在在可以看出劉教授用心所在。她一方面肯定在地、原鄉經驗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對當下以模擬論為前提的研究提出修正。寫實主義、鄉土文學每每強調文字及藝術媒介模仿、再現現實的威力,彷彿掌握某種信念或描述訣竅就能掌握時空,為土地定位。與此相對,她介紹「時空流轉」觀念,提醒我們空間—由三個線性維度所構造的座標場域—的物理性、歷史性和權宜性必須付諸不斷檢視。而如果將「空間」中文二字拆開解讀,我們理解「空」不是空空如也,而是虛位以待;「間」意味處所、地方、時候,還有最重要的,兩者之中的縫隙以及關聯。
本書前三章立刻導入正題:再沒有比原住民敘事更能凸顯臺灣的土地情結了。劉教授關心的是,在標榜原住民族土地敘事與國家、族群正義同時,我們可曾挖掘他們信仰與記憶的曲折線索,以及漢語敘事規範所加諸的軟性暴力?更何況原住民族所曾固守的土地其實早已成為國家領土的一部分,與土地息息相關的生活和信仰體系也因現代化的無所不在而節節敗退。面對這樣的難題,當代原住民族土地述寫必須另闢蹊徑。排灣族女子伊苞在眼前無路之際,踏上西藏轉山之旅。她的紀實之作《老鷹,再見》敘述異鄉朝聖的體驗如何讓她心有靈犀,重燃對故鄉祖靈的信念。排灣族與藏族的地緣差異何止千里,但兩者對「幸福空間」的追求如出一轍。聖山—不論是臺灣南部的大武山或是西藏深處的岡仁布欽、阿尼瑪卿山—跳脫了俗世的土地框架,真正有了超越意義。
賽德克族近年因為影視媒介廣受注意,但在大歷史主導的敘述下,這一族群內部的恩怨和分合,還有因此衍生的錯綜記憶幾乎已被遮蔽。劉教授重探日本殖民時期人類學研究報告,呈現賽德克亞族的遷徙路徑以及祖述起源的方式竟是如此混雜,一如他們遷居的途徑。重建這些族群的譜系重建也正是理解其間的分叉。同樣的,卑南族一支卡日卡蘭部落1633年的南遷始末歷來眾「說」紛紜。因為部落沒有文字記錄傳統,一切歷史憑靠世代口傳接力,莫衷一是。當代卑南族作家巴代憑藉人類學考察資料以及祖輩口傳寫出小說《斯卡羅人》。小說裡的歷史、記憶、虛構交相為用,所構造的族裔譜系不僅是尋根溯本的努力,更是一種詩意的召喚。
捍衛臺灣本土立場的學者企圖建立島上原生性(indigeneity)理想,當然值得尊重。但在強烈的尋根焦慮下,他們不知不覺形成原鄉、原道、原住民,原教旨的連鎖。一方面將原住民族化為正本清源的島嶼象徵,另一方面又亟亟還原原住民族的絕對本體性。前者將原住民族寓言化,後者將原住民族始原/絕緣化,兩者誠意十足,卻都忽略原住民在地的、歷史的處境與時俱變。在劉教授的研究下,原住民族不是株守部落的樣板存在,他們的征伐墾殖、生老病死形成複雜而不斷變動的生態網絡,難以由簡化的土地標籤定位。原住民族為我們上了一課:千百年的土地經驗不僅止於根深蒂固,而是根莖流轉。錯位的聖山,抵觸的記憶,以虛代實的歷史,族群的輾轉記憶與遺忘、遷徙與定居,離散與回歸,神聖與褻瀆間,不斷將古老的話題賦予新意。
本書的第四、五章處理土地/空間辯證另一組議題:離散與反離散。場景由臺灣擴大到東南亞與北美。近年華語語系統研究興起,史書美教授提出「反離散」論,要求移居他鄉者不再眷戀故土,而應落地生根,融入在地文化。如此理論有其政治正確性,卻極易陷入簡化邏輯,成為前述土地迷思的倒影。離散在任何社會形態裡都不應是常態,但離散作為生存的選項之一,卻攸關主體的能動性與自決權。劉教授以美國的張系國、新加坡的謝裕民、臺灣的伊苞作為實例。
張系國生於大陸,1949國共裂變,隨家人來臺,完成大學教育後赴美。張學成之後本擬回臺就業,因為政治原因再度決定返美定居至今。但張對臺灣未嘗或忘。從早期的《地》、《黃河之水》到後期的《帝國與臺客》,他不斷思考身份認同的種種選項,而臺灣成為他的論述槓桿最重要的支點。以往部分學者以外省第二代或旅美華人的標籤定義張的身份或作品,殊不知他筆下的中國人、臺灣人或華裔不斷游走,認同指標因此變化多端。中國也許是揮之不去的原鄉,但這原鄉也可能是弔詭的海市蜃樓,以「他者」形象作為主體思辨一己存在的方法,不論是否定還是肯定。
我在他處曾提及的華語語系的「後三民主義」:後移民,後夷民,後遺民。這當然和當代華語世界空間快速流轉現象息息相關。儘管長居美國,張系國的書寫與對話對象是臺灣,彷彿他並未離開自己的第二故鄉。儘管心懷中國,張的敘事卻總影射那「中國」的失落或可望而不可及。但張只是遺民作家麼?如果遺民總已暗示時空的消逝錯置,正統的替換遞嬗,「後」遺民則更錯置那已然錯置的時空,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這樣的姿態可以是耽溺的,但更不乏其中批判和解脫的契機。張的作品正可以如是觀。
而「後遺民」遇上「原住民」問題更引人思辨。本書第五章介紹新加坡作家謝裕民的中篇《安汶假期》,並以之與前述伊苞的《老鷹,再見》作為對照。小說中的新加坡華人父親與兒子前往印尼馬魯古群島首府安汶尋根,偶然間得知他們原籍安徽鳳陽朱姓。1662年,明亡以後十八年,十世祖欲赴臺灣投靠鄭成功,卻為颶風吹到安汶。直至十九世紀中,偶有粵人闕名來到島上,遇見土著,發現竟是朱氏後人。闕受託攜其子回到中國,即為新加坡青年的曾祖。曾祖日後自中國移民印尼,1960年代又因印尼排華返回中國,卻將一個兒子(即青年的父親)留下隨託付者前往新加坡。故事高潮,父子兩人在安汶似乎找到家族後人,但他們看來就(像)是土著……。
如果不是那場颶風,《安汶假期》主人翁可能是臺灣人,明代遺民,唐山過客,印尼土著,新加坡公民,還有缺席的「臺灣主體」,儼然就是一則後移/遺/夷民譜系寓言。劉教授又以《老鷹,再見》中的返根故事作為對照,提出「移位、易位、錯位」的觀察。「我們的血統到底要追溯到哪裏?三代前有印尼土著血統,再往前原來還是明朝的貴族。誰知道再往前追溯,會不會不是漢人?」、(謝裕民)「你在家,卻是個陌生人。」(伊苞)當新加坡的謝裕民回望自己家族的移民史,終於寫下一則華變為夷的後移民寓言,而在台灣生活在漢人霸權下的伊苞遙想祖靈,何嘗不是咀嚼另類後遺民的滋味?
本書最後兩章將焦點定位於城市想像空間的營造。並以兩個看似截然不同的案例作為討論起點。花蓮位於臺灣東部山海之間,歷來多為原住民族居住出入的區域。清代閩、客移民漸多,形成聚落,1949之後又有外省族群遷入。這四大族群有如花東海岸下的板塊般起伏互動。花蓮因為開發較遲,交通不便,因此每每為西部平原住民視為落後地區。但所謂「落後」又如何定義?近年臺灣東岸時來運轉,成為臺灣及海外遊客嚮往的景點,消費想像的始原鄉愁所在。花蓮以其「地方」風土成為觀光經濟的資本。早在六十年代初,張愛玲應該是懷著這樣曖昧的心情來到花蓮。當時她已自香港移居美國,但冷戰的世界前景難測,於是有了重回亞洲投石問路之行。花蓮是張行程裡意外的一站,而她筆下的花蓮—她所謂的「邊城」(frontier city)—也成為她搬演異國情調的場景。但張如此描繪營造的邊城艷異荒涼,又似乎投射了她個人的曖昧心境。花蓮透露了似曾相識,既近且遠的詭秘感(uncanny)。
另一方面,花蓮在地作家筆下的故鄉其實也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當年陪同張愛玲訪問花蓮的王禎和曾有不少作品描寫地方人事,嬉笑怒罵,不脫寫實風格。到了八十年代的《玫瑰玫瑰我愛你》,他放手寫六十年代一群花蓮妓女勤學英語,「為國捐軀」,娛樂度假美軍的瘋狂鬧劇。而在陳雨航筆下,也是六十年代的花蓮卻如此歲月靜好,成為臺灣永遠的抒情鄉愁所在。然而對長期徜徉花蓮山水的吳明益而言,新世紀的花蓮屢經人工整治—或複製,已漸失去原來面貌。俱往矣,不論是詭異的花蓮,傖俗的花蓮,還是抒情的花蓮。在經濟誘因的催動下,以往的山風海雨已經被馴化成規矩的觀光景點。何為地方丰采已經是難以聞問的話題。
另一案例是九龍城寨的前世今生。九龍城寨建築始於1847年,原為清廷駐軍所在在,1899年成為英屬香港殖民地的法外地區,一處無政府的城中「圍城」。城寨藏污納垢,一直被視為殖民政府統治下的一大毒瘤。然而當城寨1993年拆除改建為公園後,卻竟然成為「香港不再」的象徵。那驚人的人口密度、櫛次鱗比的屋宇建設、各式非法店家、你死我活的黑社會活動,有如末世奇觀,不僅投射香港記憶圖景「痛而且快」的刺點(punctum),也提供全球建築、社會、生態研究無數話題。有關九龍城寨的影視甚至電玩電競遊戲層出不窮,在異次元空間裡延續甚至發展了城寨的生命。城寨如幽靈般的存在、拆毀、與復返,無疑是後現代空間絕佳的例子了。
《土地的詩意想像》文本與理論涵蓋廣闊。綜述劉教授的研究方法,我們可以稱之拓撲學(topography)的實驗。最基本的拓撲意指脫離點線面三維座標空間,指向多維度的動態空間。由此產生的疊景聯動的樣式,或以主體自身標記,或以主體與社會脈絡的替代性詞語,隨時空的轉圜不斷挪移變換取代。拓撲學的功能在於偵測每一表意發聲體系的底層範式,及其張弛、隱顯的力度。以此,劉教授將目前學界鄉土或本土研究的格局陡然放開。從南台灣排灣族的聖山回歸到九龍城寨起死回生,從印尼小島的明末遺民到花蓮風月場的露水因緣,無數的空間層層在書中交織,述說一則又一則人間故事。
我們再次回到此書標題—土地的詩意想像—的意涵。從哲學層次而言,大地深邃而豐饒,何能由國族論述,族裔譜系,田野報告,個人記憶、身體經驗所能盡詳?比諸同樣生長在大地之上、之下的萬物,人類僅佔一席之地,曾幾何時,卻號稱為土地的主人。海德格(Martin Heiddger)論「世界」與「大地」的關係,得出「遮蔽」和「無蔽」,「敞開」和「封閉」的辯證循環。如果世界向光天化日敞開,大地則指向「在本質上將自己封閉在自身中的東西」;「唯有在那些被保護著,並作為一種本質上不可揭示的東西保存下來的地方,大地才能出現。」(《藝術製作的起源》)所謂「詩意」就是折衝在「敞開」與「遮蔽」之間,最重要的生發與結晶。據此,土地詩學的意義即在於捕捉、描寫、想像文字意象、藝術造作、身體行動所投射的靈光,再一次認知土地所深藏的神秘性,言說土地的難以言說性,以及土地面向歷史敞開的多重媒介性。也在這一意義上,土地詩學的論述重新規劃了我們對世界,對空間的有限與無限的認知。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5折$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