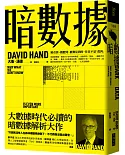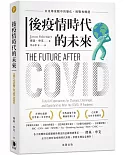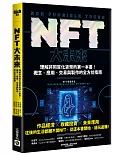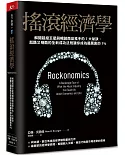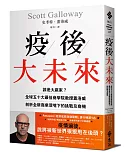前言
2018年中期以來,中美兩國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貿易摩擦。實際上,我在於2018年元旦發佈的新書《樞紐》中就已經談到這種可能性了。
我在《樞紐》下篇討論中國與世界經濟關係的部分提出,中國的經濟成長係基於西方最新一輪創新經濟的拉動,其間一系列結構性的特徵,使得在不出現實質性技術變遷的前提下,全球中低端製造業向中國的轉移是終局性的。因此,中國的經濟成長帶來了全球經貿結構的深刻變遷,從沃勒斯坦所說的“中心—外圍”結構變為一種“雙循環”結構,中國的製造業成為一個中介性的“樞紐”,銜接起西方發達國家的創新產業及高端服務業與不發達國家的原材料產業。這種結構變遷會引發全球秩序以及其他國家內部的一系列不均衡,從而籲求一系列治理秩序變革。如果變革不能向前推進,便有可能引發貿易摩擦。
未料到,《樞紐》一書出版不到半年,大規模的貿易摩擦就真的出現了,並且規模迅速升級到超出所有人想象的程度。一時間,網上滿是中國製造業面臨貿易摩擦的嚴重衝擊,大量製造業工廠正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規模轉移的消息,中國經濟似乎正面臨重大危機。很多人質疑我在《樞紐》中的說法,認為現實已經狠狠地駁斥了這本書。
從純粹的理論分析來看,我認為這種大規模轉移不大可能。因為我所論證的支撐中國供應鏈網絡的很多條件並未因貿易摩擦遭遇實質性挑戰,海外也沒有哪個國家有條件承接中國如此大規模的供應鏈網絡轉移。而在今天的全球經濟邏輯之下,僅僅轉移工廠而不轉移供應鏈網絡,是構不成實質意義上的轉移的。但是這種理論分析倘若沒有足夠的實證研究支撐,說服力仍然有限。
於是,在2019年,我與研究團隊的夥伴們一起從北到南對越南做了深入調研。我們跑了河內、海防、胡志明三個大城市,以及分佈在北方和南方的三個主要工業省份,拜訪了四個工業園、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派駐越南河內和胡志明兩個城市的分會,又採訪了河內的一家律師事務所、七家在越南的中國商會。我們還拜訪了從高科技到低科技橫跨多種產業、從跨國大公司到地方小工廠橫跨多種規模的近二十家企業,若干位越南工人及越南經理層,以及幾十位在越南打拚的中國人。此外,我們還採訪了越南的政府基層官員、兩所大學中的多位學者,甚至在一家中餐館吃飯時,遇到的一位會說流利中文的越南老闆娘都成了我們了解越南民情的訪談對象。
在去越南之前,我們先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對中國企業做了深入調研,以便獲得必要的預備知識;從越南回來之後,基於新獲得的信息,我們又逆向回溯到國內的供應鏈網絡上游,到珠三角以及廣西中越口岸地區做了深入調研。
大半年的深入調研以及與研究團隊夥伴們的反覆討論,讓我有了巨大的收穫。調研基本驗證了我在《樞紐》中提出的“樞紐”、“雙循環”結構的假說,同時讓我能夠對假說做出重要的迭代升級,把很多思考向前推進了很遠。田野調研不僅讓我對經濟活動的微觀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還讓我發現了很多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存在。
基於調研形成的理論收穫,可以總結為如下四點。
第一,製造業向越南的所謂“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事實不會發生實質性變化。
在越南和珠三角的調研告訴我們,從中國向越南轉移的,並不是某些行業中的整個產業,而是該產業生產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環節,主要是對供應鏈需求較低、人工成本佔比較高的環節,通常是最終的組裝環節。其他環節很難轉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國的供應鏈網絡中。結果就是,生產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環節往越南轉移得越多,對中國這邊供應鏈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國和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之間從而形成了一種深度的嵌合關係。這樣一種轉移,還是稱之為“溢出”更恰當一些。我們在新聞中經常看到,伴隨著貿易摩擦,越南對美國出口有了大幅增長,中國對美國出口有了大幅下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對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長。在新的生產邏輯下,過往理解問題的很多方式都得加以調整。
第二,能夠轉移的環節,和通常所說的高技術產業還是低技術產業沒有關係,而是和不同梯次工業革命所出現的產業有關係。
和通常說的產業本身的技術水平高低無關的最根本原因在於,今天各國之間已經是在工序層面的跨國分工,複雜產品很少能在單一國家或地區內部完成全部生產環節。高技術產業的生產環節中不都是高技術環節,其中的低技術環節如果符合第一點的條件,是有機會轉移走的。
但是在轉移過程中,不同梯次工業革命所出現的產業,其轉移邏輯是不一樣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形成的重化工業相當於工業經濟中的基礎設施,由於一系列原因(詳見書中內容),重化工業基本上終結在中國,無法向東南亞轉移。第三次工業革命形成的電子產業,在可預見的未來,它所依託的最大規模供應鏈網絡也會留在中國——畢竟其所依賴的經濟基礎設施在中國,但是電子產業中的組裝環節會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轉移。轉移出去的這些環節,會與中國的供應鏈網絡保持深度的嵌合關係。第四次工業革命形成的信息技術產業,從它的核心技術創新和軟件等方面來看,美國起著主導作用;從信息技術的硬件製造方面來看,這種製造是要通過電子產業完成的,中國加上東南亞會在其中起主導作用。
第三,推動中國供應鏈網絡向東南亞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國民間的力量。中國的民間經濟和社會帶給我特別多意外的發現和感動。
我在調研中注意到,貿易摩擦越嚴重,民間經濟就越努力加強自救。所謂自救,很多都是生產環節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轉移,因為那些地方無須面臨美國的高關稅。但是,在轉移的過程中,只有組裝環節能夠出去,其他環節仍然需要依託中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而中國供應鏈網絡的活力,也來自民間經濟。因此,貿易摩擦的結果是,中國的供應鏈網絡會加速向海外擴展,但這一過程的主要動力來自民間。
至於向海外“走出去”的具體載體,在各種海外大項目之外,我們通常關注到的都是那些外出設廠的企業——不管是出於全球佈局考慮而主動走出去的國際大公司,還是跟隨大客戶走出去的小供應商企業。但所有企業都是基於具體的“人”的活動才運轉起來的,過去國內對於“人”的層面關注不夠。
我們在越南的調研中發現了國內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國幹部”這個群體。所謂“中國幹部”就是,無論什麼“資”的企業(主要是台資),只要是把工廠從中國大陸遷到越南的,則中高層管理人員基本上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這群人自稱“中國幹部”,是個有幾十萬人的群體。中國幹部是把中國的供應鏈網絡與越南的組裝環節銜接起來的重要微觀載體,他們在打拚的過程中擁有了大量基於跨文化的調適能力而演化出的管理技巧,掌握了大量可實踐但難傳授的隱性知識,是具有巨大價值的海外智慧寶庫。如此重要的群體居然在國內鮮為人知,期待我在書中的討論能夠引起國人對他們的關注。
第四,是“溢出”而非“轉移”的根本原因在於,隨著技術、公司組織形式以及生產邏輯的演化,經濟空間和政治空間越發分離。經濟空間以各種方式穿透國界存在,政治無法真正約束這種經濟空間的運轉。
信息技術天然地是穿透國界的,這個我們都很熟悉了。而製造業中的生產流程也越發成為一種跨國性的存在,這跟我們過去所熟悉的不一樣了。過去我們認為,無論生產什麼東西,生產過程中的大部分環節都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完成的。但是在今天,就複雜產品而言,生產過程中的大部分環節是在幾個國家中通過跨國配合完成的。倘若把一件複雜產品從元器件到最終產品的全生產流程所經歷的物理空間稱作生產流程所依託的經濟空間,這種經濟空間已經是高度穿透國界——也就是穿透政治空間的了。
從國內層面著眼,這帶來了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民間經濟的運行邏輯和政府政策的邏輯越來越分離成兩條線。政策對民間經濟的影響機制,跟過去已經大不一樣了。從國際層面著眼,這還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以國家為單位來思考經濟問題已經越來越沒有意義了。而現在的各種國際經濟治理秩序,比如WTO(世界貿易組織)、IMF、世界銀行,以及各種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都是以國家為單位組織起來的,國際經濟治理秩序在運轉上也就越來越有問題。
世界必須找到新的治理辦法,新辦法的根基必須與新變化的動力基礎相匹配。是經濟活動穿透國界才帶來了這些問題,但經濟活動的基本單元並不是國家,而是商人,所以新的治理辦法是需要由商人來主導的。回看歷史,商人秩序曾經與政治秩序纏繞著共生演化,推動人類秩序不斷發展,中世紀以德意志商人為主導的商人秩序——漢薩同盟就是個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到了近代的主權國家時代,政治秩序變得過於強大,商人秩序被政治秩序遮蔽了。而今天,隨著技術和生產的變遷,商人秩序很可能走到了需要重新站到歷史前台的時刻。我在書中做了個大膽的構想,就是構建“東亞漢薩同盟”,它標示著我對未來可能形成的秩序的某種構想。
貿易摩擦是一種很有趣的“極端”環境,它可以把很多平常狀態下易變的、擾亂人視線的東西都拂去,底層不易改變、在更大程度上規定著演化方向的東西,會在這樣的環境中逐漸浮現出來。
正是在這種“極端”環境下,我們可以發現民間經濟正在“溢出”的強大動力;也是在這種“極端”環境下,我們會被促使著去構想未來新的秩序可能性。對未來所做的這種構想,需要我們有深遠的歷史感,因為,真正的歷史感從來都是指向未來的。在實踐的延長線上,這樣的一種思想,就是最深刻的歷史實踐!
在調研回來後,跟朋友們討論自己的思考的時候,有朋友提出一個意象,非常貼合我調研的感受,那就是——原力覺醒。“原力”是《星球大戰》電影裏的一個概念,指的是最底層的動力。原力覺醒,就是說長久沉默的最底層動力行將浮出水面。
在貿易摩擦的背景下,在當下動盪不堪的國際格局中,反倒更容易看清——在今天,中國與世界經濟關係中真正的“原力”,就是商人秩序的力量。這個“原力”一直存在,但長期沉潛,久未獲得自覺。到了今天,技術和生產的演化很可能會把它推到歷史的前台,“原力”應當“覺醒”,“原力”也必須“覺醒”。
施展
2019冬至夜,於北京
繁體版序
2018、2019兩年,中美貿易摩擦的戰火一路蔓延,一時之間國內有著各種憂慮的聲音,擔心中國會因為貿易戰而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而越南製造業似乎正在迅猛崛起,有取代中國的趨勢。一旦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則中國有可能陷入失業潮,社會可能陷入劇烈動盪。
但我對此並不擔心,原因在於我在前幾年出版的《樞紐:3000年的中國》一書中對中國製造業發展邏輯的分析。在我看來,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美國開啟的創新經濟轉型產生了生產流程大規模外包的需求,這個需求剛好與中國在那個十年中的一系列歷史節奏發生了時間耦合,於是促成了中國製造業的迅猛崛起。而中國製造業在崛起之後,促成了生產環節中企業組織形態的深遠變化,生產企業開始演化為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體系,形成了一種樂高積木式的生產—創新機理;供應鏈網絡的運營效率,成為生產過程中綜合成本控制能力的基礎,勞動和土地等要素價格在綜合成本中的佔比已經大幅下降。供應鏈網絡的形成,本身又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在多重要素發生時間耦合後自生演化的結果,其他國家極難複製,所以中國在中低端製造業層面在世界上獲得了壓倒性優勢。
在這個分析中闡釋的一系列社會和經濟邏輯,並不會因為貿易摩擦就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所以我並不覺得貿易摩擦會讓中國喪失掉世界工廠的地位,後來的時勢發展也證明了我當初的判斷。
但光是理論分析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更細緻的實證研究支撐。所以我在2019年隨同研究團隊深入到越南進行調研,基於越南的調研,再回溯到珠三角和長三角的供應鏈上游,調研的結果就形成了您手中的這本書《溢出》。我在微觀層面上看到了,所謂的中國製造業向外的“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
在微觀調研的過程中,我還進一步注意到了中國在兩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所形成的人才堰塞湖效應,它在人的層面上帶來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源動力,以及積澱出了製造業上的很多“隱性知識”,這些都是中國製造業的力量所在。
沒想到,《溢出》簡體版剛剛發佈之際,新冠疫情猛然爆發了。在2020年2月份疫情勢頭最為兇險之際,很多人都陷入了深深悲觀,覺得這回中國製造業可能真要扛不住了。但當時我的立場是一種“謹慎悲觀”,畢竟我所觀察到的中國製造業所依憑的各種力量根基都還在,所以我判斷,除非疫情僅僅局限在中國,並且持續四五年的時間,否則中國製造業仍然不會受到實質性的重創。
幾個月後,中國的疫情逐漸走出谷底,其他國家卻陷入了水深火熱。到了下半年,中國經濟不僅收復了上半年的失地,並且由於其他國家的生產嚴重受阻,中國的製成品出口比此前還有了更大的增長。於是很多人又進入了一種強烈樂觀的情緒,覺得這是中國的一個重大機遇。但這會兒我的立場是“謹慎樂觀”,中國製造業只不過是在疫情的下半場發揮了自己的比較優勢而已,但中國的比較劣勢並不會因此就克服了;甚至,如果中國在這個階段太過高調引人反感,導致西方強化在一些關鍵領域“脫鉤”的決心,中國的比較劣勢還有可能放大。(而這本繁體版就收錄了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我的上述分析。)
也就是說,在剛開始疫情很悲觀的時候,在我看來,中國製造業遠比那些特別悲觀的人所想象的更加強韌;但是在下半年疫情很樂觀的時候,在我看來,中國製造業遠沒有那些特別樂觀的人想象的那麼強大。
這樣一種無論是悲觀還是樂觀,始終抱持“謹慎”立場的姿態,自然是左右不討好,我的一些研究和分析發表出來之後,其引發的各種爭議也在我的預料之中。在一個劇烈變遷、高度撕裂的時代,真正能夠討好觀眾的是鮮明勁爆的立場,而不是冷靜理性的分析。但越是這樣的時代,就越是需要一些冷靜的聲音和理性的思考。我不敢自詡能足夠好地做到這些,但我確實在往這個方向努力,只希望這些微弱的努力能夠留下一些有用的東西。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施展
202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