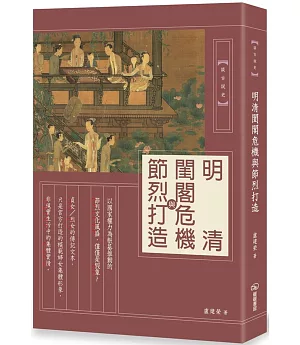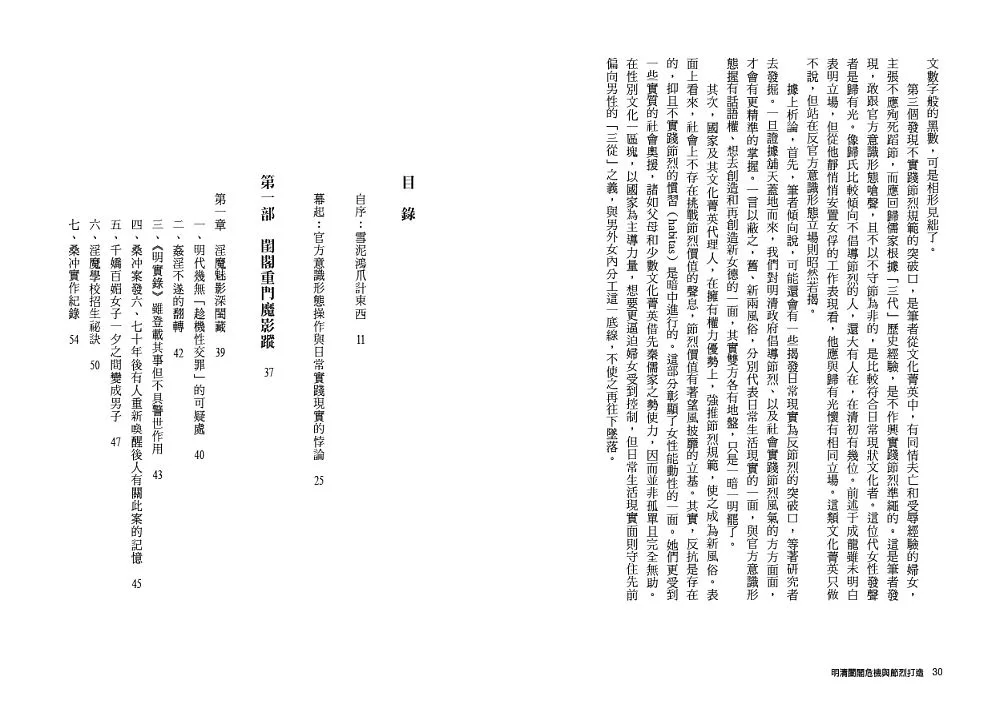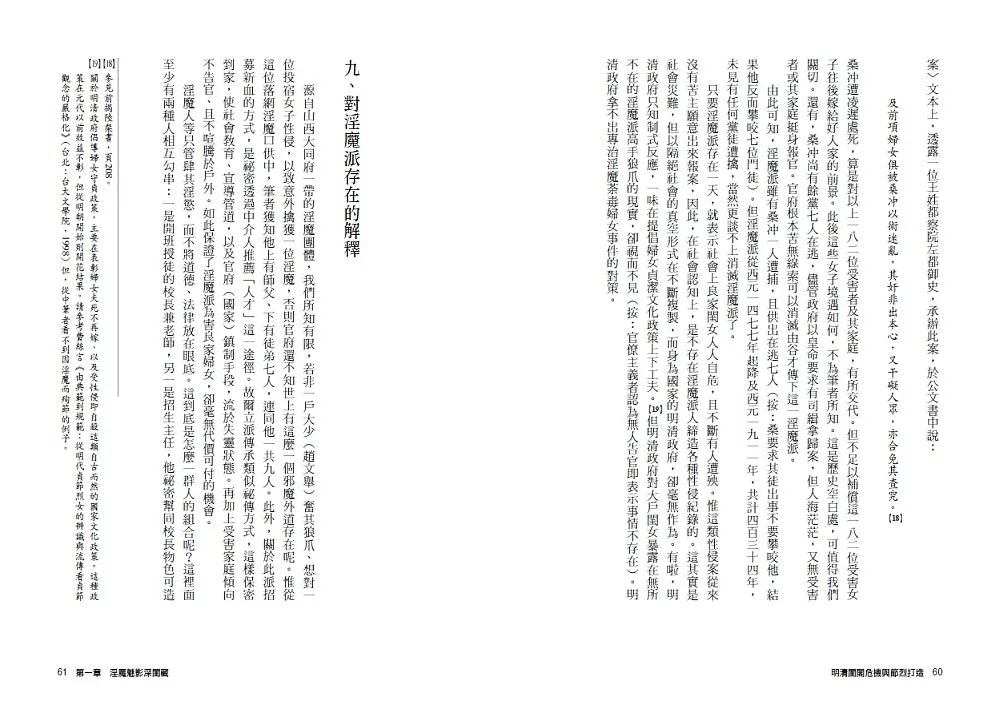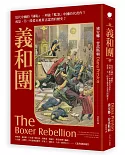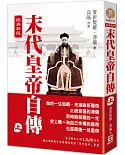幕起
官方意識形態操作與日常實踐現實的悖論
一
中國男女地位不平等,自古就有片面要求女性在一生三種社會角色扮演上,要依從男性(「三從」),而在勞務付出上,要謹守「男主外,女主內」分工原則。這在帝制時期,更形成國家意識形態,由國家部門(包含代理它的文化菁英)全力播放。到了公元第三、四世紀,更是大為加碼,對女德要求,只許一生結婚一次,這是說女性一生只能有一位性伴侶,而且是在婚姻條件下。萬一遭遇性暴力,為了這突發強加的性關係,女性只有以死捍衛清白。從三、四世紀直到十三世紀,國家及其代理菁英打造以上「節烈文化」,成效有限。但十三世紀蒙古人殖民統治中國時,因引進蒙古婚俗:「收繼婚」,意外導致中國婦女遇夫死亡,群趨守寡一途,否則就要改嫁給小叔。這造成守寡風熾,寡婦量暴增。時為十四世紀事。到了十六世紀中葉,女性在因應性侵後處境上,群趨赴死以衛貞節一途。這造成貞女烈婦數陡漲的現象。至此,以國家權力為根基的節烈文化推動,看樣子大獲全勝,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二○年代才全面退潮。
二
在片面要求女性守節上,國家享有話語權,幾無任何形式上的針對性言說,可與國家抗衡。如此,女性只能遵從節烈規範一途嗎?筆者認為未必。在表面可見的文化領域裡,我們的確看到,支持節烈文化態度的行動者,幾乎成為促進婦女守節的強大奧援。這些擁節烈文化的人中,有私人領域的父母和公共領域中的在地知識分子和官員。但父母在對待自家女兒和別人女兒(即媳婦),於實踐節烈規範上是有矛盾的。父母總是流於寬待自家女兒,而嚴待別人女兒。當女兒遇夫亡或遭性侵,為人父母者不是熱衷幫女兒再嫁,就是極力掩蓋女兒受到性侵的事實。反過來,父母成為舅姑,在遭遇兒子死亡,或是媳婦慘遭性侵的關頭,這時的父母多半要求媳婦守寡在家,或是殉節以榮耀家門。父母對節烈規範,要求女兒或是對待媳婦,產生嚴重悖論。
這樣的文化悖論,關係到中國在實踐節烈上,是依託國家去創造或再創造新的習俗,這是顯性的。相形之下,反對實踐節烈文化,是一種委婉而暗地的反國家文化政策,但它是以一種隱性的方式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反節烈實踐的,可追源到十三世紀之前中國根深蒂固的舊習俗。那時節,婦女在婚姻和家庭文化領域中,擁有較大能動性,可以夫死再嫁,更甚至夫在因協議離婚而改嫁。而不幸慘遭性侵的女性,社會也能有所包容。
三
實踐節烈的風行,是後生物事,它們並無法吞噬以前不實踐節烈的舊習俗。然而,實踐節烈由國家以正規管道在強推,使它居於明顯可見的正統文化位置上,而無視節烈的舊習俗,要在日常生活場景上存活,只能以流入地下方式繼續操辦。而就在出版和印刷這一文化區塊裡,讀者只能讀到實踐節烈的故事和思想,節烈的能見度和曝光度籠罩整個出版市場。這造成今天我們所習知的節烈風熾的假象。
事實並不如此。拒/抵反節烈的舊習俗並沒有在節烈風熾的近六百年完全絕跡!它們是存在,只是不被紀載,人們就誤以為,拒/抵節烈的具能動性的婦女早已一去不復返。
這一顯性新習俗與另一隱性舊習俗之間的拉扯,是筆者大膽提出的假說。在此之前,前賢多以線型直線史觀去觀察中國官方提倡、實踐節烈規範這段歷史,多認為節烈文化至明清時代而大倡。可是,筆者經研究指出,一方面擁節烈文化者在明清時代固有亮眼數字表現,但比之反節烈文化者量體數之不盡的天文數字般的黑數,只是小巫較大巫。沒錯,這個反節烈文化的黑數,是不易被查知的。筆者是經由一些線索才逐漸認清,舊、新習俗形式其呈現方式,是以反節烈文化和擁節烈文化的可見格局在拉扯之中。這是對節烈課題的一種新的詮釋。
四
在筆者長年研究打造節烈文化這一議題過程中,逐漸懷疑不實踐、或反對實踐節烈規範的力道,相當巨大。當然,這是一點一滴地摸索,才逐漸清晰的。最早,筆者接觸十一世紀以前,各式節烈文本的製作,確定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節烈規範,其在社會受到遵行的情形,並不踴躍。相反地,父母對於女兒遇不幸婚姻的處理,多半成功幫助女兒改嫁、或再嫁成功。這是生活現實風行的,是站在與官方倡導節烈的對立面。易言之,生活現實的習俗與官方倡議的高標女德其話語,形成巨大反差!這是一個重大發現。另一個重大發現是,官方製作的節烈文本,在抗拒性侵這一情節編織上,摻有造假的手法。亦即,敘及女性在受辱當頭,會有餘裕辱罵施暴者的文化卑下,或不文明。這番話,筆者特稱之為「文化罵戰」。筆者直接拆穿,文本作者是事發現場的缺席者,不可能得知受害者向施暴者如何振振有詞。文本作者這種造假的伎倆,相當不合情理之甚。特別是施暴者為非漢族男性的話,他們如何聽懂文明的漢女在向其作文化喊話的內容呢?
之後,筆者注意到明代有一種專門訓練少男成為繡花婆的學校。這些少男畢業後,專事出入大戶女兒閨房,名為教少女繡花技藝的「女紅」老師,實為趁機偷香竊玉的淫棍。這種類型的性侵事件,均因苦主是地方名望者流,加上此類「家門不幸」之事不為外人所知,這種本應是城裡人們談資的不幸事件,都被苦主給掩蓋下來。這些苦主掩蓋行動的本身,意味著他們是反節烈規範的行動者。苦主家庭的父母為了女兒將來幸福計,寧可假裝女兒沒發生過任何不幸。所以,在父母和女兒合謀之下,他們面對女兒受性侵事件,決定要求女兒切莫實踐節烈規範。在帝國四處遊走的淫棍通常得售所圖,從未付出過受懲的代價。但有位淫棍例外。他叫桑冲,在明成化年間被官府查獲。在招供之下,他於十年遍遊三省過程中,性侵一八二位大戶閨女!官府更從他身上,查知他受訓學校校長也是性侵老手,並訓練不少徒弟。而桑冲於犯案前先訓練七位徒弟,這才下山各自分途去獵艷的。筆者稱此女紅男校為淫魔派。他們荼毒天下、毀盡多少良家女名節,卻始終逍遙法外。這是筆者找出不實踐節烈舊風俗的一大突破口,這表示官方意識形態穩居優勢地位的同時,反官方意識形態的舊風俗,仍然頑強存在著,而且以流於地下的策略雄踞在日常生活現實中。支持節烈規範的文化菁英有著官方護持、表面上取得話語權,但日常實踐上暗中存在反節烈的舊俗,兩者各有文化領域,且做到「河水不犯井水」的平衡態勢!筆者必須指出,不實踐節烈的黑數,恐大過節烈實踐者的正數,還多得多。去調出明清龐大實踐節烈數據,說超過之前實踐數據,便斷稱明清節烈文化風盛。這是研究此一議題的一大迷思。
又一個發現不實踐節烈規範的突破口,出現在戰地常見的敵我雙方從事超限的姦淫擄掠女口的作為,在戰爭結束後,龐大受俘女性等待官府遣送回籍安置。這些戰地受俘女性,意味受過性侵卻倖存下來,而成為日後官府戰後善後的一大行政負擔。筆者特舉清初三藩之亂期間,于成龍先後任湖北黃州知府,以及福建按察使任上,我們看到于氏於戰後安輯流亡行政措施中,有大量遭俘婦女需要他去從事送返原籍的安排。在戰地裡,湖北迄未出現一則節烈故事,而福建留下數十則節烈故事,這讓筆者警覺到事情原委或許如右:戰地即令遺有實踐節烈的樣本數,但比起不實踐節烈如天文數字般的黑數,可是相形見絀了。
第三個發現不實踐節烈規範的突破口,是筆者從文化菁英中,有同情夫亡和受辱經驗的婦女,主張不應殉死蹈節,而應回歸儒家根據「三代」歷史經驗,是不作興實踐節烈準繩的。這是筆者發現,敢跟官方意識形態嗆聲,且不以不守節為非的,是比較符合日常現狀文化者。這位代女性發聲者是歸有光。像歸氏比較傾向不倡導節烈的人,還大有人在,在清初有幾位。前述于成龍雖未明白表明立場,但從他靜悄悄安置女俘的工作表現看,他應與歸有光懷有相同立場。這類文化菁英只做不說,但站在反官方意識形態立場則昭然若揭。
據上析論,首先,筆者傾向說,可能還會有一些揭發日常現實為反節烈的突破口,等著研究者去發掘。一旦證據舖天蓋地而來,我們對明清政府倡導節烈、以及社會實踐節烈風氣的方方面面,才會有更精準的掌握。一言以蔽之,舊、新兩風俗,分別代表日常生活現實的一面,與官方意識形態握有話語權、想去創造和再創造新女德的一面,其實雙方各有地盤,只是一暗一明罷了。
其次,國家及其文化菁英代理人,在擁有權力優勢上,強推節烈規範,使之成為新風俗。表面上看來,社會上不存在挑戰節烈價值的聲息,節烈價值有著望風披靡的立基。其實,反抗是存在的,抑且不實踐節烈的慣習(habitas)是暗中進行的。這部分彰顯了女性能動性的一面。她們更受到一些實質的社會奧援,諸如父母和少數文化菁英借先秦儒家之勢使力,因而並非孤單且完全無助。在性別文化一區塊,以國家為主導力量,想要更逼迫婦女受到控制,但日常生活現實面則守住先前偏向男性的「三從」之義,與男外女內分工這一底線,不使之再往下墜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