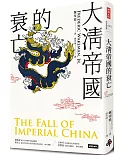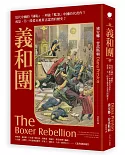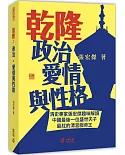前言
近年來書信和日記文獻一直很受歡迎,出版界也樂於推動刊行,利用這兩種特色史料研究近代史漸成方興未艾之勢。的確,與檔案文書、報刊、方志等資料相比,書信、日記類史料別有意味,這源於後者最本質的屬性──私密性。
家書和友朋書札是最典型的私人文獻。書信讀起來親切,語言沒有雕飾,意隨筆到,多是坦露衷腸之言。這些信函原本有很強的私密性,當初只是為了完成即時傳遞資訊的目的,並無公布與眾的考慮。甚至有些內容生怕他人知道,收信人閱後還被要求「付丙」、「付祝」(燒毀)。在歷史學家看來,這種「講私房話」的原始文獻,一旦被保存下來,披露出來,可信度更高,因而備受青睞。與「密信」相近的還有「密電」。電報傳入中國後,書信傳遞消息的速度已大為遜色。時至清季,無論是官家還是民間,凡電報線所到之處,緊要事情使用電報告知已很普遍。官員間甚至有固定的密電碼,用以保密。在史學家眼裡,這類「密電」的史料價值與「密信」並無二致。
與之相比,私人日記是「排日記事」,一般是當天所寫,也有數日後補寫的,經過逐日、逐月、逐年記錄,累積而成。這種在光陰流轉中逐步形成的編年體文獻,將作者的言行、見聞、思想乃至情緒,隨時定格、固化後,「鑲嵌」在特定的「地層」中。日記的「原始性」也因此而與眾不同。比起書信,日記更像著作,作者可以從容記述,一旦有了將來公諸於世、流傳下去的想法,寫作就會多幾分思量,難免有掩飾、隱晦的痕跡。儘管如此,曲筆之處也會被即時保留在日記原稿中,日後也不能再隨意更改。對研究者來說,內容可信與否,可以再做考量,日記的原始性則無可懷疑。一般情況下,日記也是「祕不示人」的私密文獻,往往是作者身後才被後裔、門生公布出來,或者遺落坊間被外人收藏並刊行的。一部日記中某些零星記載可能會在不經意間解決一樁長期懸而未決的歷史疑案,每令史學家激動不已,雖然這裡有可遇不可求的機緣因素。
本書收入的十三篇文章所依據的書信、日記材料或源自筆者供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或由私人藏家提供,或據已刊文獻,大致情形如下:
(一)利用書信、日記等對戊戌變法及政變史實的一組考訂,包括《汪康年師友書札》、《鄭孝胥日記》、廖壽恆《抑抑齋日記》等文獻。筆者對戊戌年保國會解散原因、戊戌八月御史楊崇伊奏請慈禧訓政、清廷捉拿康黨與軍機四卿、處置戊戌六君子等內幕情形,進行了考訂和糾謬。總理衙門總辦章京顧肇新致其兄顧肇熙家書對一八九七年中德膠州灣交涉、一八九八年春張之洞入樞受阻、翁同龢開缺原因、總署議覆康有為〈第六書〉、政變後張蔭桓革職原因及為光緒皇帝徵醫等問題,都有記述和評議,臧否人物、評議時局,多是局內人言,可糾正以往成說之訛誤。榮祿書信則披露出戊戌政變後榮祿、剛毅兩位滿洲權貴在軍機處明爭暗鬥背景下新貴袁世凱的艱難處境。
(二)對丁未政潮前後政局和慈禧、光緒死因的研究。近代史所藏張之洞檔案中的電稿原件存量不少,拙文選取部分電稿,對丁未政潮後梁鼎芬兩次參劾奕劻、袁世凱的原委進行考訂,尤其是第二次參劾行為,導致已經入樞的張之洞處境尷尬,引起張的責難,張、梁關係由此疏遠。有關光緒皇帝的死因,近代以來不少筆記、野史認為系遭謀害而死,通過對清宮檔案及軍機大臣鹿傳霖、軍機章京許寶蘅以及內閣侍讀學士惲毓鼎日記的綜合研究,種種跡象表明,光緒帝應係病死無疑,謀害之說不可信。清末大臣陸寶忠的未刊日記也是反映庚子之後朝局的珍貴資料。
(三)對辛亥鼎革之際政情與社會的反映。許寶蘅在清末任職軍機處、承宣廳,民國初年又任總統府、國務院祕書,長期活動於政治中樞,他的日記對袁世凱在光緒、慈禧去世、辛亥清室讓位、民初獲取大總統職位的活動均有零星記載,除了披露內幕和細節,對今人瞭解鼎革之際政治演化過程有不少新啟示。民初官員黃元蔚是戊戌維新志士康廣仁之婿,這種特殊身分,使他與康有為、梁啟超、陳昭常乃至其他粵籍名流具有非同一般的關係,近代史所藏黃元蔚致其妻康同荷的家書,對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前後的北京政局內幕及康、梁等粵籍人士的活動有不少記述,有助於豐富人們對北洋時期政治生態的直觀感受和認識;由康同荷保存下來的康有為三封親筆信函,也是瞭解保皇會時期康氏思想的珍貴文獻。
(四)近人郭則澐自訂年譜稿本。此件由譜主之孫郭久祺先生保存並提供,也是私人著述。郭則澐(號龍顧山人)是上世紀二○至四○年代活躍於京津地區的遜清遺老,年譜記述了譜主六十年的生平經歷,歷史資訊豐富,對研究清末民初政局、派系鬥爭、遺老活動等問題都有無可替代的學術價值。
(五)對葉德輝致易培基書信的考訂和釋讀。葉德輝與易培基在民初的交往情況,因材料所限,學界歷來關注甚少。從近代史所藏葉氏致易的十六封未刊書札看,二人不僅學術志趣相近,政治立場也大致相同;他們身上都有狂狷孤傲的鮮明個性和書生本色,這也註定二人人生悲慘結局有驚人的相似性。
本書關注和研究的都是具體問題,可能在某個層面澄清了一些疑難,推進了某些研究,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既往的歷史認識,但是,能夠與讀者分享的收穫也是有限的。研究經驗告訴我們,對書信、日記這類私密文獻也不能太過迷信。一味追逐那些揭示內幕祕辛的珍稀史料,並非史學研究的坦途。史料類型各異,本質卻是平等的。說到底,研究中沒有哪一類史料能夠包打天下。書信、日記雖是考訂歷史細節的絕好材料,也要與其他不同類型的資料對應互證,方能在人們探求歷史真相的努力中,顯示其獨特價值。當然,這還需要我們不斷充實理論素養,拓寬學術視野,在宏大精深的理論思維關照下,珍貴的史料才能被「點石成金」,發揮出最耀眼的學術意義。
馬忠文
二○一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