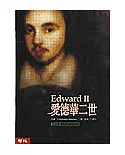推薦序
我是誰?他是誰?
鍾適芳(音樂製作人、策展人)
收到俊耀來信邀我寫推薦序,又驚又喜。我非劇評也非劇場人,只是窮劇場一名忠實觀眾,我只能猜想,或許因為我的工作跟「聲音」有關,而窮劇場作品中音/聲的典故與譯義,是最為觸動我之處。
音聲在俊耀的作品與表演中,呈現液態流動的敘事,聲軌與聲軌之間漫溢、交疊、衝撞、和鳴、相互渲染,不再是單一軌道上的聲調抑揚。《死亡紀事》、《大世界娛樂場II》、《親密》,這三部我喜愛的劇作,正是這樣完全的聲音紀事與敘事。經常在華文劇場單音調(monotone)唸白間想要逃離的我,唯有在「窮劇場」以音聲肢體建構的時空景深裡,遺失當下的我,化為劇中一角。
關係自己成長的背景,我對移民社會的身份問題較為敏感,也因此想藉此文多談一些《死亡紀事》這部劇作,如何劇烈擾動我對馬來西亞族群問題的反思。在《死亡紀事》這部作品中,「音聲」建築起時間與空間的向度,又分立為多重角色。那些透過身體發造,從語言到暴力的聲響,是人類文明衝突與諧睦的集合,是社群集體與個人心理的捏塑,同時也用以輪廓物件。這樣全面鋪陳的音響性,使得劇場原本有形者被抽象,而聲音這原本無形者成具象。
這部精煉的劇本也試圖探討一個棘手的問題——誰是馬來西亞人?馬來西亞的族群課題,盤根錯節的異同糾葛,很難從單一線節解開。佔人口比例第二位的華族,被視為一個具有經濟優勢的群體與他者。然而在承燊及俊耀的劇本中,他們細究了同一族群中個體與群體的差異,在方言-華語、穢語-知性、詛咒-祈語、伊斯蘭-佛道,兩極交鋒的快節奏行進下,我們很難再將「馬華」視為一體,而「馬來西亞」被打散成族裔之外,更為細碎的拼圖。
劇中一段台詞的提問,寫照了族群、語言群落、社經群體間的隔閡,以及形成馬來西亞族群分歧的多層因素:
弟弟:......阿爸的遺體歸屬,究竟是宗教問題法律問題?
敘述://還是種族問題政治問題?
弟弟://社會問題家庭問題倫理問題?
敘述://還是認同問題存在問題?
弟弟://利益問題制度問題?......所有問題都打了結,相互糾葛,到底我要怎麼問怎麼看?
馬來裔學者與社運領袖Syed Husin Ali在其文集《馬來西亞族群關係——和諧與衝突》(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 Harmony and
Conflict)的〈族群關係之輪廓〉一文中指出,造成馬來西亞國民分裂與衝突的四大課題為:「一、新經濟政策;二、馬來主權;三、語言與教育;四、宗教與文化」。該文撰寫於2009年,正是爭屍案等宗教課題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Syed也同時在他其他論述中提醒,馬來西亞各族群內部的差異,包括「社會、經濟、宗教、語言的個別差異」,而當代社會的「經濟、行政、教育」制度的建立,也促使新階級崛起。
透過《死亡紀事》多重角色的建立,我們可清晰探見一個華族底層家族的樣貌,也論證了Syed的觀點。亡者「陳大揚/Hassan Tan bin Abdullah」生前為了脫離弱勢階級尋找新機,改宗異教,只為獲得符合「新經濟政策」利益的合法身份。
或許我們可以試著這麼理解,族群衝突不是族群間因著本質差異所釀成,而是體制所形成的文化衝突,經由政治操弄,虛構出差異構成的利益衝突,進而放大為族群間不信任的恐慌。許多不公義的根本其實源於制度,從殖民時期的帝國主義,到當今資本主義下的新帝國擴張,階級問題在馬來西亞實非族群問題,而是跨族群的問題。
一具華人的「屍體」,在馬來伊斯蘭信眾與華人佛道家族之間,所引發的荒謬爭執,放大來看,也正是馬來西亞族群衝突的諷喻。「關鍵證物」(屍體)的消失,是否也意指著族群間相互指控或試圖剝離的「身份」,其實是種虛構與想像?想像的族群身份及認同,也構成了另一個想像的對立族群。
我想起馬來西亞國歌中的幾個馬來文詞彙:「祖國/國家」(negara)、「土地」(tanah)、「上蒼」(tuhan)。在馬來伊斯蘭為中心的體制下,祖國與土地是否也隱匿著某種專斷?《死亡紀事》的「屍」是否也暗喻,單一族群認同、僵化的文化分界,早已不合時宜,一如所有國家在國歌中的宣示。而「屍」,那與華人祖脈最後的連帶,被遺落後,可否割斷?被月光穿透的身體,那真實的存在,又是誰?
面對單一語系的觀眾群,窮劇場毫不退卻地混雜語言及語法,作為魔幻寫實的途徑。看似個人或地方性的主題,其實遍及族群、階級與家庭關係,這是我在其他臺灣或華文劇場所少見。如今,三部主題各異的劇本出版了,意味著文本的開放,可以無聲,也可無限轉譯。
期待「窮劇場」的繼續擾動,不准許我們安逸。
自序
劇場這條路我走得很慢
高俊耀
細細回想,一開始是閱讀。喜歡讀小說,聽曲折離奇的故事,看跌宕起伏的人生。想像自己下一步的左轉、下意識的回頭、下一秒鐘的抉擇,生命總在遠方,幻想無遠弗界。跟著就是看潮州戲和電影,任性地把夢變闊變長變深,直至,再也按耐不住,就開始寫。寫、寫、寫,如磨墨般磨練自己的筆。寫身邊的人、寫讀到的新聞、寫腦袋裡藏不住的一切。
多年之後看了一部電影《里歐洛(Leolo)》,「因為我夢想,我不是我」,沉浸在閱讀和書寫裡,某種孤獨所構造的城堡,瞬間把自己拉回青少年的樂趣和喜悅中。
書寫之後就發現自己想演戲,想化作筆下那個人,經歷種種脆弱與堅韌、悲欣、狂熱與傷痛。讀了戲劇系後,就理直氣壯地寫劇本,當導演,具體實現「我不是我」,探觸想像邊界。為甚麼自己這麼不想成為「自己」呢?或許隱隱意識到內在有個非常惶恐,不曉得如何應對急遽變化的小孩吧。也或許,有個陰鬱暗啞的自己待在隱蔽處,需要化為他人才能發出聲音。更或許,想透過筆觸和肉身,去接近身邊那些無法述說自己的人們,那些被遺忘被拋下的人們,那些徘徊在愛、記憶與恐懼的人們。
這些年回看,起步很早,走得很慢,實踐和探索當中,由編而演而導,定稿總在下一稿,豁然發現,磨練的不只是筆,還有意志,和自己的心。
儘管如此,喜幸一路有夥伴同行,和家人扶持。暧暧遠人村,依依墟里煙,世界的運作總是靠如此細微的相互支撐而存在。感謝聯合編寫劇本的阿忠和承燊,因為你們,讓我意識到面對他人理解的渴求,合作的謙卑,及細密不倦的準備和修繕。尤其這些年和阿忠合作,在他身上看到了從不停歇實踐的勇氣和力量。我的劇本常常在排練期間邊排邊修,邊修邊排,感謝過程中一起承擔的演員、設計、行政和技術團隊,因為你們,這些字句得以被聆聽被檢視,形諸血肉,擲地有回聲。從書寫到形成實體的出版過程中,謝謝慷慨提供協助的麗珍、湘瑩、逸仔、Galilee、漢菱,以及不具名的很多很多朋友。
這本書能出版,要感謝思鋒的推手,猶記得當年《饕餮》首演後,我和他透過一個朋友的介紹,在竹圍工作室的大樹下聊了一陣,開啟了長遠的「其後」。
感謝作品背後的謬思,第一位讀者。
我想把書獻給我的母親。在她身上學到的,生活簡單些,踏實地工作,不貪戀奢求。因為她,我得以深切感受,儘管路多崎嶇,巍顫顫中有盼望,而盼望,長出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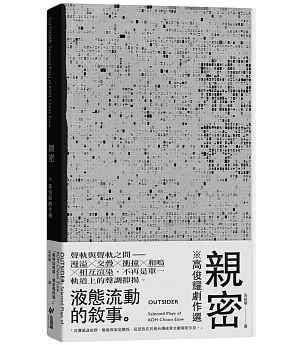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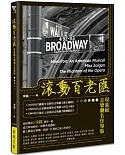










![台灣戲劇館25周年慶~歌仔戲《白雪與魔鏡》[DVD]](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69%2F58%2F0010695827.jpg&width=125&height=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