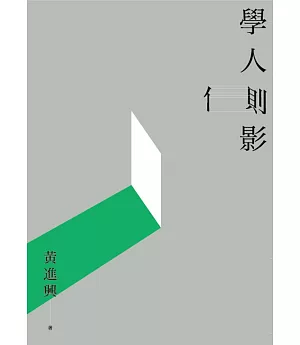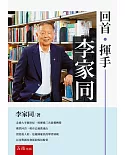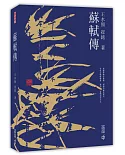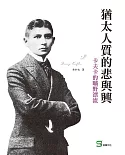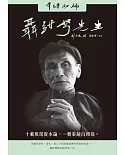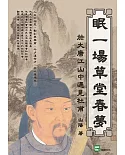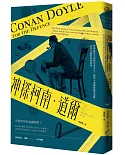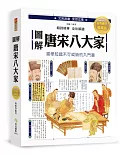序
日本文評家厨川白村(1880-1923)曾有一句名言,文學創作乃是「苦悶的象徵」。我想沒有人更能體會此中的真諦。
二○一六年九月,個人不自量力接下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行政工作。平時公務煩忙,雖說一心偶而可以數用,但又不能分心耽誤公事,所以只得利用夜晚和周末的有限時段,從事一些零星的探討,是故至多只能產出一些小品文。有天夜深人靜,突然靈光一閃,多年前書寫《哈佛瑣記》的經驗,給我一個及時的啟發:既然缺乏充分的時間可進行深度、廣度兼顧的研究,不如僅憑回憶,捕捉若干所見所聞,尤其是自己因緣所遇的學人,縱使是驚鴻一瞥亦無妨。因此拙作所描述的學人,其中有些人物僅止一面之緣,若哲學家桑代爾(Michael
Sandel);也有歷數十年情誼的老朋友,若孫康宜、王德威、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田浩(Hoyt Tillman)等,另外當然包括惠我良多的幾位飽學的師長。之間熟識的程度雖然有別,但用心則無兩樣。
然而有些名家囿於只有一言半語,卻難以成篇。例如:史基納(Quentin Skinner),二○一三年在史語所所長室談到他年少輕狂時寫下他的成名作:“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69),其自得之狀,猶歷歷在目。二○一五年,微觀史家金士堡(Carlo
Ginzburg)於「傅斯年講座」,慷慨激昂闡述猶太人的歷史情境及政治立場,義正嚴詞,聲若洪鐘,震耳欲聾。二○一六年因擔任「中央研究院講座」來訪的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教授,多年來在倫理學、政治哲學,以及思想史方面成就斐然,業已躋身世界一流學者以及思想家之列。尤其他近年來關於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理論,在學界舉足輕重;個人在從事孔廟聖地的分析時,曾有所參照。我也把握了他訪問中研院史語所的機會,與他當面討論在跨文化的脈絡下,神聖性與世俗化對立的不同可能樣態。雖至為景仰,然僅止於此,只得忍痛割愛。整體而言,這些書寫都僅止於個人的接觸,所以不免主觀成份居多,而局限於片面的觀察。記得英國史學大家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曾出了一本名人見聞錄:《個人印象》(Personal Impressions),運筆之間,或許對我多少有些微的啟示吧!拙作敘述的手法,約可比擬繪畫的「素描」或攝影的「快照」吧!
其它的學術論文的產出,大略也是處於同樣公、私交迫的窘境。學人札記約略只需兩、三天即可草就,但與「王國維」則足足奮鬥了不下三個月,方得下筆勉強成篇,寫成〈王國維的哲學時刻〉一文。本來三十多年前,我原擬以「王國維」作為博士論文,但與其糾纏了幾個月,便發現自己力有未逮,並沒有足夠的準備,可以處理像王國維這樣了不起的學者,其學問之廣博和運思之複雜,皆非初學者的我可以承擔,當時遂得中輟而滿懷挫折。歲月磋跎,即便今日智識稍長,個人也只敢擷取他問學之初的一小段,略作分析,淺嚐即止。但總算一償夙願,彌補了昔日的缺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陳甜女士復再三建議,收入若干討論思想史上重要學人的論文,與「素描」當代學人的札記並置,令思想史與學術界、研究對象與研究者作一對觀。其間究竟有何分殊,竟難以分曉?
末了,感謝允晨文化公司廖志峯先生願意刊行拙作台灣繁體字版。另外,我必須向陳靜芬女士特別致謝。多年來,她不辭辛勞而且極具耐心地整理了我塗鴉的文稿,俾便為來日刊行,做了最佳的預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