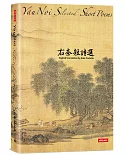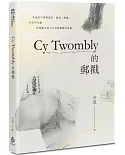詩歌是永恆的,一寫完一發表,便會很強悍的以它本來的姿彩和風格活下來,而隨後跟上來的賞析文字,總能保留住那股熟悉的芳香,不會因時間的消逝而走味。
【時代風華,經典重讀】
作者白靈是詩人,也是詩評名家。全書以11篇詩歌賞析,導讀瘂弦18首經典詩作,為讀者精闢解析「瘂弦詩風」的影響和魅力。
宣統那年的風吹著
吹著那串紅玉米
瘂弦是天才型的詩人,其詩作分「野荸薺時期」(1953—1958)、「深淵時期」(1957—1959)和「如歌時期」(1960─1965),他在詩創作上的成就與影響,可歸納為:音樂性的旋律感、語言意象的名句營造、戲劇呈現躍然紙上、靈巧運用工商業詞彙使內容現代化、豐富多元的形式編排、多元的風格變化反映詩人不同階段的人生關照。
☆★☆建議延伸閱讀《傳奇──鄭愁予經典詩歌賞析》,感受詩歌永恆的魅力。
本書特色
瘂弦,一個天才型的詩人。
從11篇精闢的詩歌賞析,走入18首瘂弦「經典」詩作,映照──
激流中眾生相轉瞬即逝的倒影!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白靈
本名莊袓煌,1951年生,福建惠安人,現任臺北科技大學及東吳大學兼任副教授。曾任年度詩選編委、臺灣詩學季刊主編五年,作品曾獲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2011新詩金典獎等十餘項。創辦「詩的聲光」,推廣詩的另類展演型式。著有詩集《昨日之肉》、《五行詩及其手稿》、《愛與死的間隙》、《女人與玻璃的幾種關係》等十二種,童詩集兩種,散文集《給夢一把梯子》等三種,詩論集《一首詩的玩法》等八種。建置個人網頁「白靈文學船」、「乒乓詩」、「無臉男女之布演臺灣」等十二種(https://myweb.ntut.edu.tw/~thchuang/body.html)。
白靈
本名莊袓煌,1951年生,福建惠安人,現任臺北科技大學及東吳大學兼任副教授。曾任年度詩選編委、臺灣詩學季刊主編五年,作品曾獲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2011新詩金典獎等十餘項。創辦「詩的聲光」,推廣詩的另類展演型式。著有詩集《昨日之肉》、《五行詩及其手稿》、《愛與死的間隙》、《女人與玻璃的幾種關係》等十二種,童詩集兩種,散文集《給夢一把梯子》等三種,詩論集《一首詩的玩法》等八種。建置個人網頁「白靈文學船」、「乒乓詩」、「無臉男女之布演臺灣」等十二種(https://myweb.ntut.edu.tw/~thchuang/body.html)。
目錄
(代序)世紀的風華,永遠的傳奇/徐望雲
為激流的倒影造像—瘂弦詩風的背景及影響/白靈
詩歌│紅玉米
【賞析】憂傷甜美的鄉愁
詩歌│鹽
【賞析】模糊在歲月中的臉孔
詩歌│巴黎、倫敦、芝加哥
【賞析】以靈眼為世界繪圖
詩歌│印度
【賞析】鋪在菩提樹下的袍影
詩歌│C教授、水夫、上校、修女、坤伶、故某省長
【賞析】逐兔的獵犬人生
詩歌│給橋
【賞析】寫在鶴橋上的詩
詩歌│出發
【賞析】從絕望中出發
詩歌│如歌的行板
【賞析】一條微笑的河流
詩歌│下午
【賞析】在窗簾間晃動的下午
詩歌│一般之歌
【賞析】駛出生命的貨車
詩歌│深淵
【賞析】深淵的見證人
為激流的倒影造像—瘂弦詩風的背景及影響/白靈
詩歌│紅玉米
【賞析】憂傷甜美的鄉愁
詩歌│鹽
【賞析】模糊在歲月中的臉孔
詩歌│巴黎、倫敦、芝加哥
【賞析】以靈眼為世界繪圖
詩歌│印度
【賞析】鋪在菩提樹下的袍影
詩歌│C教授、水夫、上校、修女、坤伶、故某省長
【賞析】逐兔的獵犬人生
詩歌│給橋
【賞析】寫在鶴橋上的詩
詩歌│出發
【賞析】從絕望中出發
詩歌│如歌的行板
【賞析】一條微笑的河流
詩歌│下午
【賞析】在窗簾間晃動的下午
詩歌│一般之歌
【賞析】駛出生命的貨車
詩歌│深淵
【賞析】深淵的見證人
序
代序
世紀的風華,永遠的傳奇
徐望雲
一九九一年,我到海風出版社任職總編輯,除了一般的文學書籍之外,平時還要負責整理編輯一套大部頭的「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系列。
【世紀的風華】
說是一「套」,其實不是很準確。這一系列,是一九八○年代,由廣西教育出版社主導文學系列「中國現代作家作品欣賞叢書」的「臺灣版(正體字)」。我進海風出版社之前, 出版社已跟廣西教育出版社完成簽約合作,合作方式就是臺灣這邊選擇適合臺灣讀者的新文學作家,增加了圖片資料,將橫排的簡體字版,重新編印成直行的臺灣版本。
印象中廣西教育出版社這一系列書最終出了近七十本,而臺灣這邊從一九八九年的第一本《魯迅》和第二本《巴金》開始,一路出下來,到我接任總編輯時,已出了二十多本,但在廣西那邊,則已規劃到六十多本了。
這一系列書中,廣西教育出版社其實也選了不少在臺灣發光發熱的作家,例如《白先勇》、《黃春明》、《賴和、吳濁流、楊逵、鍾理和》(四人合為一本)。
在海風出版社期間,我因工作需要,與廣西教育出版社不斷以郵件往返溝通,了解到他們在詩的部分已選定了三個人:余光中、洛夫和瘂弦,準備像《賴和、吳濁流、楊逵、鍾理和》這本一樣,將三人合為一本,作為這一系列叢書的最後一本,由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教授盧斯飛撰寫。
在與他們溝通的過程中,我提議增加「鄭愁予」。實話說,這提議的確懷有我的私心,因為我嗜讀鄭愁予,甚至能背誦他幾首膾炙人口的作品。當然,鄭愁予的影響,也無庸贅言。
但當時,鄭愁予的作品在大陸或許還不被熟悉,廣西那邊遲疑了很久,待我寄上鄭愁予的作品後,他們內部開了次會,最後同意補進「鄭愁予」,並將原定「余光中、洛夫、瘂弦」拆開來,將「余光中、洛夫」合為一本,瘂弦部分抽出來,與鄭愁予合為一本。
不過,在同意補入「鄭愁予」同時,廣西教育出版社開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余光中、洛夫》由盧斯飛續完(當時盧斯飛已開始寫余光中部分),但因為他對鄭愁予的詩仍不熟悉,故《瘂弦、鄭愁予》必須由我負責完成,而我也沒得選擇,就接下了這活兒。
廣西教育出版社希望《瘂弦、鄭愁予》這本,能接續在《余光中、洛夫》之後出版,但不要隔太久;礙於時間緊迫,要我同時寫兩個詩人的量,實在吃力,我便商請白靈幫忙,白靈也很阿沙力,幫我扛下了《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的「瘂弦」部分,我只負責寫「鄭愁予」。
於是,《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就成了廣西教育出版社「中國現代作家作品欣賞叢書」中壓軸的一本,也是唯一由臺灣作家擔綱完成的一本。
因為這是系列中唯一由臺灣作家撰寫,故對於臺灣版而言,整理起來比系列其他書籍方便許多。我和白靈的稿子寫完後,一份寄往廣西,另一份就留在臺灣這邊直接編排,同時,按照規格,我們還要整理相關年表和圖片資料。並準時在一九九三年前將全部稿件完成交出。
然而,事情發展或有不順。《余光中、洛夫詩歌欣賞》這本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廣西準時出版,《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這本卻遲了五年,至一九九八年六月才出版。而臺灣這邊的大樣儘管早在一九九三年就已搞定,奇怪的是,海風出版社卻一直沒有出版,後來我移居到加拿大,更與海風出版社失去聯絡,而《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臺灣版也一直沒有印刷出版。
【永遠的傳奇】
瘂弦比我更早移民加拿大,從事新聞工作的我,在一些活動或者採訪工作上,總會有機會與瘂弦碰面一敘,有幾回他問我,這本《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的臺灣版情況,我如實告之:「沒有下文,我也連絡不到海風出版社了。」
我心裡想的是,我和白靈的稿子都已全部交出,且都已校對完畢,只差付梓。如果出版社基於未便為外人知的考量不予出版,我們也沒辦法。
於是,這本《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的臺灣版就一直懸著。
直到二○一八年初,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舉辦春宴,我去做採訪報道,瘂弦也受邀前往,見了面打了招呼坐下來後,瘂弦又一次問起《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臺灣版的事,照例,我再一次回答:「不知道。」
答完後便去工作,也沒在意。
然而,就在那次春宴後不久,驚聞曾久居溫哥華並已回流臺灣的前輩詩人洛夫過世的消息,我嚇了一跳,腦海中登時跳出這本《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並閃過瘂弦每回問我這本書的臺灣版情況時,那迫切的眼神……
於是,我開始較為積極的「動」了起來。先聯絡廣西教育出版社,確認版權問題。聯絡上之後才知道,當初編輯「中國現代作家作品欣賞叢書」的團隊早已星散,當年一直跟我書信往來的編輯邱方,則到了廣東的出版部門;新的主編甚至都不知道曾出過這一套書,最後他們查了版權法後告訴我:「這本書已出版超過十年了,既沒有再印,也就沒有版權問題。」
接下來,就是臺灣這邊了。很順利,也很感恩,秀威很快就同意重新編印這本書的正體字版。
二○一八年七月間我回臺灣,與白靈連袂前往秀威討論,為了方便閱讀,決定將這本書拆成兩本,即瘂弦和鄭愁予各一本。同時,由於文字都是二十多年前寫就,有些時效性的字眼,必須做更動,因此,我和白靈各自重新再校對一遍,要校正錯字的校正錯字、要部分改動的就部分做改動。
這本書的內容大體維持當年廣西版《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的面貌(除了前段所言,部分文字因時效之類的考量做必要的改動),裡面的賞析文字本就是為這本書而寫, 從未單篇單篇在臺灣和大陸的報刊上發表過,因此,對臺灣的讀者而言,還算是一本「全新」的書。
所幸,詩歌是永恆的,一寫完一發表,便會很強悍的以它本來的姿彩和風格活下來,而隨後跟上來的賞析文字,總能保留住那股熟悉的芳香,不會因時間的消逝而走味。
瘂弦、鄭愁予的詩歌如此,這曾經連體,現在分開的兩本「經典詩歌賞析」,也是如此。
二十多年的時光把我們帶到這個時間點,可喜者,因為有更多的讀者誕生,勢必會讓這兩本書產生新的生命,於是瘂弦和鄭愁予的詩就這樣一直年輕著,而我和白靈的賞析篇章也會繼續為新來的讀者服務。
請慢慢享用。
------------------------
為激流的倒影造像
──瘂弦詩風的背景及影響
------------------------
瘂弦是六○年代出類拔萃的詩人,在他短短十三年左右(一九五三—一九六五)的詩創作生涯裡,寫了不到一百首詩,然而時隔三十年,許多他的名篇佳句迄今仍四處「流竄」, 從臺灣到大陸,在街坊間在教室裡在朗誦會上,正以看不見的驚人速度,震撼著後幾輩愛詩人的心靈。諸多與他同時起跑、寫得比他勤比他多的詩人,如今大半沉寂而不可聽聞,而他卻以一本《深淵》,僅僅一本《深淵》就能「擊退眾敵」,卓然自成一家,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
瘂弦是具極高「自覺性」的詩人(他的停筆不寫恐也與此有關),我們單由《深淵》 的出版,即可約略看出多半詩人出版詩集時,在質和量上都不免敝帚自珍,有「摻水」之嫌,而瘂弦在編纂他的唯一詩集時,卻是帶有「歷史感」的,除了自認「可傳」的詩作外,許多他的著作一開始並未收入,從最早的版本《苦苓林的一夜》(一九五九,香港國際),到改封面成《瘂弦詩抄》(未流傳),到增補成《深淵》(一九六八,眾人;一九七一,晨鐘),概未收入最後定本《瘂弦詩集》(一九八一,洪範)中所附的著作(廿五歲前作品),更不要說一些歌詠時代的、性質接近所謂「兵的文學」的得獎長詩如〈火把,火把喲〉、〈冬天的憤怒〉、〈血花曲〉(三千行)等作品了。這種類似壯士斷腕的果決作風,使得他的集子成為自有新詩出版品以來,「品質管制」得最好的少數詩集之一。
瘂弦的詩可以說是以「人」為中心的,他很少直接去歌詠一件物品、一片風景或一樁心情,當他在說「我」時,這個「我」可以是一朵「小花」、一名「乞丐」、一隻「船中之鼠」,是「黑皮膚的女奴」、「滴血的士卒」、「白髮的祭司」、「吆喝的轎夫」(見〈巴比侖〉一詩);這個「我」是可以被踐踏眼睛的(〈巴黎〉)、可以被誰踩進腦中的(〈夜曲〉)、可以被腳拔出腦漿的、可以被人賣給死的(〈從感覺出發〉),是求愛不成的「馬戲的小丑」、是想把大街舉起來的「瘋婦」。即使這個「我」貴為一位「山神」了,卻仍然微不足道―「我在菩提樹下為一個流浪客餵馬」,「我在敲一家病人的鏽門環」,「我在煙雨的小河裡幫一個漁漢撒網」,「我在古寺的裂鐘下同一個乞兒烤火」。在他的詩中,更常用的主詞是「你」、「他」、「他們」、「我們」或者「XX們」(如男孩子們、修女們、雁子們、天使們、果子們、蛀蟲們……等近四十種),以晨鐘版《深淵》詩集為例,這群主詞約使用了五百次,而「我」則約用了一百三十次,而這個「我」也很少是自己,多半是他裝扮成別人,在演一些小角色,他的詩充滿了無數的「他人」!這就構成他詩集的最大「力量」,一股彌天蓋地的巨大「悲心」。這股「悲心」有時以「神性」表現,如〈春日〉、〈印度〉,有時以「魔性」呈現,如〈巴黎〉、〈深淵〉,有時 又以「人性」表達,如〈坤伶〉、〈馬戲的小丑〉、〈瘋婦〉、〈鹽〉,有時是淡淡哀傷,如〈紅玉米〉, 有時是俏皮反諷,如〈赫魯雪夫〉。如果說人生再苦的悲劇一經旋律化後,都有了藝術上的美感,讓人可以感懷或感動,瘂弦的詩就屬於那一種。他是涉過人生的激流、出入人性的深淵後,再站出來微笑地唱詠,以甜美的語言昭告世界的詩人。
瘂弦生於河南南陽,母親出身沒落地主家庭,父親佃農出身。在他離開家鄉以前,沒有見過吐著蒸汽的火車,也沒看過可以「扭耳朵」的燈泡,但接觸文學卻很早,小時候就讀過冰心、陸志葦的詩集,是他的父親介紹他看的。其父畢業於南陽的師範學校,且辦了一本用石版印的《黃河流域》雜誌,他也有很多喜歡文學的朋友常聚集在他家裡吃飯、抬槓,薄薄的家產就這樣「用菜盤子端出去」了。他父親在民眾教育館掌管圖書,常拉著牛車到鄉 下搞「巡迴圖書」,瘂弦跟在後頭敲鑼,吸引小朋友出來看書,由此瘂弦也接觸過不少兒童詩,比如上海兒童月刊上的。這些幼年的生活經驗,不見得是快樂的,但至少是溫馨的,說不定是悲苦的,卻是農業生活環境下人與人之間最誠摯的互助,瘂弦對「人」的關注應該是從這樣的童年背景開始的吧。
他也是家中唯一離開家鄉、渡海來臺的,之後他進入臺灣的政戰學校學習戲劇,畢業後,入海軍服役,在左營電臺當電臺外勤記者時與洛夫、張默、商禽、季紅等人過從甚密。他們一方面私下傳閱三○年代詩人的作品手抄本,一方面大量吸收包括英、美、俄、法、德等西方文學著作。他曾手抄各種文學作品,如《浮士德》詩集等,「手抄本」多到將近一人高。他學習的對象包括何其芳、郭沫若、卞之琳、辛笛、里爾克、歌德、勃朗甯、艾呂亞、馬拉美、惠特曼、馬雅可夫斯基等等,那時的他,「對西方文學充滿幻想,甚至可以說崇拜」。他的少年農村生活和後來的軍人生活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態,對他的詩作都有重要的影響:1.前一階段是自發的、溫情的、與土地和人接近的;2.後一階段是被迫的、扭曲的、壓抑的、與時代和自我接近的;3.由於前後兩階段的強烈對比,此後在接受現代主義的洗禮後,轉而促使其思索人生的無常、孤絕、荒誕,乃至不得不持續下去的生命本質。
尤其在五、六○年代,對一個大陸來臺的青年人而言,剛歷經戰爭流離顛沛、充滿失落和死亡的歲月,接著面對的是如何調整失敗挫折的步伐,如何面對傳統與西化、保守與現代化的糾葛和衝擊,而那時臺灣社會為力求穩定,政治和文化上採取的是一種高壓政策,經濟又未起步,人人有被「壓」的感覺,也都想逃脫現實或超脫現實,「對遠方產生懷想」, 企圖進入 一種「出神狀態」,以求精神上的自我解放,遂成為社會風尚。這個「遠方」, 一邊是「故土」,一邊是「西方」;一邊是陸地的,一邊是海洋的;一邊是回憶,一邊是憧憬;一邊是中國抒情性的鄉愁,一邊是世界性的悲愁感。當瘂弦將這兩個「遠方」表現在詩作中時,前者便是〈鬼劫〉、〈棺材店〉、〈紅玉米〉、〈山神〉、〈乞丐〉、〈秋歌〉、〈鹽〉等作品,後者便是〈希臘〉、〈阿拉伯〉、〈巴黎〉、〈芝加哥〉、〈倫敦〉、〈深淵〉等詩作。而表現在瘂弦與洛夫、張默創辦的《創世紀》詩刊上(一九五四年十月創刊, 瘂弦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加入編務),便是「新民族詩型」(一九五六年三月提出,主張:1.藝術的―形象第一、意境至上;2.強調中國風與東方味)與「超現實主義」(一九五九年四月提出,強調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兩者看似背離的主張,其實這兩種主張都與「遠方」和「想望」有關。
瘂弦與上述兩個「遠方」有關的詩作,一般即將之稱為「野荸薺時期」(一九五三—一九五八)和「深淵時期」(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是這兩時期的交匯年(也可見出前「遠方」對詩人影響之深入),也是他創作的高峰期,兩年中共寫了四十九首詩。〈深淵〉以後的詩作,包括〈C教授〉、〈水手〉等「側面輯」及〈給橋〉、〈下午〉、〈如歌的行板〉、〈非策劃性的夜曲〉、〈一般之歌〉、〈復活節〉等作品,則不妨稱之為「如歌時期」(一九六○—一九六五)。十餘年間劃分為三期,並無藝術上嚴謹的意義,只是追索詩人創作過程中風貌的變化軌跡罷了。
(……中略)
瘂弦是天才型的詩人,在他所處的時代,臺灣新詩界人才輩出,瘂弦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學習模仿的文學大師廣及中、英、美、法、俄、德等國,不拘於詩一項,小說、傳記、戲劇、哲學等等,從最鄉土的方言、民謠、小調,到最西方的現代思潮,他都試圖汲取營養,「轉益多師為我師」,創造出自己突出的風格。他在意象的創造、語言的節奏、戲劇手法的展現上貢獻最大,也是迄今眾多詩家所望塵莫及的,雖然這期間他也寫了不少失敗的作品。然而正當「萬方矚目」,看看「如歌」之後的瘂弦還會有什麼樣更驚人的表現,他卻突然放下詩筆,結婚(一九六五年四月)、跳上舞臺飾演孫逸仙(一九六五年九月)、當選十大傑出青年(十二月)、赴美研究(一九六六年九月),兩年後回臺,從此即投入「為他人的不朽服務」的文藝行政當中。離臺之時他信誓旦旦,說從愛荷華回臺後「當再出一本詩集」(見葉珊〈深淵後記〉),出國之後因「功課咄咄逼人」,十分忙碌,予友人信中卻說:「預料這一年收穫的將是語文和『學術』,而非詩的本身(創作)。」(一九六五年十月致羅行、一九六七年一月致張默函)當時留下眾多詩材,後來都「鎖進箱底」運回臺灣,迄今仍不敢翻動,此後即以「沉默之筆」一再面對無數讀者的質詢。
瘂弦那一輩詩人輟筆不寫的,何止他一人而已,或先或後,或轉攻其他文類或偶吐泡沫。而讀者偏偏只對他關心殷切,數十年如一日,時常騷擾他的耳膜,由此也可看出「瘂弦詩風」的影響和魅力。他是從不幸的年代走出來的人,當其時,他站在時代的激流之中,眾多的人也站在人生的激流中,大多沒留下什麼就遭激流沖走,而瘂弦以他的生花妙筆,已為激流中的眾生相捕捉到他們轉瞬即逝的倒影―那幾乎不可能捕捉到的倒影,扭曲也罷,變形也好,他的確已經為他的時代作了藝術上極佳的見證,不論是悲苦或迷茫的那個年代。那又何必「在乎」今後的瘂弦是等待醒來的睡火山,或是臥在雲海下端澄明如鏡的天池?
世紀的風華,永遠的傳奇
徐望雲
一九九一年,我到海風出版社任職總編輯,除了一般的文學書籍之外,平時還要負責整理編輯一套大部頭的「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系列。
【世紀的風華】
說是一「套」,其實不是很準確。這一系列,是一九八○年代,由廣西教育出版社主導文學系列「中國現代作家作品欣賞叢書」的「臺灣版(正體字)」。我進海風出版社之前, 出版社已跟廣西教育出版社完成簽約合作,合作方式就是臺灣這邊選擇適合臺灣讀者的新文學作家,增加了圖片資料,將橫排的簡體字版,重新編印成直行的臺灣版本。
印象中廣西教育出版社這一系列書最終出了近七十本,而臺灣這邊從一九八九年的第一本《魯迅》和第二本《巴金》開始,一路出下來,到我接任總編輯時,已出了二十多本,但在廣西那邊,則已規劃到六十多本了。
這一系列書中,廣西教育出版社其實也選了不少在臺灣發光發熱的作家,例如《白先勇》、《黃春明》、《賴和、吳濁流、楊逵、鍾理和》(四人合為一本)。
在海風出版社期間,我因工作需要,與廣西教育出版社不斷以郵件往返溝通,了解到他們在詩的部分已選定了三個人:余光中、洛夫和瘂弦,準備像《賴和、吳濁流、楊逵、鍾理和》這本一樣,將三人合為一本,作為這一系列叢書的最後一本,由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教授盧斯飛撰寫。
在與他們溝通的過程中,我提議增加「鄭愁予」。實話說,這提議的確懷有我的私心,因為我嗜讀鄭愁予,甚至能背誦他幾首膾炙人口的作品。當然,鄭愁予的影響,也無庸贅言。
但當時,鄭愁予的作品在大陸或許還不被熟悉,廣西那邊遲疑了很久,待我寄上鄭愁予的作品後,他們內部開了次會,最後同意補進「鄭愁予」,並將原定「余光中、洛夫、瘂弦」拆開來,將「余光中、洛夫」合為一本,瘂弦部分抽出來,與鄭愁予合為一本。
不過,在同意補入「鄭愁予」同時,廣西教育出版社開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余光中、洛夫》由盧斯飛續完(當時盧斯飛已開始寫余光中部分),但因為他對鄭愁予的詩仍不熟悉,故《瘂弦、鄭愁予》必須由我負責完成,而我也沒得選擇,就接下了這活兒。
廣西教育出版社希望《瘂弦、鄭愁予》這本,能接續在《余光中、洛夫》之後出版,但不要隔太久;礙於時間緊迫,要我同時寫兩個詩人的量,實在吃力,我便商請白靈幫忙,白靈也很阿沙力,幫我扛下了《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的「瘂弦」部分,我只負責寫「鄭愁予」。
於是,《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就成了廣西教育出版社「中國現代作家作品欣賞叢書」中壓軸的一本,也是唯一由臺灣作家擔綱完成的一本。
因為這是系列中唯一由臺灣作家撰寫,故對於臺灣版而言,整理起來比系列其他書籍方便許多。我和白靈的稿子寫完後,一份寄往廣西,另一份就留在臺灣這邊直接編排,同時,按照規格,我們還要整理相關年表和圖片資料。並準時在一九九三年前將全部稿件完成交出。
然而,事情發展或有不順。《余光中、洛夫詩歌欣賞》這本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廣西準時出版,《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這本卻遲了五年,至一九九八年六月才出版。而臺灣這邊的大樣儘管早在一九九三年就已搞定,奇怪的是,海風出版社卻一直沒有出版,後來我移居到加拿大,更與海風出版社失去聯絡,而《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臺灣版也一直沒有印刷出版。
【永遠的傳奇】
瘂弦比我更早移民加拿大,從事新聞工作的我,在一些活動或者採訪工作上,總會有機會與瘂弦碰面一敘,有幾回他問我,這本《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的臺灣版情況,我如實告之:「沒有下文,我也連絡不到海風出版社了。」
我心裡想的是,我和白靈的稿子都已全部交出,且都已校對完畢,只差付梓。如果出版社基於未便為外人知的考量不予出版,我們也沒辦法。
於是,這本《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的臺灣版就一直懸著。
直到二○一八年初,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舉辦春宴,我去做採訪報道,瘂弦也受邀前往,見了面打了招呼坐下來後,瘂弦又一次問起《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臺灣版的事,照例,我再一次回答:「不知道。」
答完後便去工作,也沒在意。
然而,就在那次春宴後不久,驚聞曾久居溫哥華並已回流臺灣的前輩詩人洛夫過世的消息,我嚇了一跳,腦海中登時跳出這本《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並閃過瘂弦每回問我這本書的臺灣版情況時,那迫切的眼神……
於是,我開始較為積極的「動」了起來。先聯絡廣西教育出版社,確認版權問題。聯絡上之後才知道,當初編輯「中國現代作家作品欣賞叢書」的團隊早已星散,當年一直跟我書信往來的編輯邱方,則到了廣東的出版部門;新的主編甚至都不知道曾出過這一套書,最後他們查了版權法後告訴我:「這本書已出版超過十年了,既沒有再印,也就沒有版權問題。」
接下來,就是臺灣這邊了。很順利,也很感恩,秀威很快就同意重新編印這本書的正體字版。
二○一八年七月間我回臺灣,與白靈連袂前往秀威討論,為了方便閱讀,決定將這本書拆成兩本,即瘂弦和鄭愁予各一本。同時,由於文字都是二十多年前寫就,有些時效性的字眼,必須做更動,因此,我和白靈各自重新再校對一遍,要校正錯字的校正錯字、要部分改動的就部分做改動。
這本書的內容大體維持當年廣西版《瘂弦、鄭愁予詩歌欣賞》的面貌(除了前段所言,部分文字因時效之類的考量做必要的改動),裡面的賞析文字本就是為這本書而寫, 從未單篇單篇在臺灣和大陸的報刊上發表過,因此,對臺灣的讀者而言,還算是一本「全新」的書。
所幸,詩歌是永恆的,一寫完一發表,便會很強悍的以它本來的姿彩和風格活下來,而隨後跟上來的賞析文字,總能保留住那股熟悉的芳香,不會因時間的消逝而走味。
瘂弦、鄭愁予的詩歌如此,這曾經連體,現在分開的兩本「經典詩歌賞析」,也是如此。
二十多年的時光把我們帶到這個時間點,可喜者,因為有更多的讀者誕生,勢必會讓這兩本書產生新的生命,於是瘂弦和鄭愁予的詩就這樣一直年輕著,而我和白靈的賞析篇章也會繼續為新來的讀者服務。
請慢慢享用。
------------------------
為激流的倒影造像
──瘂弦詩風的背景及影響
------------------------
瘂弦是六○年代出類拔萃的詩人,在他短短十三年左右(一九五三—一九六五)的詩創作生涯裡,寫了不到一百首詩,然而時隔三十年,許多他的名篇佳句迄今仍四處「流竄」, 從臺灣到大陸,在街坊間在教室裡在朗誦會上,正以看不見的驚人速度,震撼著後幾輩愛詩人的心靈。諸多與他同時起跑、寫得比他勤比他多的詩人,如今大半沉寂而不可聽聞,而他卻以一本《深淵》,僅僅一本《深淵》就能「擊退眾敵」,卓然自成一家,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
瘂弦是具極高「自覺性」的詩人(他的停筆不寫恐也與此有關),我們單由《深淵》 的出版,即可約略看出多半詩人出版詩集時,在質和量上都不免敝帚自珍,有「摻水」之嫌,而瘂弦在編纂他的唯一詩集時,卻是帶有「歷史感」的,除了自認「可傳」的詩作外,許多他的著作一開始並未收入,從最早的版本《苦苓林的一夜》(一九五九,香港國際),到改封面成《瘂弦詩抄》(未流傳),到增補成《深淵》(一九六八,眾人;一九七一,晨鐘),概未收入最後定本《瘂弦詩集》(一九八一,洪範)中所附的著作(廿五歲前作品),更不要說一些歌詠時代的、性質接近所謂「兵的文學」的得獎長詩如〈火把,火把喲〉、〈冬天的憤怒〉、〈血花曲〉(三千行)等作品了。這種類似壯士斷腕的果決作風,使得他的集子成為自有新詩出版品以來,「品質管制」得最好的少數詩集之一。
瘂弦的詩可以說是以「人」為中心的,他很少直接去歌詠一件物品、一片風景或一樁心情,當他在說「我」時,這個「我」可以是一朵「小花」、一名「乞丐」、一隻「船中之鼠」,是「黑皮膚的女奴」、「滴血的士卒」、「白髮的祭司」、「吆喝的轎夫」(見〈巴比侖〉一詩);這個「我」是可以被踐踏眼睛的(〈巴黎〉)、可以被誰踩進腦中的(〈夜曲〉)、可以被腳拔出腦漿的、可以被人賣給死的(〈從感覺出發〉),是求愛不成的「馬戲的小丑」、是想把大街舉起來的「瘋婦」。即使這個「我」貴為一位「山神」了,卻仍然微不足道―「我在菩提樹下為一個流浪客餵馬」,「我在敲一家病人的鏽門環」,「我在煙雨的小河裡幫一個漁漢撒網」,「我在古寺的裂鐘下同一個乞兒烤火」。在他的詩中,更常用的主詞是「你」、「他」、「他們」、「我們」或者「XX們」(如男孩子們、修女們、雁子們、天使們、果子們、蛀蟲們……等近四十種),以晨鐘版《深淵》詩集為例,這群主詞約使用了五百次,而「我」則約用了一百三十次,而這個「我」也很少是自己,多半是他裝扮成別人,在演一些小角色,他的詩充滿了無數的「他人」!這就構成他詩集的最大「力量」,一股彌天蓋地的巨大「悲心」。這股「悲心」有時以「神性」表現,如〈春日〉、〈印度〉,有時以「魔性」呈現,如〈巴黎〉、〈深淵〉,有時 又以「人性」表達,如〈坤伶〉、〈馬戲的小丑〉、〈瘋婦〉、〈鹽〉,有時是淡淡哀傷,如〈紅玉米〉, 有時是俏皮反諷,如〈赫魯雪夫〉。如果說人生再苦的悲劇一經旋律化後,都有了藝術上的美感,讓人可以感懷或感動,瘂弦的詩就屬於那一種。他是涉過人生的激流、出入人性的深淵後,再站出來微笑地唱詠,以甜美的語言昭告世界的詩人。
瘂弦生於河南南陽,母親出身沒落地主家庭,父親佃農出身。在他離開家鄉以前,沒有見過吐著蒸汽的火車,也沒看過可以「扭耳朵」的燈泡,但接觸文學卻很早,小時候就讀過冰心、陸志葦的詩集,是他的父親介紹他看的。其父畢業於南陽的師範學校,且辦了一本用石版印的《黃河流域》雜誌,他也有很多喜歡文學的朋友常聚集在他家裡吃飯、抬槓,薄薄的家產就這樣「用菜盤子端出去」了。他父親在民眾教育館掌管圖書,常拉著牛車到鄉 下搞「巡迴圖書」,瘂弦跟在後頭敲鑼,吸引小朋友出來看書,由此瘂弦也接觸過不少兒童詩,比如上海兒童月刊上的。這些幼年的生活經驗,不見得是快樂的,但至少是溫馨的,說不定是悲苦的,卻是農業生活環境下人與人之間最誠摯的互助,瘂弦對「人」的關注應該是從這樣的童年背景開始的吧。
他也是家中唯一離開家鄉、渡海來臺的,之後他進入臺灣的政戰學校學習戲劇,畢業後,入海軍服役,在左營電臺當電臺外勤記者時與洛夫、張默、商禽、季紅等人過從甚密。他們一方面私下傳閱三○年代詩人的作品手抄本,一方面大量吸收包括英、美、俄、法、德等西方文學著作。他曾手抄各種文學作品,如《浮士德》詩集等,「手抄本」多到將近一人高。他學習的對象包括何其芳、郭沫若、卞之琳、辛笛、里爾克、歌德、勃朗甯、艾呂亞、馬拉美、惠特曼、馬雅可夫斯基等等,那時的他,「對西方文學充滿幻想,甚至可以說崇拜」。他的少年農村生活和後來的軍人生活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態,對他的詩作都有重要的影響:1.前一階段是自發的、溫情的、與土地和人接近的;2.後一階段是被迫的、扭曲的、壓抑的、與時代和自我接近的;3.由於前後兩階段的強烈對比,此後在接受現代主義的洗禮後,轉而促使其思索人生的無常、孤絕、荒誕,乃至不得不持續下去的生命本質。
尤其在五、六○年代,對一個大陸來臺的青年人而言,剛歷經戰爭流離顛沛、充滿失落和死亡的歲月,接著面對的是如何調整失敗挫折的步伐,如何面對傳統與西化、保守與現代化的糾葛和衝擊,而那時臺灣社會為力求穩定,政治和文化上採取的是一種高壓政策,經濟又未起步,人人有被「壓」的感覺,也都想逃脫現實或超脫現實,「對遠方產生懷想」, 企圖進入 一種「出神狀態」,以求精神上的自我解放,遂成為社會風尚。這個「遠方」, 一邊是「故土」,一邊是「西方」;一邊是陸地的,一邊是海洋的;一邊是回憶,一邊是憧憬;一邊是中國抒情性的鄉愁,一邊是世界性的悲愁感。當瘂弦將這兩個「遠方」表現在詩作中時,前者便是〈鬼劫〉、〈棺材店〉、〈紅玉米〉、〈山神〉、〈乞丐〉、〈秋歌〉、〈鹽〉等作品,後者便是〈希臘〉、〈阿拉伯〉、〈巴黎〉、〈芝加哥〉、〈倫敦〉、〈深淵〉等詩作。而表現在瘂弦與洛夫、張默創辦的《創世紀》詩刊上(一九五四年十月創刊, 瘂弦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加入編務),便是「新民族詩型」(一九五六年三月提出,主張:1.藝術的―形象第一、意境至上;2.強調中國風與東方味)與「超現實主義」(一九五九年四月提出,強調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兩者看似背離的主張,其實這兩種主張都與「遠方」和「想望」有關。
瘂弦與上述兩個「遠方」有關的詩作,一般即將之稱為「野荸薺時期」(一九五三—一九五八)和「深淵時期」(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是這兩時期的交匯年(也可見出前「遠方」對詩人影響之深入),也是他創作的高峰期,兩年中共寫了四十九首詩。〈深淵〉以後的詩作,包括〈C教授〉、〈水手〉等「側面輯」及〈給橋〉、〈下午〉、〈如歌的行板〉、〈非策劃性的夜曲〉、〈一般之歌〉、〈復活節〉等作品,則不妨稱之為「如歌時期」(一九六○—一九六五)。十餘年間劃分為三期,並無藝術上嚴謹的意義,只是追索詩人創作過程中風貌的變化軌跡罷了。
(……中略)
瘂弦是天才型的詩人,在他所處的時代,臺灣新詩界人才輩出,瘂弦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學習模仿的文學大師廣及中、英、美、法、俄、德等國,不拘於詩一項,小說、傳記、戲劇、哲學等等,從最鄉土的方言、民謠、小調,到最西方的現代思潮,他都試圖汲取營養,「轉益多師為我師」,創造出自己突出的風格。他在意象的創造、語言的節奏、戲劇手法的展現上貢獻最大,也是迄今眾多詩家所望塵莫及的,雖然這期間他也寫了不少失敗的作品。然而正當「萬方矚目」,看看「如歌」之後的瘂弦還會有什麼樣更驚人的表現,他卻突然放下詩筆,結婚(一九六五年四月)、跳上舞臺飾演孫逸仙(一九六五年九月)、當選十大傑出青年(十二月)、赴美研究(一九六六年九月),兩年後回臺,從此即投入「為他人的不朽服務」的文藝行政當中。離臺之時他信誓旦旦,說從愛荷華回臺後「當再出一本詩集」(見葉珊〈深淵後記〉),出國之後因「功課咄咄逼人」,十分忙碌,予友人信中卻說:「預料這一年收穫的將是語文和『學術』,而非詩的本身(創作)。」(一九六五年十月致羅行、一九六七年一月致張默函)當時留下眾多詩材,後來都「鎖進箱底」運回臺灣,迄今仍不敢翻動,此後即以「沉默之筆」一再面對無數讀者的質詢。
瘂弦那一輩詩人輟筆不寫的,何止他一人而已,或先或後,或轉攻其他文類或偶吐泡沫。而讀者偏偏只對他關心殷切,數十年如一日,時常騷擾他的耳膜,由此也可看出「瘂弦詩風」的影響和魅力。他是從不幸的年代走出來的人,當其時,他站在時代的激流之中,眾多的人也站在人生的激流中,大多沒留下什麼就遭激流沖走,而瘂弦以他的生花妙筆,已為激流中的眾生相捕捉到他們轉瞬即逝的倒影―那幾乎不可能捕捉到的倒影,扭曲也罷,變形也好,他的確已經為他的時代作了藝術上極佳的見證,不論是悲苦或迷茫的那個年代。那又何必「在乎」今後的瘂弦是等待醒來的睡火山,或是臥在雲海下端澄明如鏡的天池?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79折$213
-
新書79折$214
-
新書85折$230
-
新書9折$243
-
新書$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