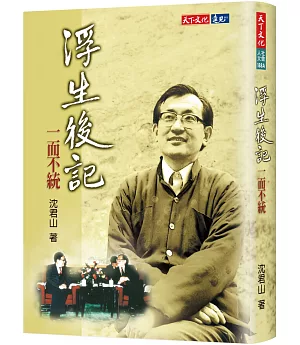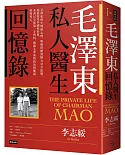「做我所能,愛我所做」—沈君山
前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教授,
於一九七三年返國服務後,即開始關注兩岸及族群溝通等議題,
本書縮影了數十年來沈君山的生活與理想;
字裏行間流露著才情與至情,令人低迴再三。
七○年代的保釣運動,影響海內外諸多菁英。四十初度的沈君山於美國接觸到兩岸學界對此一事件的種種論辯,自此啟蒙他的政治理想。
一九七三年返國服務後,沈君山開始關注兩岸議題,先後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國統會委員等職,並在許多國際會議上,代表台灣奠定與對岸平等對話的基礎。不僅如此,沈君山也為台灣的人權自由貢獻心力,與七○年代黨外人士一同歷經台灣民主化的過程。
一九九九年,沈君山中風,紀政等老友的陪伴與關懷,讓他重獲生機,再度揮灑於所關心的兩岸與族群等領域,人生也開展了另一番境界。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沈君山
浙江餘姚人,一九三二年生於南京,一九四九年來台。 一九五五年台大物理系畢業,一九五七年赴美,得馬里蘭大學物理學博士後,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太空總署、普渡大學擔任研究工作及任教。七○年代受海外保釣運動的愛國思潮影響,辭去在美國的教職,於一九七三年返台,先後擔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生命科學院籌備主任委員、人文社會學院籌備主任委員,以及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央選舉委員、中研院評議委員、國統會委員、清華大學校長、吳大猷學術基金會董事、新台灣人基金會榮譽董事長等職。 曾獲美國圍棋冠軍、世界橋牌亞軍。著有《尋津集》(遠流出版)、《耕耘歲月》(正中書局出版)、《浮生三記》(九歌出版)、《浮生後記》(天下文化出版)、《浮生再記》(九歌出版)等。 二○○六年四月十八日,中央大學鹿林天文台發現一顆小行星,二○○九年四月九日正式命名為「沈君山」(Shenchunshan,編號202605),以表彰其早年的天文著作激發台灣年輕人進行天文研究的貢獻。
沈君山
浙江餘姚人,一九三二年生於南京,一九四九年來台。 一九五五年台大物理系畢業,一九五七年赴美,得馬里蘭大學物理學博士後,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太空總署、普渡大學擔任研究工作及任教。七○年代受海外保釣運動的愛國思潮影響,辭去在美國的教職,於一九七三年返台,先後擔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生命科學院籌備主任委員、人文社會學院籌備主任委員,以及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央選舉委員、中研院評議委員、國統會委員、清華大學校長、吳大猷學術基金會董事、新台灣人基金會榮譽董事長等職。 曾獲美國圍棋冠軍、世界橋牌亞軍。著有《尋津集》(遠流出版)、《耕耘歲月》(正中書局出版)、《浮生三記》(九歌出版)、《浮生後記》(天下文化出版)、《浮生再記》(九歌出版)等。 二○○六年四月十八日,中央大學鹿林天文台發現一顆小行星,二○○九年四月九日正式命名為「沈君山」(Shenchunshan,編號202605),以表彰其早年的天文著作激發台灣年輕人進行天文研究的貢獻。
目錄
出版者的話
序一 起腳再尋浙江潮 張作錦
序二 尚思為國戍輪台 張作錦
楔子 老病與生死
自述
成長、返國與清華
族群溝通
兩岸初期交涉之參與
仕途和家庭
紀政
兩岸早期文摘(一九七○至一九九○)
談台灣「革新」
一個中國兩個制度的和平競爭
一國兩「治」
兩岸關係的三個階段
與江澤民晤談始末(一九九○至一九九二)
晤談機緣
第一次晤談第二次晤談
第三次晤談
回顧中共對台灣的心態和對兩岸關係的幾點建議
晤談中提到的幾位先生
民主化與兩岸
「中華兩岸聯合會」芻議芻議
之緣起與結果
瓊樓高處看開票(一九九八年)
瓊樓高處談開票(二○○二年)
施明德
懷念盧修一和早期的浩然營
港京來去
後記
序一 起腳再尋浙江潮 張作錦
序二 尚思為國戍輪台 張作錦
楔子 老病與生死
自述
成長、返國與清華
族群溝通
兩岸初期交涉之參與
仕途和家庭
紀政
兩岸早期文摘(一九七○至一九九○)
談台灣「革新」
一個中國兩個制度的和平競爭
一國兩「治」
兩岸關係的三個階段
與江澤民晤談始末(一九九○至一九九二)
晤談機緣
第一次晤談第二次晤談
第三次晤談
回顧中共對台灣的心態和對兩岸關係的幾點建議
晤談中提到的幾位先生
民主化與兩岸
「中華兩岸聯合會」芻議芻議
之緣起與結果
瓊樓高處看開票(一九九八年)
瓊樓高處談開票(二○○二年)
施明德
懷念盧修一和早期的浩然營
港京來去
後記
序
序
沈君山(吳大猷學術基金會董事長)
我是在一九九八年從清大退休的。對有些人而言,退休是生命的一個大轉折,是從人生的舞台上退下來了;我的感覺卻只是人生旋轉舞台又轉過了一景。
「退休」是一個現代名詞,中國從前稱之為「致仕」。「仕」是官或公務人員的意思,致仕就是從官場退下來,不再吃皇帝老子的飯了。但是「士」還是士,那個時代,「仕」是士的正途也幾乎是士唯一的專業,讀書人總要到仕途去轉一趟,才算盡了讀聖賢書的本分。致仕則是回到士的本色,是從官場上退下來,但不是從人生舞台退下來,而且在農業社會,士還有他發揮的空間。
現在時代不同,市場經濟下,社會專業劃分得更細、競爭更激烈,形式上個人或者很自由,但壓力的束縛也許更大,無形軌道的限制也許更緊嚴,一旦退休,壓力和束縛忽然都放鬆了,是一個「量子躍變」(Quantum Jump),需要很大的調適。
我的人生經驗較不同,已經經過了兩個大轉折。二十五歲出國是第一次,從台灣到美國,文化上很需要一番調適。但像我們那代的菁英青年一樣,也只有盡力在潮流安排的軌道下向前衝。十六年後,我在四十一歲時回國,是第二春,也是第二個大轉折,變換了軌道,其後又度過二十五年。其間雖然擔任過短期的公職,也參與了很多社會活動,但基本上還是在校園度過,過的是士的生活。從學校退休,有形的責任沒有了,無形的空間也許更大,也可以說人生第三春的開始吧。
在退休前後,與傳媒界的一些資深同仁聊天,都是很久的朋友了,曾被訪問也偶寫專欄,忽然發現自己一下就從青年才俊跳到「走過從前」的見證人了。被半開玩笑的問:「那你以後做什麼呢?」當時的總結是「做我所愛,愛我所做」。後來想想,改了一字,「做我所能,愛我所做」更適當些,雖一字之差,「能」和「愛」,是有距離的。
人退休之後進入老年,有兩個不同方面的忌諱:一是消沉下去,覺得自己是用舊了的,只能做汽車備胎的第五只輪胎,在各種場合都退縮不前;二是絕不服老,對於已經失去或至少已漸褪色的才智、容貌、權力、熱鬧更加眷戀,不願接受現實,逆天而為,所謂老年戒之在得的「得」,大概就是指這種心情。要避開這兩個對自己、對社會都不好的極端,首先要瞭解,並且接受自己當前所「能」,然後量能而為,做自己能做的,自然也能愛自己所做的。
這個想法在當時也只是理論上的思索,覺得實際上自己智力、體力離這需要警惕的境界還遠得很,只是當做一種指導原則,以規劃未來。我選擇了四個範圍:科普寫作、科學教育、兩岸關係和棋橋旅遊——有社會責任,有個人嗜好,在這四個範圍內,量力選擇而為。這樣有大半年,不與世爭,為己能為,愉快自在。
但想不到,真正面臨抉擇「做我所能」的時刻卻提前到來。一九九九年六月,我從雲南麗江做了一次旅遊回來,非常之累,又忙著籌辦吳健雄科學營。六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主持開會,已經覺得腳很重,提不起來,可是沒有警覺,覺得沒有關係。到星期五晚上還為清大成立科技管理學院的事,和劉炯朗校長及彭中平教務長一齊參加一個應酬,出來時走路已是一拖一拖的了。
自己開車回去,車又停得很遠,拖著腳走到家,一頭的汗,洗了個澡,爬上床。星期六起來,腳沒有輕些,就躺在床上,到下午覺得愈來愈不對勁,太太帶著小孩上陽明山娘家去了,只有打電話給母親,她叫我從前的祕書吳錚女士來看我。她一看就說我中風了,趕快叫了計程車上醫院,到時是晚上六、七點,還能走,是自己拄著雨傘當拐杖走進去的。
那天是週末,大醫生休假去了,一個實習醫生,看了看、扳了扳我的手指,說是中風,但不知是栓塞還是溢血,要觀察,把我往急診室一放,就走了。吳祕書一邊打電話給我太太,一邊跟我說:「趕快找院長或者副院長,你不是都認識嗎?」我正在猶豫,妻已從山上趕到,我們想週六深夜為這點「小事」麻煩人家,也許不必了。因此,那天晚上就單獨在急診室的一個房間的小床上度過。對中風我並不瞭解,但是漸漸的感覺手指、腳趾不聽使喚了,這是很可怕的感覺,是不是就此癱瘓呢!那時開始想今後生死的問題。
到了星期天早晨,手臂不能抬,腳不能動,嘴巴也開始發麻,這才真正開始緊張,趕快去找一位平常認識的副院長,他在十點多趕到,一看就知道是中風,而且慢慢的在惡化,但他不是專家,不敢下診斷。那時已是星期天中午了,趕快去找神經科的醫生,下午四、五點科主任趕來了,匆匆的診斷一下,判斷應該是栓塞,而且確實還在加劇,趕緊打針吃藥,緊急治療。
兩週後病情穩定了,又轉到復健科,準備在這兒住上較長的時間,一方面是復健,一方面是讓自己習慣以後要過的新生活。當時怎樣也想不到,這「新」生活、「舊」生活有這麼大的差別!
在過去「殘障者」對我只是遙遠的名詞,當然有同情,對殘障而奮發向上的,也有適度的尊重,但都是很遙遠的,是和自己不相同也不相關的另一類人。這次卻真正成了殘障界的一員了。醫生告訴我,復健不是復元,不可能完全恢復從前的生活,能恢復幾成,要看中風的輕重和對復健的投入。像我的情形,血管栓塞的時間很長,運動控制神經受創頗重,現在復健只能設法使從前不用的後備神經,活躍起來,作為補救。
總之,以後要適應行動不便的生活,這一點心理上先要接受。其次,中風過的人第二次中風的機率,比沒有中風過的人要高幾倍,我中風的原因是血管硬化,相當嚴重,再次中風的機率更高。追問之下,最後又坦白的告訴我,五年內再度中風的機會大概有一半以上。
台大復健科的病房是在舊大樓的一樓,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建築。房子雖舊,挑高頗高,樓外有一個封鎖了的花園,似乎很久沒人進去過了,但還給人一種花木扶疏的感覺。同樓的病友二、三十人,各式各樣病因的都有,中風的占了一半以上,每天見面,久了也漸漸相識。初去時,有一段時間,每天午夜都聽到一聲聲抑制的長嚎,是一位因骨癌把腿鋸去了一半的年輕人,以後還有幾十年活,午夜夢迴在抱怨上天對他的不公。
還有一位長期坐著輪椅的老先生,第三次中風了,被外傭推著,每天下午三時從病房出來,準時到走廊裡,對著窗外的花園,怔怔的發呆,空洞的眼神,不知是看穿了一切,還是看不見一切。
三點正是我出來拄著方圈拐杖練習走路的時候,要從他輪椅旁繞過去,一個多月,天天相見。看護告訴我,這位老先生三年多前第一次中風,出院時還不錯,是拄著拐杖自己一蹓一蹓的走出去;去年第二次中風再來,就不行了;今年第三次中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意識也不清楚了。
人生的舞台原是不停的旋轉,一個人要扮演的角色,有時是由不得自己的。但是,不要讓自己太痛苦,也不要對別人太妨礙,這樣最低限的目標,還應是自己可以控制甚至主導的。生老病死,人生必經之途,今天忽然中風,雖始所未料,但看著這位老先生的背影,人是不是一定要走到這樣的地步呢?
我九歲時,母親忽因中風在實驗室去世,我看著她下葬,慢慢的沉到墓穴下去,給我很深的印象。因此,有一段時間我非常怕死,不是怕生命的結束,而是怕一個人孤零零的埋在漆黑的地下,太寂寞、太孤單了,中夜夢醒,還常幻想怎樣到墓裡去陪伴母親。
後來長大,這樣的恐懼漸漸消失,也許是埋藏到下意識裡去了,而知識漸增,從老莊的哲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到科學的宇宙論、進化論;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地球的生命不過是太空宇宙間無數生命的滄海一粟;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自然界生生不息有其自然的法則,這樣漸漸形成自己的生死觀:個體的生死不過是群體延續的一個小環節。
像電視節目常有這樣的鏡頭:豹子、老虎這些生命力最旺盛的生物,在受傷衰弱面臨死亡的時候,就自行尋找一個陰涼隱蔽的樹蔭,慢慢踱進去,先是站著,眼神漸漸渙散,然後屈膝蹲下,忽的往地上一躺,眼睛一閉就結束了;在天空盤旋的兀鷹等候已久,在這一刻蜂擁而下,瞬息間只剩一堆骸骨。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雪山盟》(The Snows of Kilimanjaro),一開始就是一隻雪豹的殘骸,在雪山之巔。這些畫境,就像卡通片,中風後我深夜躺在病床上,訓練伸屈不聽使喚的手指時,一張張閃上心頭。
一九七○年代初,我就主持過安樂死的座談。近年來,也寫過一些探討科技對倫理的影響,尤其是生老病死的文章,但那都是從理性出發,超然的學術性討論;這次是切身的問題,主角是唯一的我,而不再是統計中的一個數字。死亡是一切的終結,這個我,沒了就沒了。
如何在老病中以理性的態度邁向和接受死亡,中風以後,開始認真思考,又想到如何實踐的問題,漸漸的歸納出一個個的結論。首先,想清楚什麼時候該接受死亡,然後,如何面對死亡之前的老病。人生許多煩惱都是因為有了抉擇才有,本來生死是一種自然過程,是上天決定的,閻王要人三更死,誰也無法留人到五更;但「人」定勝天後,一切有了改變,三更到五更之間是可以商量的。於是,個人願意忍受多少痛苦,社會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就成了一個可以抉擇的價值判斷的問題。
我躺在床上,望著不能如意伸屈的左腳趾,聽著隔壁斷斷續續傳來的嚎哭聲,得出選擇延續生命的三點結論:
一、對自己,不會是一直的痛苦。
二、對家人,不會成為不可忍受的拖累。
三、對社會,不會成為毫無貢獻的負擔。
這樣,活下去才有意義。
後來,把這三點綜合起來,再更具體的寫了一份生命遺囑,成為遺囑的一部分,全文如下:
我,沈君山,一九三二年生,今年六十八歲。鑑於此生已盡了對社會的責任,今後,如何處理個人之生命乃個人之基本權利。在此一原則下,立下此生命遺囑(Living Will)。
一、消極終止:在本人因病或其他原因,進入永久昏迷(permanent unconsciousness)或不可復原之終極狀態(irreversible terminal condition)時,不必以任何人為方式延長生命(例如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人工調頻、人工呼吸、鼻管餵食、心臟電擊,或其他救治行為等),應儘量減少痛苦的讓本人自然結束生命,免除痛苦而有尊嚴走完人生。其處理方式在本人無意識判斷時,授權下述被授權人(authorized agent named below)依上述原則執行。
二、積極終止:由於自然或意外原因(例如嚴重中風或車禍),本人腦部或身體受到不可復原之傷害(non-recoverable damage),生命雖或仍可自然維持,但—— 1. 此傷害將使本人之精神及身體陷入長期痛苦之狀態。 2. 此狀態將無法復原。 3. 維持生命對家人及社會將造成沉重之負擔。在上述情形確定時,本人將以積極方式尋求生命之終止,屆時或將尋求被授權人或相關人士做直接或間接之協助。為避免上述人士擔負道義上或法律上之責任,於此授權被授權人得在上述假設情況發生時,以積極或消極之方式協助本人終止生命,有尊嚴的走完人生。
三、在立此遺囑時,見報載荷蘭已在討論立法通過安樂死,其條件與本遺囑所述相似,惟無法忍受之痛苦僅限肉體方面,本人則認為應包括精神方面,但必須是因老化或傷病已陷入長期精神痛苦,且無法復原之狀態。本人瞭解目前在我國(台灣)尚無積極終止生命之立法,故(二)僅為原則性之敘述,在被授權人協助本人合法方式尋(二)之實踐時(例如出國至有積極安樂死立法之國家)免除其道義上及法律上之責任。
決心用文字寫下其法律效力的生命遺囑,起因是在醫院病房親睹吳大猷先生一段生死的經歷。
吳先生是我國學界前輩,中國現代物理的引進者和啟蒙者,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師。他於一九九五年八十八歲時從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引退,一九九九年因心臟病發住院。那時他已九十一歲,各方面都已經很虛弱,入院之初一度瀕危。他曾經表示不要人為急救,但醫師的天職是挽回生命,在沒有清楚的表達下,還是努力救了回來,而以後吳先生就沒有機會再做這樣的表示了。
六月中,我中風住院時,病房在十五樓,而他的病房在十四樓,就常去拜望他。吳先生腦筋還很清楚,但已愈來愈難表達,靠了維生系統維持。他後來完全不能與外界溝通,只有熱愛他的義女呤之每天照顧,為之憔悴不堪。吳先生在次年三月去世,去世前幾天還不慎把舌頭咬下一塊,想是十分痛苦。
我在台大醫院一直住到七月底,後來回到新竹繼續居家復健,每週去醫院一、兩次,檢查病情,有機會仍去探望吳先生,看到他逐漸的陷入完全無知無助的狀態,受到很大的痛苦,每次都令我震撼。想到物理學家派易士(Pais)在他的名著《愛因斯坦科學傳記》描寫愛因斯坦接受死亡的一段:「愛氏在晚年知道患了腫瘤,他告訴醫師不要為他開刀打點滴,他說他已經做完該做的事,要尊嚴的離開,用人為的方法來延續生命是沒有格調的。他問醫師,會不會是很痛苦的死亡,醫師告訴他會有點痛,但很快會過去,愛氏安心了,繼續做他的統一場論計算。他在睡夢中去世,病床邊的小几上仍攤著未完成的計算。」
派易士的這本書,吳先生是極喜愛的,也不止一次的向我提起,要我細讀。愛因斯坦的天才,凡人不可及;但他對死亡的態度和接受死亡的過程,是凡人可以做到的。吳先生一生浸沉科學,是極理性的人,一定也想效法愛氏處理自己的生死;但竟不能如願,拖延了很久,自己和親人都忍受了很大的痛苦,才走到終點。我每念及此,為之痛惜不已,也引起我的反思。
人定勝天的境界是人類一直嚮往的,但是真正到了這一步,實在是很可怕的。能力超越智慧時,如何用有限的智慧去運作無限的能力呢?對於生死,現在當然還不能完全主宰,但可以規劃了,可以有限的延長,也可以不要延長。科技進步又進步,但科技總還應是為人服務,不是人為科技服務;人還應是科技的主人,不是科技變成人的主人。生死者,人的終極大事。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寄托於來生再世;但那終究是未可知的,能真這樣相信是福氣。
但在此世,這最後的一段時刻是實在的,是人作為自身主人最後實踐自己的自由意願的時刻,但那時是如此虛弱。「生命延續得愈久愈好」,這傳統的價值觀已經根深柢固,在前科技時代或許是正確的,因為上天自然會為個體生命劃下一條線;在後科技時代,人必須要自己做主,這一條線該劃在哪裡,必須在神智清明時先期規劃,否則時機一瞬即逝,怎樣透徹的理念也無法實踐,自己還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
因此,再三斟酌,寫下了這一份生命遺囑,後來成為法律文字,能不能真的實踐,當然尚未可知,但至少已盡其在我了。
死之事有了一個交代,心裡放下一個負擔,可以回過來心境寧靜的規劃如何生了。當然,還是「做我所能,愛我所做」,只是中風大大的縮小了「能」的範圍,需要重新規範。
在對社會仍有點貢獻方面,科學普及教育還是最適合我的。為《聯合報》遍訪大師寫科技專欄當然只得中止,但科學營還可以繼續辦下去,只是受限在推動籌劃方面。至於自娛晚景,遊山玩水,呼朋喚友,雖不完全放棄,但卻是有所局限,獨自旅行很不方便。棋橋還是可以的,不便參加大比賽了,但在網路上與人爭鋒,別有樂趣。網路上有一個個的棋站、橋站,棋友和橋友們繳費註冊後,就可以上網,與網上的棋友通過網路交鋒,勝負都被網站記錄下來。
很快,每位棋友、橋友就有一定的位階,可以互相選擇適當的對手。我初上去的時候用了假名,因為技藝已比過去退步很多,不希望人知,但還是很快被認出來,和年齡與輩分都差很多的網友對壘,偶被嘲笑「你是真的沈君山嗎?」習慣了也就無所謂。
在新竹休養了兩、三個月,病情漸漸穩定下來之後,親友一直勸我除了西醫之外,也應看中醫。我算是中強度中風,要較長期的復健,能住院當然最好。大陸一般認為是中醫水準較高的地方,於是經朋友幫忙,在一九九九年的九月到北京住進了一般人稱之為「三○一」,但正式名字叫「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一住住了近兩個月。
「三○一」是一個頗具歷史性的醫院,從前只限軍方高幹就醫,現在開放了,有點像台北的榮總。我住在一般稱之為「老將軍樓」的南八科病房。文革的時候,軍隊的醫院也有避風港的作用,陳毅、葉劍英等元帥大將都在這兒住過,後來鄧小平也在三樓的一個套間去世,現在除了門油漆得比較亮滑外,和一般病房並無兩樣,房子平常空著,門上有一個牌子。我住進去的時候,這座將軍樓還沒有完全開放。我的病房在南翼的二樓,復健爬樓梯,有時就以北翼三樓的鄧室為終點,走八百步路,摸一下門,再轉身回來。對著這樣一位曾經扭轉了十億人命運的歷史巨人,人生的終點站如此儉樸平凡,每次到站,每次勾起百般感慨。
將軍樓是形如口字,但缺了一邊的洋房,中間還有個有噴水池的花園,水池早已乾枯,只餘殘荷枯葉;但園裡雜花生樹,依然生機盎然。北京的秋陽,和煦溫暖,迥異於它夏天的酷烈或者冬天的無力,所以初去的時候,還有不少病人,有的坐著輪椅,有的扶著拐杖,到園子來分享這秋陽的溫暖。見面次數多了,也多點頭打招呼,偶而交談兩句,照例不去打聽對方來歷。但你若有興趣,護士小姐會有一籮筐的話告訴你,一樣藍色平凡的病服後面,各有不平凡也不一樣的經歷。
這幾年來,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走資」——的浪潮席捲中國,但是就有些礁石孤嶼,這兒那兒的挺立在浪頭上,多少保留原來社會主義的面貌,不肯全然低頭,「三○一」就是一個例子,尤其它原是軍隊醫院,解放軍過去在社會上是有特殊地位的,這些年來是大大的低落了。「三○一」受了影響,過去的特權減少不少,軍管的色彩卻依然殘留。
我初去的時候,因為是第一個台灣去的病人,又是中風初期,被列為一級護理,掛了紅牌。南八科病房原則上把病人按病情分為三級:一級是最嚴格的,不得外出,無看護或家屬照顧不得下床;其次是二級,掛藍牌,外出要大夫批准;再其次是常規,掛綠牌,護士長點頭就可外出了。我住了一個月,才從一級升為二級。
我是從台灣去的,是「台胞」,因此開始是比照外賓收費,這就鬧了個小風波,在我給朋友報平安的信上,把這風波做這樣的描述:
在花園散步曬太陽時,常遇到病友點頭為禮,熟後也偶聊天。有一位老將軍,不知姓氏,只知道「援朝」、「懲越」之戰都曾參加,愛國情緒特別強。知道我從台灣來,常抒發他的民族感情,大半時候我就聽著,偶做解釋。他對「兩國論」當然特別反感,常刺刺不休。一天我收到醫院伙食賬單,一百元人民幣一天,同舍的只有二十三元一天,原來內外有別,我們台胞外賓,比照美國人,收得貴,據說可點特別的菜。
我把這事向老將軍講了,我說:「我們只是說說,你們卻在實踐兩國論。」他聽了臉色鐵青,默不作聲。但是,第二天醫院的伙食總務就來向我解釋,最後加收二元,二十五元一天。我去謝謝老將軍,他一聽還是多了二元,仍不以為然。我怕再多事,趕快向他解釋,這就是一國兩制,可以了。無論如何,這樣一來,我的醫療費用將比同大陸同胞,要便宜好多,兩國論的風波有這點實效,想像不到!
還有一次,我初到三○一時,楊振寧先生來探病,陪同來的還有《中國時報》的江才健,大概衣著隨便了些,在門口被門房小姐擋了駕,後來打電話驚動醫院一位大牌醫生(就是後來SARS 時頂頂大名的蔣彥永),才能進來。此後這位門房小姐大概挨了訓斥,見到我就板著臉,我試著修好(門房是一個重要職位)。
我說:「那天來的楊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年長朋友。」
她說:「誰知道你的台灣朋友是什麼人?」
「楊先生不能算『台灣』朋友。不過,你知道哪些台灣人呢?」
她說:「兩個。一個好人,一個壞人。」
「哦?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壞人」是誰?猜猜就知道,是大陸官方電視台天天宣傳抹黑的當時的台灣領導;好人呢?她說是張惠妹。
「張惠妹是誰?」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就是阿妹呀!」她對我的無知大為驚訝,就給我上了課「阿妹學」。原來,阿妹才去北京表演了一場秀,座位萬人的大體育場,從場內到門口,擠得滿滿的,風靡大陸的青少年,尤其是小姑娘們,不但迷她,而且認同她。 後來,我把此事給楊先生說了,楊先生說他在東北已有過類似的經驗。他和某歌星同機,下機後歌星前呼後擁的坐加長轎車而去;楊先生的場面雖然冷清些,也有加長轎車來接。同機旅客乃耳語相問:「那位先生是唱什麼歌的?」
我聽了加以評論,諾貝爾獎得主不如歌星未必是壞現象。首先,大陸,至少大陸的都市,已進入「美式民主初階段」,價值多元化了。其次,阿妹現象表示,雖然兩岸中年以上一代,價值觀有所差異;年輕一代,尤其基層,卻是相通的。
我是一九九九年九月下旬入三○一醫院的,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月。十一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和同樓的醫生、病友告別後,我便去向三樓鄧的病室道別,因為第二天就要出院回台灣去了。兩個月來,每天復健散步,從二樓到三樓來回三次的向此室報到。就好像游泳比賽時,游到泳池對面,用手碰一下,這一圈才算完成了。而今,此一歸去,不知何時再來。
面對兩個月來朝夕報到的此室,不勝感慨,若不中風,怎樣也不會有這樣的際遇。鄧一生三次大起大落,歷盡風波,看透世事,中年之後,成為徹頭徹尾的唯「抓」主義者——黑貓、白貓,「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年逾古稀,忽然的大權在握,「蒼茫大地,我主沉浮」,但面臨的卻是一個毛澤東遺留下來前未有過的爛攤子。如何去抓住老鼠,唯有摸著石頭過河,從不弄翻這個攤子。
但一切實事求是的基本立場出發,制定了兩條路線:建國方面取所謂「改革開放」;統一方面取所謂「一國兩制」。數十年建國的實踐,檢驗了真理:毛澤東使中國人民翻了個身,卻沒能讓她站起來;改革開放讓她站了起來,卻又把不在少數的人壓到腳下,而這不在少數的人,又正是社會主義理論上最應該照顧的。
江澤民蕭規曹隨,在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中,揹著共產體制的外殼過河,一步一摸索。到今天,中國不但沒有像蘇聯東歐的分崩離析,在世界上甚至更有地位,他日地下再見鄧小平,說一聲「不負所托」,當之無愧。但人總是受限於歷史條件的,真的要渡到彼岸,還要待第五代以後的「新中國人」重新摸索。
至於一國兩制,平心而論,站在中共的立場,若不是鄧小平的眼光及務實的心態,在當時還不容易公開的提出來。但問題不在兩制,而在一國。若像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皇民,率海之濱,莫非皇土,中國就是天下,那一國兩制,實在是非常開明的政策。但現在中國已不是天下,台灣的問題,既要從歷史眼光看,也要從世界潮流看。
試問,今天全世界除了北京以外,有哪一個國家願見中國統一?美日尤其不願意,中國愈強愈不願意。你以為咬住一個中國,就是甕中捉鱉(或者好聽點說網中捉鳥),台灣怎樣也跑不出去,他們卻讓你骨骾在喉,既不讓你吞下來,又不讓你吐出來,維持現狀,和平解決,卻不斷的軍售訂約,兩岸的中國人,付出了多少代價!
瞻望未來,如何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一個中國的原則不能變,但中央集權的國家形式,或者可以與時俱進吧。統一的目標不能動搖,但統一的方式應可研究,一國兩「治」也可以作為統一過程中的一個過渡的形式吧。
我慢慢的從鄰室一步一躓的拐回二樓的己室,望著樓下已經衰敗枯萎了的花園,有多少歷史上的大事,曾在此啟蒙,在此醞釀,心中浪潮起伏。
三十年前,我因為釣魚台運動的衝激,而開始思考國事,而提出「革新保台,一國兩治,志願統一」的看法,而決定回國,那時鄧還下放在江西的工廠做工呢。三十年光陰如大江東去,「形骸已與流年老,詩句猶爭造物功」(陸游〈幽居夏日〉)只是詩人的期望,是違反自然律的﹔「形骸已與流年老,詩句難爭造物功」才是真實的。中風終究是一個人生的大轉折點,我明天從這兒走出去,體力、精力日見退化,是肯定的事。
我對實際政治既乏興趣,又無能為力,但三十年來,也是一貫堅持,也是因緣際會,在兩岸關係上,問津尋津,也有一些看法,一些際遇,一些影響。待時機適合,還是應該把它整理出來。作為真正的《浮生後記》,回到自己病房時,已暗暗的下了決心。
回台之後,篩選那一段時期與兩岸有關的論述對話,再始之以此為主之自述,成為本書。
沈君山(吳大猷學術基金會董事長)
我是在一九九八年從清大退休的。對有些人而言,退休是生命的一個大轉折,是從人生的舞台上退下來了;我的感覺卻只是人生旋轉舞台又轉過了一景。
「退休」是一個現代名詞,中國從前稱之為「致仕」。「仕」是官或公務人員的意思,致仕就是從官場退下來,不再吃皇帝老子的飯了。但是「士」還是士,那個時代,「仕」是士的正途也幾乎是士唯一的專業,讀書人總要到仕途去轉一趟,才算盡了讀聖賢書的本分。致仕則是回到士的本色,是從官場上退下來,但不是從人生舞台退下來,而且在農業社會,士還有他發揮的空間。
現在時代不同,市場經濟下,社會專業劃分得更細、競爭更激烈,形式上個人或者很自由,但壓力的束縛也許更大,無形軌道的限制也許更緊嚴,一旦退休,壓力和束縛忽然都放鬆了,是一個「量子躍變」(Quantum Jump),需要很大的調適。
我的人生經驗較不同,已經經過了兩個大轉折。二十五歲出國是第一次,從台灣到美國,文化上很需要一番調適。但像我們那代的菁英青年一樣,也只有盡力在潮流安排的軌道下向前衝。十六年後,我在四十一歲時回國,是第二春,也是第二個大轉折,變換了軌道,其後又度過二十五年。其間雖然擔任過短期的公職,也參與了很多社會活動,但基本上還是在校園度過,過的是士的生活。從學校退休,有形的責任沒有了,無形的空間也許更大,也可以說人生第三春的開始吧。
在退休前後,與傳媒界的一些資深同仁聊天,都是很久的朋友了,曾被訪問也偶寫專欄,忽然發現自己一下就從青年才俊跳到「走過從前」的見證人了。被半開玩笑的問:「那你以後做什麼呢?」當時的總結是「做我所愛,愛我所做」。後來想想,改了一字,「做我所能,愛我所做」更適當些,雖一字之差,「能」和「愛」,是有距離的。
人退休之後進入老年,有兩個不同方面的忌諱:一是消沉下去,覺得自己是用舊了的,只能做汽車備胎的第五只輪胎,在各種場合都退縮不前;二是絕不服老,對於已經失去或至少已漸褪色的才智、容貌、權力、熱鬧更加眷戀,不願接受現實,逆天而為,所謂老年戒之在得的「得」,大概就是指這種心情。要避開這兩個對自己、對社會都不好的極端,首先要瞭解,並且接受自己當前所「能」,然後量能而為,做自己能做的,自然也能愛自己所做的。
這個想法在當時也只是理論上的思索,覺得實際上自己智力、體力離這需要警惕的境界還遠得很,只是當做一種指導原則,以規劃未來。我選擇了四個範圍:科普寫作、科學教育、兩岸關係和棋橋旅遊——有社會責任,有個人嗜好,在這四個範圍內,量力選擇而為。這樣有大半年,不與世爭,為己能為,愉快自在。
但想不到,真正面臨抉擇「做我所能」的時刻卻提前到來。一九九九年六月,我從雲南麗江做了一次旅遊回來,非常之累,又忙著籌辦吳健雄科學營。六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主持開會,已經覺得腳很重,提不起來,可是沒有警覺,覺得沒有關係。到星期五晚上還為清大成立科技管理學院的事,和劉炯朗校長及彭中平教務長一齊參加一個應酬,出來時走路已是一拖一拖的了。
自己開車回去,車又停得很遠,拖著腳走到家,一頭的汗,洗了個澡,爬上床。星期六起來,腳沒有輕些,就躺在床上,到下午覺得愈來愈不對勁,太太帶著小孩上陽明山娘家去了,只有打電話給母親,她叫我從前的祕書吳錚女士來看我。她一看就說我中風了,趕快叫了計程車上醫院,到時是晚上六、七點,還能走,是自己拄著雨傘當拐杖走進去的。
那天是週末,大醫生休假去了,一個實習醫生,看了看、扳了扳我的手指,說是中風,但不知是栓塞還是溢血,要觀察,把我往急診室一放,就走了。吳祕書一邊打電話給我太太,一邊跟我說:「趕快找院長或者副院長,你不是都認識嗎?」我正在猶豫,妻已從山上趕到,我們想週六深夜為這點「小事」麻煩人家,也許不必了。因此,那天晚上就單獨在急診室的一個房間的小床上度過。對中風我並不瞭解,但是漸漸的感覺手指、腳趾不聽使喚了,這是很可怕的感覺,是不是就此癱瘓呢!那時開始想今後生死的問題。
到了星期天早晨,手臂不能抬,腳不能動,嘴巴也開始發麻,這才真正開始緊張,趕快去找一位平常認識的副院長,他在十點多趕到,一看就知道是中風,而且慢慢的在惡化,但他不是專家,不敢下診斷。那時已是星期天中午了,趕快去找神經科的醫生,下午四、五點科主任趕來了,匆匆的診斷一下,判斷應該是栓塞,而且確實還在加劇,趕緊打針吃藥,緊急治療。
兩週後病情穩定了,又轉到復健科,準備在這兒住上較長的時間,一方面是復健,一方面是讓自己習慣以後要過的新生活。當時怎樣也想不到,這「新」生活、「舊」生活有這麼大的差別!
在過去「殘障者」對我只是遙遠的名詞,當然有同情,對殘障而奮發向上的,也有適度的尊重,但都是很遙遠的,是和自己不相同也不相關的另一類人。這次卻真正成了殘障界的一員了。醫生告訴我,復健不是復元,不可能完全恢復從前的生活,能恢復幾成,要看中風的輕重和對復健的投入。像我的情形,血管栓塞的時間很長,運動控制神經受創頗重,現在復健只能設法使從前不用的後備神經,活躍起來,作為補救。
總之,以後要適應行動不便的生活,這一點心理上先要接受。其次,中風過的人第二次中風的機率,比沒有中風過的人要高幾倍,我中風的原因是血管硬化,相當嚴重,再次中風的機率更高。追問之下,最後又坦白的告訴我,五年內再度中風的機會大概有一半以上。
台大復健科的病房是在舊大樓的一樓,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建築。房子雖舊,挑高頗高,樓外有一個封鎖了的花園,似乎很久沒人進去過了,但還給人一種花木扶疏的感覺。同樓的病友二、三十人,各式各樣病因的都有,中風的占了一半以上,每天見面,久了也漸漸相識。初去時,有一段時間,每天午夜都聽到一聲聲抑制的長嚎,是一位因骨癌把腿鋸去了一半的年輕人,以後還有幾十年活,午夜夢迴在抱怨上天對他的不公。
還有一位長期坐著輪椅的老先生,第三次中風了,被外傭推著,每天下午三時從病房出來,準時到走廊裡,對著窗外的花園,怔怔的發呆,空洞的眼神,不知是看穿了一切,還是看不見一切。
三點正是我出來拄著方圈拐杖練習走路的時候,要從他輪椅旁繞過去,一個多月,天天相見。看護告訴我,這位老先生三年多前第一次中風,出院時還不錯,是拄著拐杖自己一蹓一蹓的走出去;去年第二次中風再來,就不行了;今年第三次中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意識也不清楚了。
人生的舞台原是不停的旋轉,一個人要扮演的角色,有時是由不得自己的。但是,不要讓自己太痛苦,也不要對別人太妨礙,這樣最低限的目標,還應是自己可以控制甚至主導的。生老病死,人生必經之途,今天忽然中風,雖始所未料,但看著這位老先生的背影,人是不是一定要走到這樣的地步呢?
我九歲時,母親忽因中風在實驗室去世,我看著她下葬,慢慢的沉到墓穴下去,給我很深的印象。因此,有一段時間我非常怕死,不是怕生命的結束,而是怕一個人孤零零的埋在漆黑的地下,太寂寞、太孤單了,中夜夢醒,還常幻想怎樣到墓裡去陪伴母親。
後來長大,這樣的恐懼漸漸消失,也許是埋藏到下意識裡去了,而知識漸增,從老莊的哲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到科學的宇宙論、進化論;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地球的生命不過是太空宇宙間無數生命的滄海一粟;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自然界生生不息有其自然的法則,這樣漸漸形成自己的生死觀:個體的生死不過是群體延續的一個小環節。
像電視節目常有這樣的鏡頭:豹子、老虎這些生命力最旺盛的生物,在受傷衰弱面臨死亡的時候,就自行尋找一個陰涼隱蔽的樹蔭,慢慢踱進去,先是站著,眼神漸漸渙散,然後屈膝蹲下,忽的往地上一躺,眼睛一閉就結束了;在天空盤旋的兀鷹等候已久,在這一刻蜂擁而下,瞬息間只剩一堆骸骨。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雪山盟》(The Snows of Kilimanjaro),一開始就是一隻雪豹的殘骸,在雪山之巔。這些畫境,就像卡通片,中風後我深夜躺在病床上,訓練伸屈不聽使喚的手指時,一張張閃上心頭。
一九七○年代初,我就主持過安樂死的座談。近年來,也寫過一些探討科技對倫理的影響,尤其是生老病死的文章,但那都是從理性出發,超然的學術性討論;這次是切身的問題,主角是唯一的我,而不再是統計中的一個數字。死亡是一切的終結,這個我,沒了就沒了。
如何在老病中以理性的態度邁向和接受死亡,中風以後,開始認真思考,又想到如何實踐的問題,漸漸的歸納出一個個的結論。首先,想清楚什麼時候該接受死亡,然後,如何面對死亡之前的老病。人生許多煩惱都是因為有了抉擇才有,本來生死是一種自然過程,是上天決定的,閻王要人三更死,誰也無法留人到五更;但「人」定勝天後,一切有了改變,三更到五更之間是可以商量的。於是,個人願意忍受多少痛苦,社會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就成了一個可以抉擇的價值判斷的問題。
我躺在床上,望著不能如意伸屈的左腳趾,聽著隔壁斷斷續續傳來的嚎哭聲,得出選擇延續生命的三點結論:
一、對自己,不會是一直的痛苦。
二、對家人,不會成為不可忍受的拖累。
三、對社會,不會成為毫無貢獻的負擔。
這樣,活下去才有意義。
後來,把這三點綜合起來,再更具體的寫了一份生命遺囑,成為遺囑的一部分,全文如下:
我,沈君山,一九三二年生,今年六十八歲。鑑於此生已盡了對社會的責任,今後,如何處理個人之生命乃個人之基本權利。在此一原則下,立下此生命遺囑(Living Will)。
一、消極終止:在本人因病或其他原因,進入永久昏迷(permanent unconsciousness)或不可復原之終極狀態(irreversible terminal condition)時,不必以任何人為方式延長生命(例如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人工調頻、人工呼吸、鼻管餵食、心臟電擊,或其他救治行為等),應儘量減少痛苦的讓本人自然結束生命,免除痛苦而有尊嚴走完人生。其處理方式在本人無意識判斷時,授權下述被授權人(authorized agent named below)依上述原則執行。
二、積極終止:由於自然或意外原因(例如嚴重中風或車禍),本人腦部或身體受到不可復原之傷害(non-recoverable damage),生命雖或仍可自然維持,但—— 1. 此傷害將使本人之精神及身體陷入長期痛苦之狀態。 2. 此狀態將無法復原。 3. 維持生命對家人及社會將造成沉重之負擔。在上述情形確定時,本人將以積極方式尋求生命之終止,屆時或將尋求被授權人或相關人士做直接或間接之協助。為避免上述人士擔負道義上或法律上之責任,於此授權被授權人得在上述假設情況發生時,以積極或消極之方式協助本人終止生命,有尊嚴的走完人生。
三、在立此遺囑時,見報載荷蘭已在討論立法通過安樂死,其條件與本遺囑所述相似,惟無法忍受之痛苦僅限肉體方面,本人則認為應包括精神方面,但必須是因老化或傷病已陷入長期精神痛苦,且無法復原之狀態。本人瞭解目前在我國(台灣)尚無積極終止生命之立法,故(二)僅為原則性之敘述,在被授權人協助本人合法方式尋(二)之實踐時(例如出國至有積極安樂死立法之國家)免除其道義上及法律上之責任。
決心用文字寫下其法律效力的生命遺囑,起因是在醫院病房親睹吳大猷先生一段生死的經歷。
吳先生是我國學界前輩,中國現代物理的引進者和啟蒙者,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師。他於一九九五年八十八歲時從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引退,一九九九年因心臟病發住院。那時他已九十一歲,各方面都已經很虛弱,入院之初一度瀕危。他曾經表示不要人為急救,但醫師的天職是挽回生命,在沒有清楚的表達下,還是努力救了回來,而以後吳先生就沒有機會再做這樣的表示了。
六月中,我中風住院時,病房在十五樓,而他的病房在十四樓,就常去拜望他。吳先生腦筋還很清楚,但已愈來愈難表達,靠了維生系統維持。他後來完全不能與外界溝通,只有熱愛他的義女呤之每天照顧,為之憔悴不堪。吳先生在次年三月去世,去世前幾天還不慎把舌頭咬下一塊,想是十分痛苦。
我在台大醫院一直住到七月底,後來回到新竹繼續居家復健,每週去醫院一、兩次,檢查病情,有機會仍去探望吳先生,看到他逐漸的陷入完全無知無助的狀態,受到很大的痛苦,每次都令我震撼。想到物理學家派易士(Pais)在他的名著《愛因斯坦科學傳記》描寫愛因斯坦接受死亡的一段:「愛氏在晚年知道患了腫瘤,他告訴醫師不要為他開刀打點滴,他說他已經做完該做的事,要尊嚴的離開,用人為的方法來延續生命是沒有格調的。他問醫師,會不會是很痛苦的死亡,醫師告訴他會有點痛,但很快會過去,愛氏安心了,繼續做他的統一場論計算。他在睡夢中去世,病床邊的小几上仍攤著未完成的計算。」
派易士的這本書,吳先生是極喜愛的,也不止一次的向我提起,要我細讀。愛因斯坦的天才,凡人不可及;但他對死亡的態度和接受死亡的過程,是凡人可以做到的。吳先生一生浸沉科學,是極理性的人,一定也想效法愛氏處理自己的生死;但竟不能如願,拖延了很久,自己和親人都忍受了很大的痛苦,才走到終點。我每念及此,為之痛惜不已,也引起我的反思。
人定勝天的境界是人類一直嚮往的,但是真正到了這一步,實在是很可怕的。能力超越智慧時,如何用有限的智慧去運作無限的能力呢?對於生死,現在當然還不能完全主宰,但可以規劃了,可以有限的延長,也可以不要延長。科技進步又進步,但科技總還應是為人服務,不是人為科技服務;人還應是科技的主人,不是科技變成人的主人。生死者,人的終極大事。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寄托於來生再世;但那終究是未可知的,能真這樣相信是福氣。
但在此世,這最後的一段時刻是實在的,是人作為自身主人最後實踐自己的自由意願的時刻,但那時是如此虛弱。「生命延續得愈久愈好」,這傳統的價值觀已經根深柢固,在前科技時代或許是正確的,因為上天自然會為個體生命劃下一條線;在後科技時代,人必須要自己做主,這一條線該劃在哪裡,必須在神智清明時先期規劃,否則時機一瞬即逝,怎樣透徹的理念也無法實踐,自己還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
因此,再三斟酌,寫下了這一份生命遺囑,後來成為法律文字,能不能真的實踐,當然尚未可知,但至少已盡其在我了。
死之事有了一個交代,心裡放下一個負擔,可以回過來心境寧靜的規劃如何生了。當然,還是「做我所能,愛我所做」,只是中風大大的縮小了「能」的範圍,需要重新規範。
在對社會仍有點貢獻方面,科學普及教育還是最適合我的。為《聯合報》遍訪大師寫科技專欄當然只得中止,但科學營還可以繼續辦下去,只是受限在推動籌劃方面。至於自娛晚景,遊山玩水,呼朋喚友,雖不完全放棄,但卻是有所局限,獨自旅行很不方便。棋橋還是可以的,不便參加大比賽了,但在網路上與人爭鋒,別有樂趣。網路上有一個個的棋站、橋站,棋友和橋友們繳費註冊後,就可以上網,與網上的棋友通過網路交鋒,勝負都被網站記錄下來。
很快,每位棋友、橋友就有一定的位階,可以互相選擇適當的對手。我初上去的時候用了假名,因為技藝已比過去退步很多,不希望人知,但還是很快被認出來,和年齡與輩分都差很多的網友對壘,偶被嘲笑「你是真的沈君山嗎?」習慣了也就無所謂。
在新竹休養了兩、三個月,病情漸漸穩定下來之後,親友一直勸我除了西醫之外,也應看中醫。我算是中強度中風,要較長期的復健,能住院當然最好。大陸一般認為是中醫水準較高的地方,於是經朋友幫忙,在一九九九年的九月到北京住進了一般人稱之為「三○一」,但正式名字叫「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一住住了近兩個月。
「三○一」是一個頗具歷史性的醫院,從前只限軍方高幹就醫,現在開放了,有點像台北的榮總。我住在一般稱之為「老將軍樓」的南八科病房。文革的時候,軍隊的醫院也有避風港的作用,陳毅、葉劍英等元帥大將都在這兒住過,後來鄧小平也在三樓的一個套間去世,現在除了門油漆得比較亮滑外,和一般病房並無兩樣,房子平常空著,門上有一個牌子。我住進去的時候,這座將軍樓還沒有完全開放。我的病房在南翼的二樓,復健爬樓梯,有時就以北翼三樓的鄧室為終點,走八百步路,摸一下門,再轉身回來。對著這樣一位曾經扭轉了十億人命運的歷史巨人,人生的終點站如此儉樸平凡,每次到站,每次勾起百般感慨。
將軍樓是形如口字,但缺了一邊的洋房,中間還有個有噴水池的花園,水池早已乾枯,只餘殘荷枯葉;但園裡雜花生樹,依然生機盎然。北京的秋陽,和煦溫暖,迥異於它夏天的酷烈或者冬天的無力,所以初去的時候,還有不少病人,有的坐著輪椅,有的扶著拐杖,到園子來分享這秋陽的溫暖。見面次數多了,也多點頭打招呼,偶而交談兩句,照例不去打聽對方來歷。但你若有興趣,護士小姐會有一籮筐的話告訴你,一樣藍色平凡的病服後面,各有不平凡也不一樣的經歷。
這幾年來,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走資」——的浪潮席捲中國,但是就有些礁石孤嶼,這兒那兒的挺立在浪頭上,多少保留原來社會主義的面貌,不肯全然低頭,「三○一」就是一個例子,尤其它原是軍隊醫院,解放軍過去在社會上是有特殊地位的,這些年來是大大的低落了。「三○一」受了影響,過去的特權減少不少,軍管的色彩卻依然殘留。
我初去的時候,因為是第一個台灣去的病人,又是中風初期,被列為一級護理,掛了紅牌。南八科病房原則上把病人按病情分為三級:一級是最嚴格的,不得外出,無看護或家屬照顧不得下床;其次是二級,掛藍牌,外出要大夫批准;再其次是常規,掛綠牌,護士長點頭就可外出了。我住了一個月,才從一級升為二級。
我是從台灣去的,是「台胞」,因此開始是比照外賓收費,這就鬧了個小風波,在我給朋友報平安的信上,把這風波做這樣的描述:
在花園散步曬太陽時,常遇到病友點頭為禮,熟後也偶聊天。有一位老將軍,不知姓氏,只知道「援朝」、「懲越」之戰都曾參加,愛國情緒特別強。知道我從台灣來,常抒發他的民族感情,大半時候我就聽著,偶做解釋。他對「兩國論」當然特別反感,常刺刺不休。一天我收到醫院伙食賬單,一百元人民幣一天,同舍的只有二十三元一天,原來內外有別,我們台胞外賓,比照美國人,收得貴,據說可點特別的菜。
我把這事向老將軍講了,我說:「我們只是說說,你們卻在實踐兩國論。」他聽了臉色鐵青,默不作聲。但是,第二天醫院的伙食總務就來向我解釋,最後加收二元,二十五元一天。我去謝謝老將軍,他一聽還是多了二元,仍不以為然。我怕再多事,趕快向他解釋,這就是一國兩制,可以了。無論如何,這樣一來,我的醫療費用將比同大陸同胞,要便宜好多,兩國論的風波有這點實效,想像不到!
還有一次,我初到三○一時,楊振寧先生來探病,陪同來的還有《中國時報》的江才健,大概衣著隨便了些,在門口被門房小姐擋了駕,後來打電話驚動醫院一位大牌醫生(就是後來SARS 時頂頂大名的蔣彥永),才能進來。此後這位門房小姐大概挨了訓斥,見到我就板著臉,我試著修好(門房是一個重要職位)。
我說:「那天來的楊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年長朋友。」
她說:「誰知道你的台灣朋友是什麼人?」
「楊先生不能算『台灣』朋友。不過,你知道哪些台灣人呢?」
她說:「兩個。一個好人,一個壞人。」
「哦?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壞人」是誰?猜猜就知道,是大陸官方電視台天天宣傳抹黑的當時的台灣領導;好人呢?她說是張惠妹。
「張惠妹是誰?」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就是阿妹呀!」她對我的無知大為驚訝,就給我上了課「阿妹學」。原來,阿妹才去北京表演了一場秀,座位萬人的大體育場,從場內到門口,擠得滿滿的,風靡大陸的青少年,尤其是小姑娘們,不但迷她,而且認同她。 後來,我把此事給楊先生說了,楊先生說他在東北已有過類似的經驗。他和某歌星同機,下機後歌星前呼後擁的坐加長轎車而去;楊先生的場面雖然冷清些,也有加長轎車來接。同機旅客乃耳語相問:「那位先生是唱什麼歌的?」
我聽了加以評論,諾貝爾獎得主不如歌星未必是壞現象。首先,大陸,至少大陸的都市,已進入「美式民主初階段」,價值多元化了。其次,阿妹現象表示,雖然兩岸中年以上一代,價值觀有所差異;年輕一代,尤其基層,卻是相通的。
我是一九九九年九月下旬入三○一醫院的,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月。十一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和同樓的醫生、病友告別後,我便去向三樓鄧的病室道別,因為第二天就要出院回台灣去了。兩個月來,每天復健散步,從二樓到三樓來回三次的向此室報到。就好像游泳比賽時,游到泳池對面,用手碰一下,這一圈才算完成了。而今,此一歸去,不知何時再來。
面對兩個月來朝夕報到的此室,不勝感慨,若不中風,怎樣也不會有這樣的際遇。鄧一生三次大起大落,歷盡風波,看透世事,中年之後,成為徹頭徹尾的唯「抓」主義者——黑貓、白貓,「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年逾古稀,忽然的大權在握,「蒼茫大地,我主沉浮」,但面臨的卻是一個毛澤東遺留下來前未有過的爛攤子。如何去抓住老鼠,唯有摸著石頭過河,從不弄翻這個攤子。
但一切實事求是的基本立場出發,制定了兩條路線:建國方面取所謂「改革開放」;統一方面取所謂「一國兩制」。數十年建國的實踐,檢驗了真理:毛澤東使中國人民翻了個身,卻沒能讓她站起來;改革開放讓她站了起來,卻又把不在少數的人壓到腳下,而這不在少數的人,又正是社會主義理論上最應該照顧的。
江澤民蕭規曹隨,在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中,揹著共產體制的外殼過河,一步一摸索。到今天,中國不但沒有像蘇聯東歐的分崩離析,在世界上甚至更有地位,他日地下再見鄧小平,說一聲「不負所托」,當之無愧。但人總是受限於歷史條件的,真的要渡到彼岸,還要待第五代以後的「新中國人」重新摸索。
至於一國兩制,平心而論,站在中共的立場,若不是鄧小平的眼光及務實的心態,在當時還不容易公開的提出來。但問題不在兩制,而在一國。若像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皇民,率海之濱,莫非皇土,中國就是天下,那一國兩制,實在是非常開明的政策。但現在中國已不是天下,台灣的問題,既要從歷史眼光看,也要從世界潮流看。
試問,今天全世界除了北京以外,有哪一個國家願見中國統一?美日尤其不願意,中國愈強愈不願意。你以為咬住一個中國,就是甕中捉鱉(或者好聽點說網中捉鳥),台灣怎樣也跑不出去,他們卻讓你骨骾在喉,既不讓你吞下來,又不讓你吐出來,維持現狀,和平解決,卻不斷的軍售訂約,兩岸的中國人,付出了多少代價!
瞻望未來,如何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一個中國的原則不能變,但中央集權的國家形式,或者可以與時俱進吧。統一的目標不能動搖,但統一的方式應可研究,一國兩「治」也可以作為統一過程中的一個過渡的形式吧。
我慢慢的從鄰室一步一躓的拐回二樓的己室,望著樓下已經衰敗枯萎了的花園,有多少歷史上的大事,曾在此啟蒙,在此醞釀,心中浪潮起伏。
三十年前,我因為釣魚台運動的衝激,而開始思考國事,而提出「革新保台,一國兩治,志願統一」的看法,而決定回國,那時鄧還下放在江西的工廠做工呢。三十年光陰如大江東去,「形骸已與流年老,詩句猶爭造物功」(陸游〈幽居夏日〉)只是詩人的期望,是違反自然律的﹔「形骸已與流年老,詩句難爭造物功」才是真實的。中風終究是一個人生的大轉折點,我明天從這兒走出去,體力、精力日見退化,是肯定的事。
我對實際政治既乏興趣,又無能為力,但三十年來,也是一貫堅持,也是因緣際會,在兩岸關係上,問津尋津,也有一些看法,一些際遇,一些影響。待時機適合,還是應該把它整理出來。作為真正的《浮生後記》,回到自己病房時,已暗暗的下了決心。
回台之後,篩選那一段時期與兩岸有關的論述對話,再始之以此為主之自述,成為本書。
內容連載
施明德
我第一次認識施明德,是一九八○年初美麗島軍法大審時。高雄事件後,他逃匿多時,後來成為台中市長的張溫鷹還幫他易過容,最後隔了幾個月才在一間閣樓上被抓到,那段時間報紙每天都登他的消息,給人一種汪洋大盜的印象。
所以他出庭那天,我們旁聽觀審的都抱著興奮好奇的心理,果然他搖啊搖的、自在的走進來,一點也不在乎的樣子,而且當庭和自己的律師爭辯起來,異峰突起,真是絕無冷場。
法庭上向來敵我陣營分明,被告絕對是與自己的辯護律師合作無間、共同「禦敵」,沒聽說過有被告和自己的律師當庭對吵這種突兀場面的。
當時這樣的罪名相當嚴重,是戒嚴法中的所謂「二條一」,定罪後是唯一死刑。但施明德居然完全不否認,而且還順著法官,頗為自得的說:「沒錯,我是,我主張合法顛覆政府!」面對施明德的脫稿演出,坐在後方的辯護律師鄭勝助(施明德當時有兩位辯護律師,一位是鄭勝助,另一位是尤清)嚇了一大跳,當場連忙澄清:「法官,他沒有顛覆啦!他沒有要顛覆政府!」兩人相吵的原因是施明德的一句用詞,充滿肅殺氣氛的法庭上,法官問施明德是否意圖「顛覆政府」?
沒想到施明德卻毫不領情,而且還愈說愈高昂:「民主國家都有合法顛覆政府的制度,例如美國就是每四年顛覆一次……。」他繼續堅持自己的確在「顛覆政府」,還引經據典力陳合法顛覆政府之合理必要。
鄭律師怎麼想也想不到,居然有人會自己替自己套上罪名,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的他,只能急得頻頻否認施的話:「你沒有顛覆!你這樣不叫顛覆……」兩人當場槓上。律師強調法律上顛覆就是顛覆,沒有什麼合法顛覆、非法顛覆的,但施明德依舊堅持自己的說法沒錯,民主政治就允許合法顛覆。
後來,他被判了無期徒刑。原來是死刑的,是蔣經國諮詢了多位人士,才手下留情,這段經過,我從側面有相當瞭解,但也沒有再私下見過他。直到九○年代中,他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做美麗島口述歷史的工作,我也是受訪者之一,因此,和他又多了些認識。結束時他請大家吃飯,席間,有人打趣提起傳聞中他對交女友的「三不」政策,他坦率的承認開玩笑說過「不主動、不拒絕」,最後的「不負責」卻是別人加的。
我第一次認識施明德,是一九八○年初美麗島軍法大審時。高雄事件後,他逃匿多時,後來成為台中市長的張溫鷹還幫他易過容,最後隔了幾個月才在一間閣樓上被抓到,那段時間報紙每天都登他的消息,給人一種汪洋大盜的印象。
所以他出庭那天,我們旁聽觀審的都抱著興奮好奇的心理,果然他搖啊搖的、自在的走進來,一點也不在乎的樣子,而且當庭和自己的律師爭辯起來,異峰突起,真是絕無冷場。
法庭上向來敵我陣營分明,被告絕對是與自己的辯護律師合作無間、共同「禦敵」,沒聽說過有被告和自己的律師當庭對吵這種突兀場面的。
當時這樣的罪名相當嚴重,是戒嚴法中的所謂「二條一」,定罪後是唯一死刑。但施明德居然完全不否認,而且還順著法官,頗為自得的說:「沒錯,我是,我主張合法顛覆政府!」面對施明德的脫稿演出,坐在後方的辯護律師鄭勝助(施明德當時有兩位辯護律師,一位是鄭勝助,另一位是尤清)嚇了一大跳,當場連忙澄清:「法官,他沒有顛覆啦!他沒有要顛覆政府!」兩人相吵的原因是施明德的一句用詞,充滿肅殺氣氛的法庭上,法官問施明德是否意圖「顛覆政府」?
沒想到施明德卻毫不領情,而且還愈說愈高昂:「民主國家都有合法顛覆政府的制度,例如美國就是每四年顛覆一次……。」他繼續堅持自己的確在「顛覆政府」,還引經據典力陳合法顛覆政府之合理必要。
鄭律師怎麼想也想不到,居然有人會自己替自己套上罪名,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的他,只能急得頻頻否認施的話:「你沒有顛覆!你這樣不叫顛覆……」兩人當場槓上。律師強調法律上顛覆就是顛覆,沒有什麼合法顛覆、非法顛覆的,但施明德依舊堅持自己的說法沒錯,民主政治就允許合法顛覆。
後來,他被判了無期徒刑。原來是死刑的,是蔣經國諮詢了多位人士,才手下留情,這段經過,我從側面有相當瞭解,但也沒有再私下見過他。直到九○年代中,他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做美麗島口述歷史的工作,我也是受訪者之一,因此,和他又多了些認識。結束時他請大家吃飯,席間,有人打趣提起傳聞中他對交女友的「三不」政策,他坦率的承認開玩笑說過「不主動、不拒絕」,最後的「不負責」卻是別人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