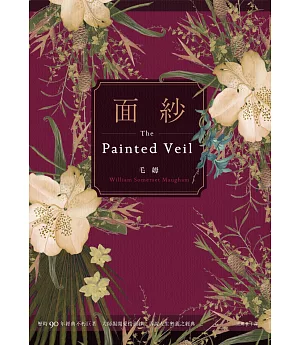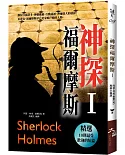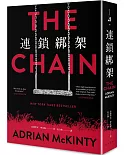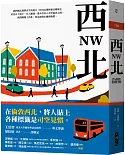導讀|揭開人生面紗之後……
文/鄧鴻樹(台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毛姆是英國現代文學史上首位以中國為題材的作家。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五年間,他發表三部以中國為背景的暢銷作品:劇作《蘇伊士之東》(East of Suez)、遊記《在中國屏風上》(On a Chinese Screen)、以及小說《面紗》。當時恰逢現代主義興起,毛姆的實驗精神雖不及同期作家,他對東方的追尋仍為英國讀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題材。
《面紗》作於毛姆事業的巔峰,延續《月亮與六便士》(一九一九年)人生如畫的寓意,預告《餅與酒》(一九三○年)揭發人生真相的旨意。一九二○至一九二九年間,毛姆共發表十一部戲,卻只出版《面紗》這本小說。因此,本書意義特殊,值得了解。
◎毛姆的婚姻與中國行
《面紗》背景設於霍亂橫行的中國,派駐香港的英籍醫生婚姻破裂,出軌妻意外懷孕,丈夫以出人意料的手段報復,妻子將如何追尋幸福,最後有驚人發現。
本書以抓姦開場,善用以對話為主的戲劇手法,章節緊湊,如劇場景幕更迭,展現毛姆編戲的才華。
如毛姆於序言透露,故事「角色的骨架」源自他在「不同情境裡認識的真人」。這些真人真事的「情境」很可能來自他涉及的婚姻醜聞與隨後的中國之旅。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毛姆與有夫之婦雪瑞.惠康(Syrie Wellcome)爆發婚外情。雪瑞父親為知名慈善家湯馬士.巴納多(Thomas Barnardo),丈夫為製藥家亨利.惠康(Henry Wellcome)。雪瑞無意從事父親建議的中國傳教事業,對丈夫的救世濟人也毫無興趣,人生痛苦之際與毛姆熱戀,一九一五年生下私生女。
惠康無法接受妻子與毛姆的「姦情」,一狀告上法院。一九一六年二月,毛姆這位名作家成為離婚官司的共同被告,非常難堪。毛姆那時已遇見人生伴侶傑拉德.哈克斯頓(Gerald Haxton),深怕若不娶雪瑞,同志身分將會曝光(同性戀當時違法),一九一七年五月在美國與雪瑞匆促完婚。同年秋,毛姆赴瑞士參與英國諜報工作,積勞成疾,染上奪走母親性命的肺癆。
毛姆妻子婚後發覺他另有地下情人,還是男兒身,非常受傷,婚姻急轉直下,瀕臨破裂。毛姆健康好轉後,一九一九年八月拋下一切,遠赴芝加哥與哈克斯頓會合,共赴中國。他們從香港一路北上,四處雲遊拜會,回程還深入內地,一九二○年四月才結束旅程。
這趟旅途的見聞將成為《面紗》的重要素材:醜態畢露的殖民社會、特異獨行的歐洲人、犧牲奉獻的傳教士等。中國隨處可見的腳伕、田埂竹林、貞節牌坊、城牆廟宇,乃至棄嬰孤兒等畫面,令毛姆印象深刻,忠實化為小說場景。書中有關偷情的描寫,除改寫自他在香港聽來的一段醜聞,也可能源自他的親身經驗。毛姆幼年雙親病故,疾病與死亡的陰影貫穿全書,具有強烈的自傳性。
◎粉彩人生,霧裡看花
《面紗》書名原文出自浪漫詩人雪萊一八一八年的詩作〈勿掀粉彩面紗〉(“Lift Not the Painted Veil”)。人生幻麗,如同粉彩面紗欺瞞視線:「我知有人脆弱心碎,掀起面紗,卻遍尋不著心愛之物」。
雪萊是命運最坎坷的浪漫詩人。他與妹妹的同學私奔,不到三年婚姻失敗;一八一五年情婦瑪莉(Mary Godwin)所生的私生女夭折;一八一六年十一月,元配投湖自盡;他與情婦成婚後又與其妹有染,一八一八年私生女誕生,同年,一歲女兒不幸病逝;一八二○年,送人領養的私生女不幸去世。一八二二年,歷經連串打擊,雪萊命喪義大利的一場船難,二十九歲客死異鄉。
毛姆曾為婦科醫師,目睹許多單親媽媽的慘況,對偷情所致之家破人亡特別有感,曾根據行醫經驗寫成處女作《蘭貝斯的莉莎》(Liza of Lambeth, 一八九七)。《面紗》延續毛姆對受害婦女的關注,對女性人生幻滅的過程,有深刻的描寫。
女主角吉娣來到中國,編織幻麗夢想,「情欲獲得滿足的心無所牽掛」,藉偷情逃避現實,「將自己比擬為清晨悠閒掠過稻田的白鷺鷥」。中國城鎮縹渺虛幻,「宛如彌撒書裡所述的城市」,帶來慰藉。
無奈,「憂慮的暗潮卻洶湧不歇」,異地生活有如「一幅五顏六色的畫布」,美夢「徹底不真實」,周遭「全是一齣假面劇裡的虛構人物」。她意外懷孕後,飽受羞恥的煎熬,同時失去兩個男人,就像雪萊詩句裡的「脆弱心碎」之人,最後「遍尋不著心愛之物」,令人同情。
◎面紗後的神祕真相
《面紗》最為神祕之處,在於女主角的婚姻破滅,可能另有隱情。
沃特長年旅居海外研究細菌學,婚後在中國全心防疫,與妻子甚少相處。他成天與一位神祕的余上校為伍,令妻子十分不解。沃特死前,吉娣終於見到這位「守在床邊的男人」:「他是余上校。他一刻不曾離開床邊」。余上校「眼眶泛淚光」,令她納悶:「心頭不禁一揪。這個黃臉胖子為什麼眼裡含淚?」
沃特「天生就注重隱私」,「床笫間,兩人的互動也未能讓吉娣更貼近他」;每當他「顯露外人不知的一面」,妻子「對他的鄙夷就多一分」。沃特與余上校有何私交?故事並未清楚交代。讀者只能從妻子的控訴,略窺面紗後的真相:「我自始至終都覺得你面目可憎」,「我認為你根本不是男子漢」。
吉娣後來發現,「身邊所有人」可能都跟自己一樣,「也全私藏可恥的祕密」。有人認為「人生本身就美」;吉娣卻驚然發覺,美麗人生實為不可揭發的謊言。幸福幻滅後,她不願乞求「苦海眾生的宗教愛」,而想尋求「人對人的溫情」。可是,她最後卻終於領悟,人間最難尋者莫過於溫情。
吉娣的悲劇在於窺探人生的真貌。無奈,人生無法重來,她只能將希望寄託於未出世的小孩:「教她不能踏上我走錯的路」。故事結尾,她繼續編織夢想,替悲情人生塗上更多粉彩:「一幅令人屏息的美景」,虛實間,人生道路「在稻田間蜿蜒」。
粉彩面紗掀起又蓋上,吉娣的「心寧之路」終究如同白鷺鷥掠過的田埂,晨霧中格外縹渺,通往遙不可及的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