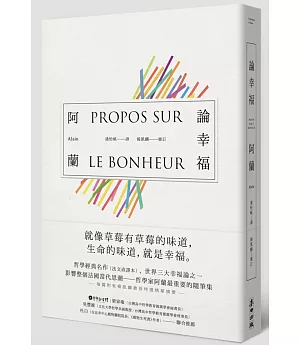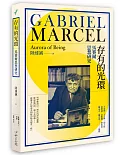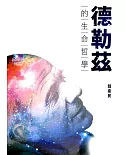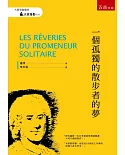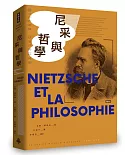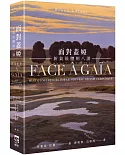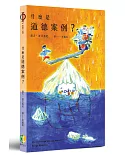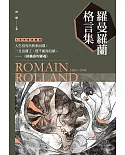譯者序
哲學家阿蘭(一八六八-一九五一)是思想的行動者。他承繼了笛卡兒的哲學思辨,然而從行事風格來看,他則是接近蘇格拉底的思想者。這意謂著,比起建構一個足以容納整個宇宙的知識體系,他更在意思想運動的不斷啟動;比起關心存有起源的問題,他更樂意探尋人該如何生活的問題。這都是哲學思想的重要關懷,而阿蘭選擇了付諸行動,這一方面呼應他的生命養成,另一方面也實證了他所謂教育的意義。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閱讀二十世紀初的作品或許有些不合時宜的疙瘩,如同散落在本書篇章裡,時而可見的馴馬、駕馬車、蒸汽火車等,除了時光逆流的倒轉感,也有觀念老舊的嫌疑。事實上,在哲思學習的過程裡從來不乏如此疑慮。身處於光影搖晃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讀者)是否仍有必要學習柏拉圖、尼采、老莊、儒家等古典思想?倘若每一種新的哲學都是對過去既有思想的批判與改良,最經濟的法則難道不正是挑最新出爐的想法來讀即可?這種對知識內容的去蕪存菁或許是哲學與科學間的最大區別。對科學而言,求真求新是根本信念;哲學做為眾學門之本,除了涵納這兩個特點之外,更涉及一種思想技術的鍛鍊。與其給人一條魚,不如教人學會用釣竿;與其給人一套道理,不如教人學會自己釐清道理;學會如何思考是哲學最基進的價值,這也是何以在任何時代裡哲學都不可能過時的原因。哲學的內容做為一種知識論,或許有汰舊換新的必要性;但它做為促發思考的運動,卻是使人有必要一再回溯各個哲學家思想脈絡的原因。我們應當認識的是如何思考,而非孰記思想的知識,而這也是阿蘭與其作品所帶給我們最核心的啟示:以思想啟動思考。
來自飼育名種馬(佩爾什馬)的民族與獸醫之子的成長背景,阿蘭的教育從不僅止於紙上的閱讀。他的書寫裡一再出現動物的譬喻及體察,例如「動物沒有脾氣」(第十二篇)、「像馬車夫駕馭馬匹一樣控制情緒」(第五十三篇)、「動物完全受制於即將來臨的暴風雨控制」、「動物不會多想」(第六十六篇)等,在在說明他的日常不乏與動物接觸的真實經驗。這種身體力行的認識隨著閱歷的增加,逐步轉化成對各種生理探究的興趣與要求直接行動的「實事求是」態度。比方說,他認為藝術家可以透過身體操演熟練的運動(鋼琴家靈巧的手指運動)去掃除、戰勝恐懼(第十七篇),而想像則可能會倍增人的痛苦(第九篇);阿蘭的想法極其實事求是,因為他的觀點總是根據不同個案的內部結構來論證,總是針對糾結處境的實際化解,好比透過農人的勞動說明快樂源自於積極爭取、透過失眠來說明放任思想的危險等等,這使得他的道理往往深入淺出、切中核心,然而,這種與個案同步的思維卻也為他帶來最大的危機,思想因此出現不一致性。
隨著個案間的差異,阿蘭的論述經常也跟著改變。例如在不同的情況下,他有時會推崇想像,認為它有益於治癒憂傷,但他有時也貶抑想像,認為只會加重憂傷(第五篇、十三篇);他在某些章節中指出戰爭對人類安寧的摧毀性,可是卻又在其他文章裡分析戰爭如何為人帶來平靜(第七十九、九十二篇)。但阿蘭從來不是一個態度曖昧的思想者,相反地,從他的書寫當中,讀者總是能夠立即感受到他明快、果決的判斷力。他每每提出不同觀點所致使的矛盾,而現實、具體的事件總是一次性與不可能重複的,因此所有面對生活處境的方法都應該因時制宜,因此必然無法一以貫之,誠如他所言:「無所事事雖是所有惡習的溫床,這同一張床卻也養育了所有的美德。」(第四十三篇)同一種主張可能會酌情之別而導致好壞兩面的結果;人在窮極無聊的時候可能會無事生事、挑釁造反的行惡,但是什麼都不做的人也同樣阻斷了行惡與暴力的可能,因為他的思想不受身體運動的干擾,從而避免了一味行動的後果。阿蘭的這番道理說明,強調應當時刻採取行動的他並非天真到毫無注意伴隨即起行動而來的不思考之惡。他從不認為有「一言以蔽之」的道理,這促使他大量書寫不同的事件與針對各個事件的不同看法,然而,在這些論述之間彼此不同調的矛盾從未使他放棄依據個案提出該勇於行動,或該克制行為的各種堅持。他隨著不同事件而搖擺的態度,最終會如同他反戰又參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爭議行徑,使自己成為自己的頭號大敵。在每一篇隨筆中,阿蘭的論點都顯得如此鏗鏘有力,但或許正因為他總是言之鑿鑿,才更凸顯了他思路上的前後不一。當讀者已然被上一篇文章裡的阿蘭說服的時候,該如何繼續面對下一篇書寫裡的那位顯然已更換立場的阿蘭?偏偏作者的驟變,從來不只是對同一種觀點的幾經反省後的修正、微調,就如同他始終反戰,也始終承認、面對那個曾經參戰過的自己一樣,那就是兩種,甚至兩種以上的想法、態度。這種堅決的語調與姿態最終促使他成為自己思想上的最大背反與爭議。
不成系統的論述造成了阿蘭哲學思想上的最大困難,這也是任何企圖繼承、構造其思想的追隨者、研究者們的最深隱憂。因為一旦脫離了他所描述的實際場景,阿蘭那曾看似強而有力的各種觀點便會開始搖晃,且顯得立論薄弱。多重可能的選擇反而會招致人的無所適從,這使得事事堅持變成一種難以捉摸的毫無堅持,實事求是其實可能是無跡可尋的毫無表態。於是,遵循阿蘭的思想從看似簡單卻變成最困難之事,因為只要處境不同,處置方法便無法被沿用。誠如他所說:「現實的災難不會重演。」(第九篇)阿蘭對個案講究實際介入的態度使得他在置身困境之時,與其推測困境的成因,他更在意如何解決眼下的問題。由此發展出來的酌情處置擴大了他論述的龐雜,各種細節上的差異因此無法被忽視、也無法被歸納成具有一致性的體系。即便在本書中的〈布賽法勒〉,阿蘭用「找別針」隱喻「事出有因」與「尋找原因」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尋找原因」仍是目的導向的,也就是為了「解決」問題,而非一種對理論、根源上的「起因」探究。這也是為什麼他不討論思想與憂鬱之間的抽象關聯,卻實際地提出身體運動的「處方」來解決憂鬱的問題。由此看來,阿蘭的「原因」做為解決方案(處方)中的之一,總是指向一種具體、可描述、可想像的情況,好比焦躁與睡不飽有關、暴力與恐懼有關;其目的在於解決、消除,而非進一步的探究、複雜化以便形成理論體系中的環節。因此,看似不斷透過論述來解答疑難雜症的阿蘭,一旦逃離了他筆墨下的描述,似乎什麼也未曾解決。然而,這樣不一致、搖擺的思想也許正是阿蘭的哲學中最精采、最核心之處,也是他將自己徹底置於傳統倫理學之外的根本姿態。
表面上,阿蘭針對人的各種處境、生活展開討論,這使得他所具體提出的處世之道很容易被視作倫理學準則。然而,無論是從他本人的書寫或原著編者的說明裡,都再三重申著他與倫理學之間的不同。即便阿蘭大量地討論幸福、教育、道德等生活議題,他的論述仍然有別於倫理學。因為相較於倫理學的系統性思想和指導生活態度與行為的準則,阿蘭提供的是無法被遵循的守則,或者更正確的講,他透過無法被按表操課的法則,以便促使思想運動。在阿蘭的文章裡,確實可以找到許多行為的準則與建議,然而這些建議與觀點往往會隨著他所描述的不同時空場景,產生自相矛盾與相互抵消的結果,這使得他的眾多「處方」變得無效。而這種無效或許意謂著另一層意思:照本宣科的重複與教條是不可能的。脫離阿蘭所描述的框架即失效的建議說明著,他的論述並非一種應當被遵循的刻板守則,他的解決方案不是為了被如法炮製、重演,而是為了促發思想運動。誠如他所說:「我的一番道理全是詭辯,卻深合我意;這些經常也是能一棒敲醒我智性的清明。」(第六篇)「合意的詭辯」與「能敲醒智性的保持清明」說明了阿蘭的重點顯然不在於真相的追查,或解套方式的提供,而在於如何維持一種智性的清明狀態。阿蘭所考慮的是如何培養自我反思及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簡言之,如何成為一個思想者。因為再大量的書寫也無法涵蓋世間所有困頓,與其提供永遠不足的藥方,不如使人成為自己的醫生,學會以思想自我療癒。如此,讀者得以明白,阿蘭的每個篇章都是關於如何思考的展演,而非必須被簡單遵照的童子軍信條。如此,讀者得以理解,阿蘭論述之間的矛盾不是邏輯上的缺失、有欠周延,而是使思想總是能夠另起爐灶、重新啟動的思想運動。在這樣的考慮之下,阿蘭說:「同樣的想法不要重複兩次。」(第七十五篇)任何現成的、已經完成的想法都不會是永恆不變的解答,因為世界總是無時不刻地處於變動之中。套用已知的思想(答案)只是反射動作,其實是不思考,而非重新經歷思想運動的正在思考中。也正是因為如此,已經成形的想法才具備其重要性。它做為思想的起點,做為必要差異的在場,是為了促使新的思想運動展開與新的思想誕生。阿蘭強調不可能重複同樣的想法,因為每一次的思想都將重新啟動一個新的思想運動,這是思想活體的在場,而非被陳腔爛調奴役的不思考。
這種展現思想運動的思考,無疑地為阿蘭的讀者指出笛卡兒的思想如何通抵蘇格拉底哲學行動的實際道路。笛卡兒在其著作《方法論》(Discours de la
méthode)的序言裡提到,「我所談的方法只對我自己有效,我的書寫也從來不是為了教给大眾一種方法,並且以為人人皆必須遵從這種方式才得以正確地運用自己的理性;而是要告訴大眾,我是如何運用我自己的理性。」論述如果具有揭示真理的能力,絕非因為論述的內容本身就是真理,論述的建構過程正在於創造一個能夠開啟、辯證真理的思想活動。在這個不斷思考、建構的過程中,才可能逐步使想法、觀點朝向真理。這是何以笛卡兒認為重點在於「如何運用理性」,他向大家展示的,其實是理性思考的行動如何實際發生,而不是某種特定的研究或思想方法。因為方法可能被推翻,可能隨著時代演進推陳出新,但只要擁有思考的能力,人便可以自己展開各種方法的串連,甚至更新思想方法。因此,書寫與閱讀各種思考方法的目的在於建構自身的一套想法,以返回蘇格拉底的思想做為一種行動的自我實踐。這便是二十世紀的阿蘭如何重返古典希臘的哲學教育路徑,也是閱讀阿蘭的不二法門:成為自己的思想者。
潘怡帆(巴黎第十大學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