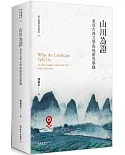修訂版自序
情色書寫沉浮錄
本書的寫作緣於一九九一年夏日的一次閒聊。那天我與西安的幾位朋友在大雁塔附近的某酒樓聚餐,在座各位多是讀書寫書之人,杯酒間不期然就談到了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的《中國古代房內考》中譯本不久前在國內公開出版之事。座中有人因此大發感慨說:「咱們中國有很多文化遺產,中國人自己沒能力沒條件發掘研究,不少領域都叫外國人捷足先登,填補了我們自己無所作為的空白。你看,主編大部頭中國科技史的人是英國的李約瑟,重構古漢語音韻系統的人是瑞典的高本漢,現在連『房中書』這類老祖宗夫婦床上把玩的圖冊都得經人家外國學者收集和探討,中國人才得知那些祕笈是怎麼一回事。」
在座的另一位接著補充說:「中譯本的書是出版了,但不是隨便哪個讀者想買就能買的。你要去新華書店選購此書,可得持單位證明,恐怕只有專家學者或某些領導才買得到手吧。」
於是又有人提議說:「老康寫風騷談豔情的書都出了,現在該趁熱打鐵,再寫本面向普通讀者評介性文化性文學的書嘛。」
我立即對諸位解釋說,我那本書的主題是「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所謂「風騷」,乃指源自《國風》和《離騷》的詩歌傳統;所謂「豔情」,則泛指吟詠女性及其閨房世界的一種香豔詩風,其實與色情文字並不沾邊。就我目前有限的閱讀範圍而言,要下筆縱論性文化性文學,還有待大量搜求材料,進一步廣泛閱讀。高羅佩那本書我還沒買到手;齊魯出版社新出的足本《金瓶梅》定價昂貴,我也買不起;《肉蒲團》等一系列明清色情小說,圖書館裡更借不出來。要想作這方面的研究,實在是無從入手啊。
座中有位評論家從北京來此地出差,他說他正好收藏了不少這方面的祕笈,都是託出國訪學的朋友在歐美各大學圖書館複印回來的,說是我若有機會去北京查找資料,他願意把他的全部收藏借給我閱讀或複印。熱心文化事業的企業家王永鋒先生那天做東,他當即鼓勵我去北京查閱資料和購買相關書籍,並當場宣佈可資助我一筆研究經費,條件是書稿完成後由他出版。
西鳳酒喝得大家都有點醉意陶然,就在此胡煽浪諞的氛圍中,我貿然接下了這個一般人多會避嫌的課題,而且仗著酒力在席間縱言告白:既然我那些談風騷說豔情的文字總難免色情嫌疑,現在索性就一頭栽進去,把色情乃至淫穢的學問做到家吧。
王先生不久即給我送來他許諾的經費,選修我「西方現代文藝思潮」課程的學生幹部也從交大團委給我開來了購書證明。我持證明從新華書店購回《中國古代房內考》一書,接下來還買了很多相關的書籍。讀完了《房內考》和《中國禁書大觀》,我基本上確定了需要查找的書目,那年秋季學期的課程一結束,我就前往北京,住進了北京圖書館附近的旅館。白天我在圖書館內瀏覽和複印相關資料,晚上回到旅館,在燈下惡補從那位評論家手中借回的《繡榻野史》等文字粗劣的末流小說。北京一月份的氣溫遠低於西安,一大早從旅館直奔北圖,大街上凍得我耳朵麻痛,吸一口氣冷徹了肺腑。就這樣,在北圖泡了好多天,我記了不少讀書筆記,複印了一包材料。回到西安,我立即動筆,趁寒假趕寫起我在酒席上承諾的書稿。
書稿時寫時停,多是因找不到需要閱讀的書籍。特別是寫「男風面面觀」一章,有篇題為〈潘文子契合鴛鴦塚〉的短篇小說,被認為是有關男同性戀敘事的原型文本,我四處查找,卻求之不得。後來終於託一熟人帶我去某大學圖書館書庫中找出不予外借的明代擬話本小說集《石點頭》,查閱目錄,發現此短篇正好收入該書的第十四卷。但翻到第十四卷所在的頁碼,眼前的空白頁上只印有「全文刪去」四字。原來這個經過「清洗」的新版本只有該篇的存目。一九四九年以後重印的某些舊小說版本,常會有此類大刪特刪的現象。官方話語對同性戀問題一貫持特別禁忌的態度,比如像《弁而釵》這類男風故事集的經典文本,即屬於頂級封存的淫書,根本連影子也找不到。我只能通過馬克夢《十七世紀中國小說中的因果與限制》和辛赤《中國男同性戀史》兩部英文著作轉述的內容瞭解其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總的來說,那時候很多涉及性和色情的書籍,凡外面不易找到的,圖書館一般也都束之高閣,祕不示人。我只好把那本刪節本《石點頭》放回書架,敗興而歸,書稿的寫作也因此中斷了好久。
我這部書稿本是急就章,真要等博採精選而後動筆,以當時的條件來看,是根本不可能的。這資訊短缺的情況反玉成了我的論述策略,由於能讀到的材料很有限,我斷然捨棄貪大求全的取向,不再走高羅佩那種羅列文獻、大量徵引原文的歷時性敘述方式,而選擇了我自己獨創的勾畫輪廓、傳達妙義、散點透視的路徑。正如我在《風騷與豔情》一書中絕不用「愛情詩」或「色情詩」之類憑空亂貼的新式標籤來框範所討論的古典詩詞,而是特拈出「風騷」與「豔情」兩個傳統用語,以其貫串始終的掃描構成了該書的敘述框架。寫這部書稿,我仍堅持採用傳統的批評用語,以「風月鑑」正反兩面的圖景檢驗從文學到政治、法律、醫藥、宗教等領域叢雜而散亂的「性文本」,同時穿插女性主義批評的透視,從而揭示出基本上供男性讀者閱讀的色情讀物如何傳達了男人的性幻想和性恐懼,如何鋪陳了富於誘惑的場景,又如何散佈了性命攸關的告誡。我特別從色情書寫發生學的意義上詳述了房中術指導性實踐的教條文字如何通過窮形極貌的「辭賦化」描寫而生發出娛樂消遣的功能,最終達成其代償性滿足的效果。為解析性文本在史書、辭賦、詩詞、小說和筆記叢談等不同文類中所傳達的趣味,所強調的懲戒,我依次推出尤物、妖后、淫婦、女鬼、狐狸精、孌童、契弟、相公、狎客等一系列風月鑑脈絡中扮演「性角色」(sexual
personae)的各類人物,通過他們沉溺、戲謔、狂歡、遭罪、受罰的經歷,深入剖析了固精、採補、仙趣、豔福、「陽道壯偉狂」等熒惑人心的性頑念。
我緊趕慢趕,終於在一九九三年春完成了這部書稿,但事過境遷,我那位資助人忙於其他生意,再也無暇過問此書的出版事宜。當時房中術和性文學正在書市上走紅,北方的一家出版社對我的書稿很感興趣,接到我的投稿,很快就出了三校稿。不巧正碰上賈平凹的小說《廢都》挨批,還沒等我看完校樣,出版社就嚇得毀約退了稿。稿子後來讓南方一家出版社熱心要去,卻在校樣出來時趕上那裡掃黃,社長怕惹事,遂壓下稿子,此後就再也沒有下文。我失去了耐心,只好把這部面向國內讀者撰寫的新書轉到台灣出版,其時已是一九九六年初。直到一九九八年底,經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力薦,遼寧教育出版社才在大陸推出了此書的簡體版。
遼寧版兩刷後再沒有續印,時隔十七年之久,如今秀威資訊又要精工重印,連帶推出其電子書新版。這至少表明,我這本舊作仍不乏潛在的市場需求,尚未在書刊過量生產的淘沙大浪中廢渣沉底。今日中國大陸的資訊傳播渠道和文化市場比起二十多年前我撰寫此書時的情況顯然更加豐富,也大膽開放了許多,儘管與台灣相比,還有很多惱人的限制。但不管怎麼說,面對影視音像螢幕日益暴露的俗豔畫面,以及網際交往中千姿百態的私密傳遞,新一代受眾已對形形色色有關性的圖文資訊見多不怪,甚至因貪求過量的感官消費,給自己平添了厭倦和疲勞。這種終於平淡消停下來的認知狀態也許最適合閱讀某些去魅消解性的文字,比如從本書重審的風月鑑中照照鏡子,沒準會照出一個人自己的、乃至我們大家的那不太願意被正視和承認的一面。本書遼教版出版後報刊上的一篇評論曾中肯地指出:
《重審風月鑑》的「審」所針對的,不僅僅是中國古典文學中關涉「風月」的一個傳統,或那些作品以及作品的寫作者。更進一步的雄心則在於:審視傳統的接受者,作品的閱讀者或者儘管並不閱讀但卻經由「亞文化」感染的、「性陳規」與「性頑念」的持有者,―這,才是真正的大多數,是我們,是始終站在窺視和偷聽的角度在想像中參與他人的性活動―藉助幻想愉悅自己、藉助恐懼嚇唬自己打擊別人的人。
我一直很欣賞王國維詞作中這句警策:「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二十多年後,我在修訂重印本校樣的過程中重讀自己的舊作,仍能從這面自我認識的鏡子中審視到自己至今尚未徹悟的癡迷和妄念。相信此「重審」之視境會經過觀者的視角調頻而反復映現,並會越審視越明晰,直至審視到風清月白,天朗水澂,確認了自我的真相。
二○一五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