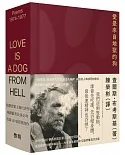前言
這本書的形成出於一串美麗的因緣。二O一四年八月中旬,陳黎受邀參加上海書展「國際文學週」,有幸與書展貴賓美國詩人羅伯特.哈斯及其夫人女詩人布蘭達.希爾曼在活動期間一起分享詩創作與翻譯的經驗。赴上海書展前,陳黎在家中閱讀布蘭達.希爾曼的詩,非常喜歡,發現她重視字本身,創新形式、探索新可能的寫作傾向與自己有些類似,忍不住中譯了她幾首詩,並在上海書展「詩歌與翻譯」論壇中引之為例。哈斯伉儷是非常富親和力且大度的前輩,與陳黎一見如故。知道陳黎在秋天將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約好屆時邀陳黎到哈斯任教、陳黎女兒陳立立正攻讀作曲博士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談詩、唸詩。下旬,陳黎赴美三個月,十月初,應約前往柏克萊,在哈斯主持下進行了一小時多演講與唸詩活動。為此柏克萊之約,陳黎在愛荷華期間即埋首中譯了一些哈斯伉儷的詩,並在柏克萊選了數首朗讀。與哈斯同在柏克萊任教的波蘭詩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一九八O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時,陳黎是最早將其詩譯成中文在報上發表者,而我們知道哈斯是米沃什詩的主要英譯者,哈斯英譯的《經典俳句:芭蕉、蕪村、一茶詩譯集》(The Essential Haiku: Versions of Basho, Buson, &
Issa)也是喜歡日本古典詩的陳黎多年來的案頭書。多重因緣,讓陳黎與哈斯伉儷約定出版一本哈斯伉儷兩人的中譯詩選,由陳黎和張芬齡合力為之,並且希望有一天哈斯伉儷能到台灣,在熱情的寶島讀者面前談詩、唸詩。
從愛荷華回到台灣後,陳黎和張芬齡持續中譯了哈斯伉儷更多詩作,並決定以「當代美國詩雙璧」之名結集。上海書展國際文學週有一場「詩歌之夜」,與會作家們輪番登台唸詩——自己的一首詩外,另選一首別人的。陳黎選的是與張芬齡中譯的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的(Wisława Szymborska)〈在一顆小星星底下〉,哈斯選的是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詩,布蘭達.希爾曼選的是狄瑾蓀(Emily Dickinson)。惠特曼和狄瑾蓀是美國詩歌的雙璧,哈斯自己也是像惠特曼般歌詠土地、自然與自我的「國民詩人」,而編有狄瑾蓀詩精選集,以處女詩集《白衣》(White Dress)向狄瑾蓀致敬的布蘭達.希爾曼,寫詩時標點、句法、形式的獨特一如狄瑾蓀。我們可以說,哈斯與希爾曼伉儷也是美國詩雙璧——當代美國詩雙璧。
一 閱讀羅伯特.哈斯
羅伯特.哈斯(Robert Hass,
1941-)是當代最知名的美國詩人之一。他的詩作富含音樂性,描述性和沉思的知性,帶給讀者會心、深刻的喜悅。哈斯曾說:「詩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類的活動,就像烤麵包或打籃球一樣。」除了寫詩,他也是評論家和翻譯家,他和諾貝爾獎得主波蘭詩人米沃什合譯了十二卷米沃什詩集,也翻譯了日本俳句大師松尾芭蕉、與謝蕪村、小林一茶的詩作。從哈斯詩作中觸及的關於詩藝以及政治的題材,我們看到米沃什對他的影響;從其文字所呈現的清澄、簡潔的風格,和取材自日常生活的意象,我們看到日本俳句的影子。哈斯對中國古典詩並不陌生。他書架上放著的年少以來陸續閱讀的相關書籍包括羅伯特.佩恩(Robert
Payne)英譯的中國古典詩選《小白馬》(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詩人龐德(Ezra Pound)的《神州集》(Cathay),王紅公(Kenneth Rexroth)英譯的《中國詩歌一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收錄、評介亞瑟.韋利(Arthur
Waley)中國古典詩英譯的《山中狂歌》(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詩人史耐德(Gary Snyder)英譯的唐代詩僧寒山的《寒山集》(Cold Mountain
Poems)。他享受中國古典詩中呈現的愉悅、明澈心境,對李白的飄逸,杜甫的憂時,寒山的灑脫印象深刻。
哈斯的第一本詩集《田野指南》(Field Guide, 1973)為他贏得耶魯年輕詩人獎,初試啼聲,即讓人驚艷。此詩集中的諸多意象源自哈斯自幼生長的加州鄉間,以及他對斯拉夫民族的研究背景。詩人佛瑞斯特.甘德(Forrest
Gander)說:「《田野指南》蘊含豐富的俄國口音,大茴香蕨類的氣味,拔除了瓶塞的酒味,以及動植物生態的指涉:舊金山灣區的綠色蛾螺和岩蟹,風琴鳥和安皇后蕾絲花,海浪和木蘭科胡椒樹。」詩人麥可.瓦特斯(Michael
Waters)稱哈斯是難得一見的好詩人,讚許《田野指南》試圖替萬物命名,透過自身成長之環境建立歸屬和認同感,將自然世界翻譯成個人歷史,這是複雜且艱鉅的工程,但哈斯用清晰明澈的文字和悲憫的心境達成了目標。名詩人史坦利.庫尼茲(Stanley
Kunitz)認為閱讀哈斯的詩就像踏入海洋之中,你渾然不覺水的溫度和空氣的溫度有何差異,當你感知拍岸的海浪回流入海時,你已然被帶入另一個元素。
在〈秋天〉一詩,我們看到哈斯這群採蘑菇的「業餘生手」為了在平凡枯索的生活注入活絡因子,拿生命與死神進行一場場豪賭:「心想有一半的機率/會因一個錯誤而致死」,「在那些日子,死亡不止一次/晃動我們,而當它漂回原位時/我們覺得又活了過來」。他們勇於嘗試,在冒險的快感中採集生之新意;他們「向事物之名漂流」,試圖到陌生的領域開發或探索生之興味。香氣濃郁的真菌名為「愛與死」,貼切但弔詭地傳遞出詩人不惜以生命作賭注來換取生機的生之慾。
在哈斯詩作中,生命活力蘊藏於生活的各個角落——在鍋裡嘶嘶作響的培根,冒著熱氣的咖啡,韓德爾的《水上音樂》,在樓上熟睡的妻子(〈房子〉);蘊藏於與生之苦難的拉鋸、抗衡之中——在窮困的歲月裡,即便物質匱乏到與妻子「為了買不買圖釘而爭辯」,仍堅持精神生活的價值,為了看部好電影,兩人寧可挨餓(〈黏著劑:給珥琳〉);蘊藏於對生存意義的艱澀思辯之中——在一成不變卻又無常的生活型態與「萬物皆動」的理論中,帶著模糊的來生概念,接納人類今生終將歇止的事實(〈關於來世,加州中部印第安人只有最模糊的概念〉);更存在於安頓身心的寫作過程中——「那生我造我者,/與其說從陽光//或李樹,不如說/是從構成這些詩行的/脈動裡。」(〈方寸〉)。
哈斯在他的第二本詩集《讚美》(Praise, 1979)再度展現創作長才,獲得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獎。此書進一步處理隱含於第一本詩集中的主題:為世界命名之舉可否讓我們自世界抽離?如何忍受憂傷,接納死亡?如何讓心靈承受磨難?詩人、詩評家毅拉.薩多夫(Ira
Sadoff)認為哈斯在第一本詩集雖然展現出敏銳的觀察力和細膩的寫作技巧,卻總覺得其中滲出一股知性的冷冽,詩人與其題材似乎未能融合成一體;在《讚美》一書,這樣的問題不復存在。他說《讚美》或許是一九七O年代最震撼人心的詩集,此書奠定了哈斯在美國詩壇的地位。
在〈拉古尼塔斯沉思〉一詩,哈斯以「一個詞於是成了其所指之物的輓歌」的思維邏輯,道出逝去之物的無可取代性,永恆不存在的失落感,美好回憶與渴望之彌足珍貴。在〈替花命名的小孩〉一詩,哈斯熬過了童年的恐懼,得以倖存者的目光回望過去,自大自然汲取安定的力量:「在成年歲月裡的/這個晴朗早晨,我定睛/注視喬琪亞.歐姬芙畫作裡/一顆純淨的桃子。/它如是圓熟地靜置於/光中。紅眼雀在我敞開的門外/樹葉間刮擦作響。」在〈致一讀者〉中,他為如何解憂卸苦給出建議:「想像一月與海灘,/泛白的天空,海鷗。而/面向大海:不存在的東西/居然在,不是嗎……」的確,「危險無所不在」(〈九月初〉),憂傷、疑懼如影隨形,然而美好事物也無所不在,垂手可得,如何用心觀看,讓兩者抗衡、相剋相生,是生命的課題。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