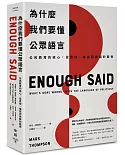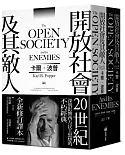推薦序
《民主在退潮》大量引證新興民主國家的案例,反映了我們所生活的時代,也讓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的未來。在反映時代與反思未來的結合中,所有的讀者都會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碰觸如下問題:為什麼民主體制是非西方國家政治發展的「必要之痛」?
問題的意義在於這個假設:只有在全面民主化的政治社會中,每一個人渴望自由的期待才能夠獲得實現的機會。可是,這個假設讓我們繼續問,什麼叫做全面的民主化社會?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許多人認為,只要固定地舉行全民普選,就是全面民主化社會的具體表徵。這一個聽似簡化的答案,卻無可否認地成為所有支持民主發展人士的願望,甚至連推動全球民主化最熱心的美國都不例外。
本書的主要重點,就在於分析美國在全球推進民主化的過程中,引發的各種不符合民主運作的事實。在這個分析之中,有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民主化第四波」。作者認為,全球民主化已經歷經三波的發展。第一波指的是西歐與北美國家在十九世紀所發展的民主。第二波是二十世紀前半葉出現的君主立憲國家。第三波的特徵是推翻軍事專制,還政於民所引發的浪潮,其歷程從一九七四年的葡萄牙開始。一九九○年代,蘇聯瓦解,東歐國家紛紛脫離鐵幕,採取民主制度,為第四波的民主浪潮拉開了序幕。
四波民主發展的浪潮,讓加入民主制度的國家,如同雨後春筍一般,數量大幅度地上揚。不過,在發展的過程中,除了少數歐洲國家之外,大多數的新興民主國家都面對了民主發展倒退的問題。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泰國。作者在二○一一年開始本書的寫作,所以可想而知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就是曼谷在二○一○年春天所發生的紅衫軍與黃衫軍的對抗。
紅衫軍代表的是大多數的農民,也是經濟情況比較貧窮的大眾。紅衫軍支持非常具有領袖魅力又懂得選舉的塔信政府。塔信在受到農民支持下,不斷贏得選舉的勝利,痛宰二○○五年黃衫軍所支持的民主黨。接下來的幾次選舉中,民主黨根本不敢參選,讓塔信能夠完全執政,自詡代表平民大眾。不過,這可惱火了以中產階級自居的黃衫軍,尤其是住在曼谷,生活比較富裕的上層社會。他們走上街頭,懇求國王,諂媚軍方,訴願能夠透過非民主手段終結民主選出來的政府。
事實上,作者在敘述民主倒退的例子的時候,引用大量的事實,像分析新聞一樣,巨細靡遺地闡述許多國家如何一度熱情擁抱民主,卻又在不久後,無情地推開民主,甚至樂於回到專制政府。不只是泰國,連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緬甸等東南亞國家,經常因為實施民主制度以後,新政府未能有效改善生活,產生各式怨言之外,還讓中產階級感覺生活水準的下降。於是,資金的外流,人才的出走,讓原先已經很不穩定的政治局勢,雪上加霜。加上選舉獲勝的新政權,執政結果,不但未如預期,還破壞了原先在專制政府下所維持的穩定。在這類國家中,民主的倒退,往往是事實,甚至於很荒謬地變成了許多人的期待。
最荒謬的發展,莫過於晚近從二○一一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在作者的眼中,這一場從突尼西亞開始的茉莉花革命,席捲北非與中東,依然屬於打倒專制政府的第四波民主化。在作者截稿的時候,他看到的是阿拉伯之春風起雲湧地擴散至埃及、利比亞、巴林以及敘利亞等國。當時作者已經注意到這一場發生在伊斯蘭世界的民主革命好像與其他第四波國家有一點不同,所以在本書付梓之際,作者增加了一段有關埃及民主的敘述。他指出當時埃及民選總統,也是出身於穆斯林兄弟會的莫西,膽敢解除陸軍司令坦塔維元帥的職務。當時軍方接受了莫西的決定,不過顯然作者並未能預見後續的發展。
二○一三年,埃及的政治出現混亂,大規模的示威運動,讓軍人重新專政,罷黜莫西的總統職務,同時宣布其所屬的穆斯林兄弟會為非法組織。二○一五年,法院以支持二○一一年監獄暴動的理由,判埃及首任民選總統莫西死刑!此舉讓我們不得不反思,如果真像日裔美國學者福山所言,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的終點,那麼這句話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我不停地思索,感覺這是作者最想問,但又不願意提出來的問題。
本書的成功之處,就是大量閱讀與新興民主國家相關的資料後,健全民主的條件會在腦海中逐漸浮現。我認為,民主本身並不是一項終極價值,卻是一個實現終極價值的手段。作者很清楚地表明,定期舉辦選舉就是民主制度的想法,不但是錯誤的,還會忽略非常多不民主文化在投票行為過程中所展現的不自由現象。買票固然是一個例子,但是在許多新興民主國家中,獲選人當仁不讓地對於政治利益的剝削,更是令人不敢恭維。
因此,作者仿效名言,提出「笨蛋,問題出在經濟」之語。他指出,民主制度做為保障全民幸福的手段,應當反思於三項目標:經濟繁榮、終結貪污與社會和諧。首先,民主制度的核心目標,就是保障中產階級的富裕。中產階級是任何社會中有才能與錢財的人,而他們的穩定,就是所有其他人獲得經濟繁榮的基礎。中產階級推動經濟發展,必然也能夠帶動社會的發達與穩定。誠如作者所言,民主政治的成功關鍵是經濟的發展,而成功的經濟發展也是推進民主制度的首要目標。
其次,所有在第四波中的新興民主國家,都希望能夠在推翻舊有的政權後,帶來一個沒有特權,廉能有效的政府。民主化下的法治社會能夠達成這個目標的原因,是因為定期的投票制度讓想要恣意妄為的政治人物知道,一旦觸法,在失去政權後,必須面對法律制裁的下場。事實上,打擊貪腐,就是所有老百姓在新政府中,引頸盼領下的期待。然而,一個不能杜絕貪污的新政府,無論是不是民主政府,必然因為被人民唾棄,又進入被推翻的命運。
最後,我們需要民主制度的目的,並不是要一個人人各自獨立的個人主義社會。個人自由固然重要,但這不是一個民主社會所期待的價值。民主社會基於自由與平等的原則,都希望能夠透過這些普世原則,讓社會中的所有人、族群、社群,宗教團體能夠和諧共存。其中,我們需要養成相互信賴,服從多數,尊重少數,將心比心等價值,促進社會和諧。
在說明這三點反思之後,我也必須針對本書在出版後,民主化發展的議題做一點說明。本書在二○一二年出版之後,民主發展的過程有進有退。其中,緬甸在二○一五年底舉行有史以來的首度總統選舉,翁山蘇姬所代表的政黨大獲全勝,是緬甸民主化重要的里程碑。但同時在中東地區,民主化的潮流卻引發了至今令多國束手無策的一連串災難。宗教的衝突,並沒有因為民主選舉的結果而消彌。正好相反,各式各樣激進化的回教教派,各立山頭,持續戰鬥,甚至還出現了重建回教帝國,以哈里發政權作為號召的伊斯蘭國之建立。這些方興未艾的政治亂象,不但讓原先令人期待的阿拉伯之春毀於旦夕,民主的大倒退也成為中東地區的現象!
本書特別提到了中國模式與民主失靈之間的關係。這一點讓我們活在寶島台灣的每一份子,感覺到既驚嚇又期待。如果你認為民主制度的發展,就是人類文明的答案,那麼在中國模式逐漸顯著的過程中,你可能要失望了。有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光是空談民主並不足以滿足渴望幸福的人。但是,如果你相信民主是人類必然要走的道路,那麼如果中國的模式,能夠發展經濟繁榮,終結貪污濫權,以及促進社會和諧的話,那麼這個模式在許多感覺民主失靈的人心中,會不會是一個選項呢?
這當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因為牽涉到許多不成熟的條件,所以我不能越俎代庖替大家回答這個問題。不過,在閱讀本書中,我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這是一個作者暗示要解決的問題,是他在陳述各式民主失靈案例之後呼之欲出的問題,更是閱讀本書過程不得不反思的問題。我至為傾心於作者這種從講解事實到反思民主的寫作方式,並因此鄭重推薦本書予所有關心民主政治發展的人。
苑舉正(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譯者序
追求「正義型民主」
二○一五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如果以每個世代為二十五年計算,在這將近三個世代的時間裡,可以說是美式或西方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主導著地球大部分人口的生活與思想的時代。即使是在蘇聯解體前的冷戰年代,最多時有四億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它所控制的國家集團內,另有十億人口住在不屬於西方集團或蘇聯集團的中國境內。但是全世界五十億以上的人口當中,仍有近四分之三的地球公民,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獨裁國家的居民在內,無時無刻不直接間接受到西方民主生活方式的熏陶與影響。自由主義民主的力量隨著美國國力無遠弗屆的擴充,滲進世界的每個角落。
戰後的台灣,從初期各種民主力量不斷萌芽,反抗國民黨一黨獨大開始,民主日益紮根,並在二〇〇〇年以民進黨獲得執政權力為起點,正式踏上了全面民主的不歸路。雖然一路走來,道路坎坷,但是以民選領導人和代議制民主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民主根基,已牢不可破,難以動搖。
在全球範圍內,伴隨著台灣開始進入全面民主發展時期而來的是,全球民主國家的擴散,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達到了高峰,東歐和不少非洲國家都紛紛加入了民主的行列。然而,到了二〇〇〇年中期以後,以選舉程序、多元主義、政治參與、政治文化、政府運作和公民自由等為標準來評分的全球民主指數,卻開始下降,帶動了全球民主的大退潮。正如今年九月十五日史丹福大學民主理論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評論民主在退潮的專欄文章中所說的:「在[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過去了三十年之後,民主曾以前所未有的步伐擴散到了全世界,但是到了二〇〇六左右,卻突然停頓了下來,雖然民主國家的總數沒有急劇減少,但是公民社會的空間卻不斷縮小。自由與民主都在退潮。」
這種退潮顯然與這段期間西方民主的錯誤運作與示範息息相關。一九九一年年底蘇聯的解體,將美國的國際地位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世界都寄望作為民主自由領頭羊的美國,能帶領受到四十年冷戰惡性消耗的世界,擺脫意識型態的泥沼,步向共同繁榮昌盛的全新局面。然而,從二〇〇一年起,美國以反恐名義發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給中亞和中東地區帶來的連鎖式破壞猶未平息,二〇一〇年起由美歐西方國家大力介入的「阿拉伯之春革命」,又再度將中東地區帶進了戰爭與死亡的地獄深淵,至今西方國家欲透過大規模群眾示威運動和武力介入,而強行將其帶進現代民主國家行列的利比亞、埃及、敘利亞和葉門等國,不是內戰不止,恐怖主義活動猖獗,就是軍人干政,難民四處流散。同樣是在美國力量的影響下,這些國家的處境,與今天台灣社會的安定以及周邊國際環境的相對平穩,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但是,稍微深入觀察,我們卻不難發現,有幸進入民主標兵行列的台灣,在社會表面祥和的背後,卻是處處充滿了不應有的不協調現象,隨手都可舉出這類的例子。譬如凸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弊病的貧富不均現象,在台灣同樣不可倖免,「台灣近年來的國家財富,正往極少數人集中,前一%所得者占全國總所得比例,已從六%竄升至十一%,有錢人不必靠上班薪水謀生,用錢滾錢就能迅速累積財富;市井小民市面對房價飆漲、荷包縮水,卻是難以翻身。」(引自:《遠見雜誌》,二○一五年三月號。)又如上世紀九〇年代以提出「歷史終結論」而名噪一時的美國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其去年底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提出的,實現現代民主良治社會的三大基石,即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在台灣似乎都不充分具備,也因此導致了選舉至上、政黨政治失序、司法和教育隨政治風向而轉、民粹主義泛起、貪腐詐騙橫行、道德水準掉落、少數綁架多數以及名嘴治國等社會亂象。這些現象造成了作為社會主流動力與價值塑造者的中產階級的退縮與沉默,社會失去了行動準繩與領導力,也失去了四小龍時代全民在國際上共同衝刺的視野、雄心與能力。
二〇〇八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使西方民主制度受到了進一步打擊。全世界人民目睹了新科技時代華爾街是如何以各種新穎的金融手段躲避政府監控,將財富迅速集中到到少數人手中,但同時在遭遇没頂之災後,卻仍舊能夠安然無恙地繼續大行其道,由美國政府以所謂的量化寬鬆大印美元,助其脫困,但由受到拖累的全世界人民為其買單。至今,美國本身因為掌握了美元發行權,雖未能完全擺脫其經濟困境,但是歐元區在美元的強勢打壓下,昔日的強勢已一去不復返,大部分國家的經濟乏善可陳;日元雖不斷貶值,但日本經濟上叱吒風雲的日子也已成陳年往事,目前除了在政治上更全力靠攏美國外,實已無法在提振經濟方面有更大的作為。在美日均自顧不暇的背景下,在政治上緊密跟隨美國和日本的台灣,也自然無法在經濟上找到出路。
但更大的傷害是,在全世界許多國家人民的心目中,過去認為只要走上美國的民主道路就可帶來美國的富裕繁榮的信念,開始產生動搖。建立在美元霸權上的私有制資本主義,並不能保證給全世界人民帶來真正的福祉。更有甚者,從小布希總統開始,美國在出兵攻打阿富汗、伊拉克方面的決策草率,及其在推翻伊朗和敘利亞政權上的決策失誤與反覆,在在都顯示了其在後蘇聯時代國際秩序的治理上獨斷獨行的非民主本質和能力極限。各國人民對美國民主制度與管理世界能力的信心動搖,無疑給經濟上趁勢而起的中國,提供了吸引全球注意力的巨大空間。
本質上,正如本書所說的,中國現行發展方式之所以受到一些國家的青睞,主要體現在它看來優於西方模式的以下特點上:
一、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過去三十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速度平均高達一○%,直到二〇一〇年後才因全球經濟放緩和經濟結構調整而有所下降,今年雖可能達不到七%的年均增長目標,但仍將是排名全球前列的國家。
二、高效建設的速度和執行力度:不論是從基礎設施到高速交通網路的建設,或是從大型國際運動比賽到大閱兵的完美運作,都表現了高度貫徹與快速執行的能力。
三、中國大陸對經濟上有需求的國家提供了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慷慨經濟援助和技術援助。相對的,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提供援助時往往要求當事國政府進行政治改革或取消人權壓迫,或提出其他附帶政治條件,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樂意接受這類苛刻條件。
四、這些國家,不論大小貧富,與中國交往時,能感受到平起平坐的待遇,但與西方國家,尤其是與美國交往,卻不一定能得到應有的尊重。
在此同時,隨著中國大陸的日益對外開放和出國旅行人數的迅猛增加(每年超過一億人),過去作為專制社會所給予外界的封閉式非民主國家的刻板印象已快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正由世界最大中產階級消費人群帶動的初級富裕社會(或稱小康社會)所呈現出來的更開放面貌,從而淡化與模糊了其不完全民主的一面。
此外,在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為表、國家資本主義為實的經濟體系下,私有企業的不斷壯大與向海外進軍,甚至蠶食鯨吞西方與美國的大小企業,也必然會縮小從管理理念到企業文化方面中國與西方私有制資本主義之間的差異。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加速,西方社會眼中中國模式的負面因素還會進一步減少。
因此,不足為奇的是,中國模式對西方民主制度構成的挑戰,已不僅僅是學術層面的爭議而已,實際上已填補了後冷戰時期蘇聯遺留下來的意識型態真空,以改良式專制主義的形式對自由主義民主構成挑戰。一方面由於中共治理能力的不斷加強和國際影響力的持續擴大,另一方面由於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千瘡百孔,永無寧日,不斷完善中的中國模式,削弱美式和西方民主的能力自然只增不減,不會停頓下來。
然而,在這種競爭當中,我們看到的並不單純是有選舉與沒有選舉的形式之爭而已,其範疇實際上已從加拿大學者貝淡寧(Daniel A. Bell)所說的「菁英統治」(Political
Meritocracy,或稱賢能政治)模式與「民主制度」之爭上升到哪一種模式或制度更能夠解決對全世界人民更為迫切的根本問題的能力上。這種競爭與冷戰時代意識型態高高掛帥的競爭有本質的不同。當前各國更需要解決的問題層出不窮:富國與窮國的貧富差距、經濟成長緩慢、金融危機循環發生、氣候變遷、環境破壞、宗教爭端、恐怖主義、局部戰爭…,不一而足。美國作為後冷戰時期的世界頭號強國,始終自認可以擺脫聯合國的羈絆,帶頭解決這一切問題。但是,中國作為後來者,正逐步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對美國的領導地位構成了無形的挑戰。具體來說,如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體系和國際貨幣基金會體系與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戰略下的亞洲投資銀行體系的競爭,或是人民幣國際化後與美元地位的競爭,演變下去,最後會促成與窮國息息相關的世界金融格局的根本性改變。這才是今後中國模式與美國民主制度競爭的實質,而不是在於何種形式的政治體制更為優越。
但是,從眼前來說,這兩種體系都存在著各自無法解決的內在嚴重缺陷,即本國人民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按西方的統計,到二〇一六年,世界一%的人口所佔有的財富將超過其餘九九%的人口,在美國國內,根據其人口普查局的統計,二○一三年十一月,其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達到了歷年最高的十六%以上;二○一一年每日生活費用不到二美元的住家數達到了一百五十萬戶,其中包括萬名兒童在內。在中國大陸,二〇一四年北京大學發表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發現,中國大陸三成以上的財富被頂端的一%家庭所佔有,而底端的二五%家庭僅有社會一成的財富。另據《二〇一五年中國家庭發展報告》,前二○%的家庭和後二○%家庭財富收入相差達十九倍。
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社會的健康發展,造成了社會不公不義的永久化。從羅馬教皇方濟各氏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都對此發出抨擊。尤其是方濟各式的抨擊更是毫不容情。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少數人的財富以幾何級數增長,使多數人得不到那少數人所享有的繁榮。是維護股市與金錢投機絕對自主性的意識型態造就了這種失衡狀態。」「為了維護排斥他人的生活方式,或為了維持對自私的交易的熱誠,無動於衷的冷漠已蔓延到全世界。最後,幾乎不知不覺地,我們已感受不到窮人的呼喊,不會為他人的痛苦哭泣。」這種情況不只普遍存在於美國社會,新富的中國大陸也無處不在。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並不只是文人的想像。
擴而大之,從非洲到亞洲到拉丁美洲,那些與高樓大廈連在的貧民區,更是令人怵目驚心。在肯亞首都內羅畢市區內非洲最大的貧民窟奇貝拉(Kibera),一百萬人口擠在五平方公里的小山坡地上,旁邊緊鄰著中國援建的柏油公路,居民住的是鐵皮或木頭搭建的矮小破房子,一間連一間,沒有洗手間,沒有自來水,裡面又黑又暗,頭都直不起來。教會或私人捐助的「學校」,其實只是小小的房間,或有如美國超市旁邊收舊衣服的救世軍儲藏間,裡面擠著不同年齡層衣衫襤的小孩,操場就在旁邊污水橫流的小小空地,或是堆滿了污濁垃圾的垃圾場上。學校供應的「伙食」,不過是幾片破菜葉煮出來的菜湯而已。不身歷其境,不論是美國人或是中國人,都很難想像欠發達國家的貧民,是這樣過日子的。
因此,從追求正義公平的角度,這個世界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形式上你死我活的模式或制度之爭,真正要爭的是哪一種模式或制度能夠更好地解決不管是國內或國際上的巨大貧富鴻溝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的翻譯出版,並不只是為了幫助讀者瞭解世界民主的發展現狀而已,更是要提示我們自己,作為民主社會中的一員,現在應當是開始思考如何超越本書中所揭露的美式自由主義民主的困境或弊病的時候了,我們每一個人應當攜手共同推動台灣向更高意境的正義型民主社會前進,不能一直停留在民粹性的政治纏鬥中,原地踏步,停滯不前!
湯錦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