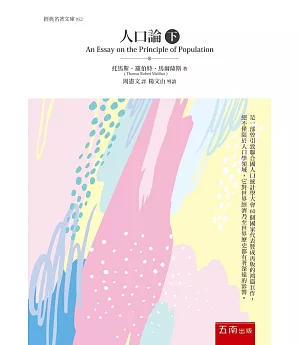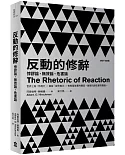譯序
一
由於社會人士的鼓勵與本行當局的支持,本叢書已開始作第三次的推進。這一次,最初決定譯書七種。這七種是:(1)Malthus 的《人口論》,(2)Say 的《經濟學泛論》,(3)List的《國民經濟學體系》,(4)Mises 的《貨幣與信用原理》,(5)Klein 的《凱恩斯革命》,(6)Kalecki 的《經濟變動的理論》及(7)Schumpeter
的《經濟分析史》。後又增加三種,即(8)Menger 的《國民經濟學綱要》,(9)Gide 的《經濟學原理》及(10) Dorfman 的《線型計劃與經濟分析》。
在這裡,我似有一述個人對於本叢書所持態度的必要。當本叢書計劃進行的時候,我曾就商於一位朋友;他表示這工作十分要緊,但其最後的結論,是帶點告誡口吻的接連三個「需要慎重」。我答覆他:這工作需要慎重,那是不成問題的,但不能因為需要慎重而就不做。所謂「需要慎重」,說痛快些,就是難得適當的譯者,翻譯怕有錯誤。關於此點,我明白表示與他的見解不同。我認為:一本理論著作的翻譯,錯誤是在所不免的。試看現代的所謂「先進國家」,它們對於外國的名著,都不止有一種的譯本,而且每種譯本都經過多次的訂正(甚而至於每版都有訂正);這就是翻譯有錯的公開告白。它們未曾「怕有錯誤」而停住不做。我們出版本叢書,只想做點開路的工作。西諺:「路是人走出來的」;我們不能只見眼前的「康莊大道」,而忘前人的「篳路藍縷」;天下事那有都可「一蹴即幾」的。我們只能就此時此地,盡其在我;我們不能坐待「聖人出現」;這是超現實的。
而且,今天已是二十世紀的後半期,說我們還沒有夠譯這類書籍的人,即使是事實,我也得問:要到什麼時代才會有?其實,我已說過,一本理論書籍的翻譯,要說絕對正確,這是不可能的(雖然有人在我面前說過:他的翻譯是絕對正確的);即使是最簡單的日常用語 good by,我們譯「再見」;嚴格說來,這是誤譯(按:good by 為 God be with you
的略稱,不論所謂直譯或意譯,都沒有「再見」的意思)。至於相對的正確,凡有相當修養的譯者,都是可以辦到的;但得有一條件,那就是充分的時間。誰都知道:同樣一本書,同一人用一年時間譯的與用五年時間譯的,它的正確性決非一與五之比。當然,這所謂時間,也絕不是孤立的;假使一個人終日為生活所苦,他縱有充分的時間,也是不會有理想的結果的。
總而言之,我們做的只是已經落後幾十年的開路工作,我們不存盡善盡美的幻想,我們希望「繼起有人而後來居上」;一本名著,有幾種譯本,那是應該的。
二
我想:世界上知道者最眾、共鳴者最多而反對者最烈的著作,恐無過於 Malthus的《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了。但是,從頭到尾讀過《人口論》的,可能不會太多。不過,至少,凡有現代社會科學常識的人,不僅無不知道這本書,而且無不知道這本書的根本原理,即所謂
Malthusism。至於不知道這本書,而與這本書的根本原理發生共鳴的,那是充滿了世界的任何角落與任何階層。今天那些感覺孩子太多、生活困難而需要節育的,都是所謂新 Malthusism 者(Malthusism 與新 Malthusism 的區別,詳見下文)。但在反對方面,早在十八世紀,就有人對本書絕詞痛罵,說這只是一些淺薄的材料;如果要說著作,那是一本最無聊的著作。
那末,這本書到底講些什麼呢?它的結論十分簡單(任何有價值的著作,都是論證複雜而結論簡單的)。即著者由「食色性也」兩大法則出發,根據各種論證,斷言人口的增加一定超過食物的增加。照著者的說法,人口如無限制,是按幾何級數的比率(即一、二、四、八、一六的比率)增加,
而食物的增加,則僅按算術級數的比率(即一、二、三、四、五的比率)。故『在兩世紀之後,人口與生活資料的比數為二五六對九;三世紀之後,則為四○九六對一三;二千年之後,這一差額,幾乎無法計算』。但因人類沒有食物絕對無法生存,所以這種優勢的人口增加力,一定以某種障礙的形式,而被抑制於食物增加率的水準。此所謂某種「障礙」,著者最初說是罪惡與窮困,主要是指戰爭與疾病(見初版《人口論》);後來加上了「道德的抑制」(moral
restraint),主要是指延緩結婚。著者並就各種「障礙」的性質,而分為「積極的障礙」與「預防的障礙」;前者主要為罪惡與窮困,後者主要為延緩結婚。這就是《人口論》的精華,也就是通稱之Malthusism。後人再加上了「節制生育」(著者當時還不知道生育是可人為節制的),這就是新 Malthusism。
首先,必須指正一點誤解。有人曾以後來的事實,證明人口的增加未必是按幾何級數的,食物的增加也未必是按算術級數的,因謂著者的理論為不可信。這是誤解。蓋著者之所謂幾何級數與算術級數,實在都是為了說明的方便,至多是就著者當時所得的統計數字而言;它的真正含義,只是說:如無其他障礙,則人口的增加快過食物的增加。
三
只就上文所述,原無什麼問題(嚴格說來,我認為是有問題的;問題就在「如無其他障礙」這一前提;此且不論)。但是,後人拿著者的 the checks to
populatoin(對於人口的障礙),理解而成人口限制;情形就完全兩樣。說詳細些,著者的出發點,原只客觀地說:食物不足是人口增加的障礙;而後人則主觀地說:因為食物不足,故須限制人口。儘管前者自然也認有限制人口的必要,但與後者的含義顯不相同。而事實證明:即使著者主張限制人口,他的動機,也毋寧是較多消極的成分;即其主要目的,是在反對當時那些獎勵生育的議論。尤其是到了新
Malthusism 時代,主張以人為方法節制生育,以求符合食物的產量;因為這樣一來,必然會發生下列諸問題。
第一:就時間來說,需要限制人口的,比較之下,將是地廣人稀的太古時代(有人說是亞當、夏娃時代)而非人口眾多而土地俱已相當開發的現代;因在太古時代,雖然到處都是荒原,但因當時生產智識與生產技術的落後,這無補於食物的生產。但是,多少年來,人口大量地增加,人類的生活反而大為改善。
第二:就空間來說,今天如需限制人口,則比較之下,這不是五穀不分的都市士紳而反是胼手胝足的鄉村農民。假定某國國內發生糧荒而國外糧食又無法接濟,試想首先挨餓的到底是哪些人?如果國外糧食雖可接濟而仍有部分人民必須挨餓,則尤其如此。
第三:Malthus 之所謂人口與食物問題,原就全世界而言,而在世界被分為許多國家的時代,自然也可應用於各國;但總不能應用於國內的某一地區(不論省區或市區)。如以國內地區而論,則都市人口麋集而不產粒米,這卻未聞成為需要限制人口(指節制生育)的理由。
第四:人們直接吃的固然是食物,但在今天這一貨幣經濟與交通經濟時代,就一國家來說,毋寧說人們吃的是一國的購買力或生產力;除非像在戰時,對外交通斷絕(這已在問題的範圍以外),平時只要有充分的購買力或生產力,就不愁沒有充分的食物(如果世界食物不足,挨餓的是購買力不足的人)。假定現有某一國家,其全部農地完全變為工廠廠基,國內不產粒米;此時,這一國家的農業與農民儘管是沒有了,但其人口的養活能力,顯然只有大量增加,決不因而絕滅。
國家如此,個人尤然。今天每個人所注意的,乃是本身購買力的有無與多少而非市上糧食的有無與多少,至少絕非本國糧食生產的有無與多少。假使你執某人而對之曰:現在國家產米不多,請你少生一個孩子,請問他會有怎樣的感想?同樣的道理,東南亞那些經濟落後地區,雖其產米極為豐富,但不成為可以大量增加人口的理由。
第五:「窮人多產」,這似有生物學的根據,所以由於社會的進步與生活的改善,人口增殖力自有減少的趨向;而同時文化的發展與環境的轉換,也使人類自動地(不是由於糧食的壓迫)改變其「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所以結婚勢必延遲,人口的出生率勢必減低。目前世界人口的急速增加,毋寧是由於醫藥的進步與衛生的改善,使人類的生存率大為提高(特別是嬰兒),使人類的壽命大為延長。其次,著者認為對於人口增加的另一障礙,即由於戰爭的死亡,也因文明的進步而日益減少(儘管武器的殺傷力日益兇猛),而且,瞻望前途,和平而無戰爭的世界,當非幻想(至少,我們應以此為努力的目標)。
第六:過去,我不研究人口問題;今後,我也不打算研究人口問題。現在,我譯《人口論》,這只由於偶然的原因(詳見下文);因此,我不怕說「外行話」,貽笑方家。Malthus
說「人口的增殖快過糧食的增殖」(且不說前者是幾何級數的,後者是算術級數的)。但是,在我想來,不論動植物,它的增殖,總該是低級的快過高級的。以人口與糧食對比,這應是糧食的增殖快過人口的增殖,而非人口快過糧食。而且,自有生民以來,幾千萬年,人的生長,「十月懷胎」,雖有現代的科學,也未能使其生長的時間縮短,今後也無此可能;至於糧食的生長,則現代科學不僅已使其生長的時間縮短,而且已使其「單位面積的產量」大為增加,今後還有此可能。我絕不否認:古代(與現代對稱)糧食有欠充足,妨礙一般人民的生存,但這原因是另有所在。(只有一點,那就是說:人口與糧食都生長在地面上,而地面有限,人口愈增加,所占的地面愈多,勢必至糧食生長所需的地面愈少,終使「糧食」日益落在「人口」之後。但是,即使有此可能,這也不是過去與現在的事情;它的實現(假使實現)也將在遙遠的未來;所以,這與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毫不相干。)
第七:那麼,它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這不是這篇「譯序」所當討論的。不過,《人口論》裡有節文字,似與這一原因有關,不妨引述。Malthus說:『據Park的報導,在非洲還有許多肥沃的耕地;所以也許有人以為:饑饉的原因是在人口的缺乏。但是,如其果然,則如此大量的人口,每年向外國輸出(按:指當時非洲的大量人口向外輸出為奴隸而言),這理由是無法想像的。黑人真正缺乏的,確是財產的安全與勤勉(勤勉一般是跟著財產的安全而來的);如果少此兩者,則人口的增加,只有使窮困深刻化。如果為了填滿似乎人煙稀薄的地方,而給以巨額的生育獎勵金,則其結果,恐怕只是戰亂的頻發、奴隸輸出的增加及貧困的加重;真正的人口增加是幾乎或完全難以希望的』。這確是當年的實在情形;但問題是在:Malthus
肯定了非洲缺乏「財產的安全」而反對增加人口;這猶肯定了掠奪的存在,而謂「漫藏誨盜」,反對積蓄。因像當時的情形,一方面既有大量的沃土未能耕種,而同時則又有不少的人民不能生活,這顯然不是什麼人口增殖快過糧食增加的問題,更不能由此而得出需要限制人口的結論。這一定是有些什麼阻礙了「人未能盡其力、地未能盡其利」;而 Malthus
之所謂「缺乏財產的安全」,只其一端而已。但即就此一端而言,我們應有的主張與措施,也毋寧是力求「財產的安全」,而使人口得以增殖、土地得以耕種、糧食得以增產。此後非洲的發展,也確實是走這一條路。
據上所述,似乎我是反對節制生育的,其實不然;至少到了今天,我是傾向於節制生育的。而且,不論科學如何發達,縱使人類已可依賴化學糧食而生活(這是大有可能的),根本已無 Malthus
之所謂「糧食不足」,我也不甚了解儘量促使人口增加,除非還有廣大的國土急需人力開發,這到底有何必要(這在過去是有必要的)。我既不只因本國糧食不足而主張節制人口,更不只因本國糧食充足而主張獎勵人口。固然,人不能沒有飯吃;但是,人不能只要有飯吃。此人之所以為人,此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
總而言之,我的意思,人口問題,這與其由一國的糧食生產量來衡量,毋寧應以一國的生產力為標準;這與其由個人的經濟出發,毋寧應就國民的健康著想(如果節制生育完全由個人的經濟出發,這將成為窮人特有的義務)。因此,這就變成了國民優生的問題。換句話說,今後人口問題的真正焦點,與其說在「量的節育」,毋寧說在「質的優生」。「質的優生」如能達到,「量的節育」聯帶完成。不過,國民優生的實現,亦得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絕不像過去那些優生學者所幻想的這樣容易推行。因為:一方面,優生的本質,原是科學的結晶;而同時,優生的實行,則須有民主的前提。沒有科學,根本無從知道優劣;沒有民主,就是知道了優劣,也無從實行。現在舉個近似(只是近似)的例子。在(以家為主)之迷信的、宗法的社會,「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只是為了「上墳祭掃」,也得有個「不肖兒孫」,誰又願意為了國民的優生而絕後。我所以說這只是一個「近似的例子」,乃有種種理由,此處不擬申述,其中之一,就是目前生育的作用,除了「傳後」以外,還有「防老」的意義;故在防老的問題未得解決以前,優生仍是不易澈底推行的。然則如何可以解決防老的問題呢?這自有待於民生主義的澈底實現;務必達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地步而後可。(說通俗些,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是不可分割的,而且都須以科學為基礎。)
四
接著,得介紹一下著者的經歷與本書的背景。
著者 Thomas Robert Malthus,一七六六年二月十四日生於倫敦附近 Surrey 地方的 Rookery 山莊;父名 Daniel Malthus,是一富有教養的紳士。著者幼年,按照英國上流社會的習慣,受教於家庭教師;一七八四年入劍橋大學,習哲學與神學;一七八八年,以優等成績卒業。此後幾年間,在其父親身邊,繼續研究。一七九七年,充任英國教會的牧師,主持
Surrey 地方的一小教區。本年,其最初著作《危機》(Crisis)成,因反對當時英國總理 Pitt 的政策,為其父親所扼而未印行。翌年,即一七九八年,初版《人口論》問世;時,著者三十二歲。從一七九九年至一八○二年,遊歷歐洲大陸。一八○三年,二版《人口論》問世,分量比較初版約增四倍。一八○五年與 Harriet 結婚;同年,受聘於東印度學校。該校設在倫敦附近的 Haileybury
地方,是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養成所。此後三十年間,連續擔任歷史與經濟學的課程。他於教課之餘,經常從事《人口論》的訂正與增補;此外,並於一八一四年著《穀物關稅論》,一八一五年著《地租論》,一八一七年著《救貧法論》,一八二○年著《經濟學原理》,一八二七年著《經濟學諸定義》;在經濟學上,貢獻甚大。一八二一年,他與 Ricardo 及 J. Mill
等組織經濟學會,又於一八三四年發起統計學會;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六十八;遺體葬在 Bath Abbey。
著者成長的時代,正是英國產業革命的時代。各種機械,相繼發明;利用這些機械的工場工業,逐漸取代了老式的手工業;勞資的對立,愈益顯著。被工場工業所驅逐的小手工業者與因農業資本主義化而失去土地的農民們,陸續加入了工資勞動者的陣營。同時,當時歐洲戰亂相尋。而且,英國又常為饑荒所苦;英國人民,生活艱窘。食物的價格,一再上升;但是一般的工資,反因人浮於事而趨下降。為了救濟窮苦的工人,政府雖曾推行救貧法(Poor
Laws),但未有何效果。當時英國,充滿了失業、貧窮、疾病與所謂穀物騷動。在這樣不安的社會,而『富國強兵首須增加人口』的重商主義思想猶有強大的力量;不但是英國,幾乎任何國家,無不為了充實軍備與充實工場而獎勵人口。著者的《人口論》,可說就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產生的。雖然是有這種社會背景,但使著者執筆寫《人口論》的直接動機,還是 Godwin 與 Condorcet
的無政府主義。這情形,在本書第二版的序文上有所記載。而 Godwin 與 Condorcet 的思想,結局也不外乎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Godwin 在一七九三年發表《政治的正義與倫理對於幸福的影響之研究》,又在一七九七年發表《研究錄》,在當時的思想界,引起了非常的反響。他在這些著作上強調人類及社會的完整性,而力謂:完全自由平等的社會是可實現的。他受 Locke 與 Hume
經驗論的影響,認為人類的理念,不外乎外界印象的產物。他以此為前提,認為:社會的環境與制度,如加改革,則一切罪惡與貧窮都可消除;人類社會可以達到完整的狀態。他主張:理性的力量是萬能的,這種改革必須訴諸理性,而且可以訴諸理性。又照 Godwin
的說法,可以規律人類行動的,只有正義。所謂正義,這是為社會全體的幸福而努力。正義的觀念,必然要求財產的平等。有人生而擁有巨富,有人努力工作而仍不免於饑餓,這是正義的觀念所不許的。因此,人類如果根據正義而行動,就無貧富的不均;各人每天做一半時間的工作,就可自由生活。社會到了這種地步,各人的肉體乃為其精神所支配,可以繼續永久的生存。
Condorcet 在一七九四年出版《人類精神的發達》,提倡人壽無限說,謂因理性的發達與科學的進步,人類的物質幸福跟著增加,終可長生不老。
要之,Gdwin 與 Condorcet 都是極樂天地描繪理想的社會。這是「黑暗時希望光明」。當時的社會,正如前述,極其暗澹。而且,這一時代,是近世科學勃興的時代。因此,他們空想:由於科學的發達,可以少量的勞動生產大量的生活資料,而出現地上的樂園。所以,這種樂觀說,得到不少的共鳴者;這不是無理的。
著者在初版《人口論》的序文上,曾謂:『這一論文,原是對於 Godwin 先生論文的主題、即就他在《研究錄》中所說貪慾與浪費,我與一朋友的談話﹄。這所謂「一朋友」,就是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接受 Godwin 的思想,他則反對;兩者的爭論,成了他寫《人口論》的動機。因此,初版的議論,自然對於 Godwin
等,大事攻擊。一八○三年出版的二版《人口論》,不論內容與外形,都面目一新。初版是匿名的,二版始行署名;字數也增加五倍。《人口論》在著者生前,共出六版;每次都有訂正,但以初版與二版相差最大。本譯書是根據第六版翻譯的。
本譯書所附有關著者的八張照片,是我在多種日文書籍上找到的;孫震兄曾為此事,在美國花去不少時間;他寄來著者的遺像,因我已有,沒有用上;特此道謝,並示歉意。
五
我在拙譯 J. S.
Mill《經濟學原理》的譯序上,曾謂:『這幾年來,我竟不自量力,從事這一工作(按:指翻譯工作),我有時感到很大的樂趣,但也有時感到無限的煩惱。……今後我不打算再做這種工作;我一手造成的「臺灣文獻叢刊」,歷盡艱苦,已可初步結束,我有意於利用這些文獻,寫些有關臺灣社會史方面的東西。我想以此書告別譯壇』。從本年開始,我確實朝此方面進行;我集中有關資料,每天在做摘記,費時近三閱月,還未整理出一個眉目,而霹靂一聲,家人病發,且係惡疾。我因心緒惡劣,這一工作就停止下來;但是,為了鎮定神經,排遣苦惱,不得不找點事做;因在書架上找了一本已經破爛的舊書,是一九二七年出版神永文三譯的
Malthus《人口論》(第六版)。我原沒有譯完的計劃,更沒有出版的打算。
在譯完兩篇(已逾一半)的時候,黃晉福兄始由東京寄我一九四一年第二版寺尾琢磨的譯本。比照之下,後者高明多了,因就改據寺尾本翻譯。(《人口論》在日本翻譯的情形,我不甚清楚;但據所知,六版《人口論》的譯本,計有(1)寺尾琢磨與伊藤秀一的合譯本、(2)神永文三譯本、(3)鈴木政孝譯本、(4)佐久間原譯本、(5)松本信夫譯本、(6)寺尾琢磨的改譯本、(7)吉田秀夫譯本及(8)大島清、兵頭次郎的合譯本。初版《人口論》,則有(1)谷口吉彥譯本、(2)高野岩三、大內兵衛的合譯本、(3)大內兵衛的改譯本及(4)吉田秀夫、佐藤昇的合譯本)。因為這一寺尾本不僅是譯者與伊藤共譯本的完全改譯,而且譯者在改譯的時候,除參考神永與松本兩譯本外,還參考了
Valen-tine Dorn 的德譯本與 Pierreet Guillaume Prévost 的法譯本。(但我發現:也有寺尾本不如神永本正確的地方,足見翻譯之難)。舉例來說:第三章原題「Of the Checks to Populaton in the Lowest Stage of Human
Society」,神永本譯『論在人類社會最低階段的人口限制』,而寺尾本則譯『論在人類社會最低階段對於人口的障礙』,雖然文字此較冗長,意義正確多了。
同樣正確的翻譯,由於各人的譯筆不同,措詞造句,必然兩樣(我有這樣的感覺,即使是同一人的翻譯,昨天譯的與今天譯的,也不會完全一樣的)。所以,我在譯完本書以後,乃將前兩篇(根據神永本的),澈底改譯一遍,所費時間,多於重譯(我的文稿,從不起草,此番卻煩陳招治、李彩雲、郭孝翼諸同事代為謄正)。後來,為了準備出版,始找一九六○年出版的英文本,對照改正一遍,並於認為必要的地方,註出原文;自然,我已精疲力竭,再無根據英文本從頭重譯的勇氣了(英文本只有第二版序文,故本譯書第五版序文、第六版緒言、附錄一及附錄二,都是根據寺尾本的。這兩附錄,它的內容,全是
Malthus 與別人辯論或答覆別人的。因我沒有看到「別人」的文字,說實在的,有些地方,我沒有澈底了解;我的翻譯,只是「依樣葫蘆」而已。我為了「藏拙」,也為免「遺害」,曾經多次打算把它略去;而結果終於譯出,而且刊出;因我認為:這兩附錄,如不趁此時期譯出、刊出,可能將永無機會與國人見面;儘管譯文定多錯誤,但以此供讀者參考、請方家指正,這也是必要的)。
至於翻譯的體例,與拙譯 Smith《國富論》上冊及 Mill《經濟學原理》一樣,已詳見兩書的譯序,玆不復贅;但有一點,為了讀者的方便,轉錄如下。
『本譯書有些文句,附有原文。這(1)或因那些文句,過分歐化(換句話說,就純中文的眼光看來,有點蹩扭),附之,以便讀者的對照。試舉一簡短的例子。原文『……(河流)……always convey off a given
quantity』,我譯「常是運走一定量」;再讀一遍,不僅生硬,且似不適;因查日譯本,其中之一是譯「常是運走一定量的水」,這就十分明白了。不過,仔細想想,原文並無水字(加之固亦無妨),且 quantity
顯為名詞,加「水」就成形容詞;原譯生硬則有之,不通則未必;生硬是習慣的問題,我因維持原譯,而於其後附註原文。我的意思,我們既然閱讀西人的著作,就得多少培養一點對西人寫作習慣的了解。一本理論書籍的翻譯,定要使它完全漢化而又不失原意,這是不可能的。(2)或是為了遷就中文,而對原著語意,微有出入。(3)或因有些文旬,有黠難懂;我深怕拙譯未能達意(甚或誤譯),附之,以利高明的指正。總而言之,這些都是本譯書的缺點所在(我已意識到的)。我認為:缺點的自我暴露,這是進步的必要條件;我們要有認錯的精神,我們得提倡這種精神。有位朋友說:不過,你這樣做,容易給人以「斷章取義、吹毛求疵」的機會;我說:「斷章取義」,對我無害;「吹毛求疵」,於事有益』。
本譯書初稿的完成,全在家人病痛期內;翻譯之時,或在午夜,或在清晨,或神志清明,或精神恍惚;原稿紙上,淚痕斑斕;『思澄』、『念台』,情何以堪!天昏地暗,慘絕人寰。所以本譯書將是我用力最勤、用心最苦而結果最差的。
不知怎的,近來忽常記起兩句聯語(但記不起它的來歷):『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豈非上蒼示意:莫再災梨禍棗、浪擲辰光!
周憲文 於惜餘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