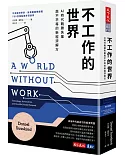導讀
重構民主與資本主義
文/張鐵志
主流價值相信,資本主義和民主這兩大當代政治經濟體制,一起創造了世界的自由與繁榮。這兩者甚至彼此支持,互為前提:沒有資本主義,不會有民主,反之亦然。
然而,事實上,資本主義和民主在本質上就是彼此矛盾,不斷爭鬥。因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不平等──這也是今年的暢銷名著,法國學者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再次重申的智慧,而民主的本質之一就是平等。
但顯然,在過去四十年,資本主義嚴重侵蝕了民主的意義與實踐。這是本書《當企業購併國家:從全球資本主義,反思民主、分配與公平正義》的主旨。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逐漸壯大的民主抑制了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因為當工人階級獲得普選權後可以透過選票和組織,迫使國家實行社會福利和各種工人保護制度;在美國的三○年代經濟大蕭條後,開始實行「新政」。到了戰後的西方,凱因斯主義取代了古典自由主義,強化了民主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以維持總體經濟需求與充分就業為目標,確保了二次戰後到一九七○年代的相對社會平等。甚至可以說,民主改變了資本主義的性質,讓資本主義可以被普遍接受。
一九七○年之後,新的經濟危機讓凱因斯主義無法回應而逐漸式微。進入一九八○年代,雷根和柴契爾夫人發動新自由主義革命,推動私有化和去管制化/鬆綁(deregulation)、打壓工人,讓經濟利益和貪婪成為新的時代精神,這是作者赫茲認為「企業悄然奪權」的開始。
進入九○年代,冷戰瓦解,共產主義失敗了,似乎自由資本主義取得最終歷史的勝利。民主黨的柯林頓、工黨的布萊爾,乃至德國的施若德,主張新中間路線或者第三條路,更承認自由市場的力量,解除市場管制(尤其是對華爾街的管制),削減社會福利。資本主義走向金融化,加上科技進展讓全球化極速擴張,企業可以更快速地移動,而且透過購併越來越巨大,因而對國家有更大的要脅力,要求更多減稅與特殊補貼,甚至足以決定遊戲規則。
另一方面,也是主要始自八○年代,國際經濟組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透過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外援與貸款,推動第三世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於是,國家漸漸被企業併購。
於是,自由市場、經濟成長、私人利益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膜拜教條。
二○一○年過世的歷史學家、公共知識分子東尼‧賈德(Tony Judt)說,「我們帶著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將二十世紀留在身後,大膽地跨入新世紀,在自說自話的、半真半假的事實面前止步:西方的勝利,歷史的終結,單極的美國時刻,不可避免地邁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場。」
而這對民主的意涵是什麼呢?
首先,民主是政治社群的成員平等地參與決定資源如何分配,但如今這個政治領域的決定越來越轉移到由市場來決定,由企業來定義公共領域。
知名的政治哲學家麥可桑德爾在《錢買不到的東西》一書中指出,「市場以及市場導向的思考延伸到傳統上由非市場基準所規範的領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大的一個發展。」而這有什麼不好? 桑德爾指出,商品化會造成:一、不平等,二、腐化。這的確也是民主的困境。
腐化原則用在政治上,就是民主從「一人一票」變成「一元一票」。當企業對於不論是政策或是選舉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民主就成為可出售的商品。這不僅本身是對民主價值的傷害,更會扭曲政治平等的原則。而政治的不平等又會進一步惡化經濟的不平等──因為掌權者不僅會設定規則讓金錢在政治影響力中更大,也會在經濟領域中制定有利於自己的政策。
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如此不斷惡性循環,彼此強化。
這對民主又會造成另一個惡果,亦即當民眾認知到政治只是服務於財團和既得利益者,媒體是被財團控制的,而民主無能改變他們的生活時,他們會有嚴重的政治無力感、政治冷漠,和越來越低的政治參與。赫茲在十多年前就提出深刻的觀察:「民眾投票率降低、失去對政府的信心,政治日益腐敗,在在使得民眾覺得政治完全不重要。選民和政府似乎都放棄了民主,覺得選舉不能真的改變什麼……」這是當代的「民主的危機」。
今年三月《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故事就是〈民主出了什麼問題?〉。
文章提到:「發達國家的黨員數量持續下降:現在僅僅一%的英國人參加政黨,而一九五○年的數字是二○%。選民數量也在下降,一項針對四十九個民主國家的研究顯示,選民數量自一九八○~八四年至二○○七~一三年間下降了十個百分點。二○一二年針對七個歐洲國家的調查顯示,逾半數選民根本不信任政府。同年Yougov公司針對英國選民的調查表明,六二%的受訪者認為政客永遠在撒謊。」
而當一般公民不介入政治,金錢就有更多空間介入和決定公共生活,於是造成另一個惡性循環。
民眾的政治冷漠也可能造成另一個惡果:孕育出民粹主義極右政黨。他們的修辭是對抗菁英的傲慢,在美國,他們結合起極端放任自由主義而成為茶黨,在歐洲他們結合起排外民族主義。
當代資本主義戰勝民主的另一種意義, 是許多國家為了推動市場資本主義而犧牲民主,這也是戰後美國常幹的事。一九七三年的智利是最主要的例子2,然後是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四小龍經驗,九十年代東歐解體後是震盪治療(shock
therapy),而現在,是「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尤其在二十一世紀,美國小布希政府的「民主輸出」反映了美國的偽善帝國主義,並讓美國式的民主吸引力下降,而中國的經濟成長,尤其是相對平穩地度過二○○八年金融危機,都讓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大增,甚至西方都出現許多中國統治世界的說法。
確實,發展才是硬道理。
二十多年前冷戰終結之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說歷史終結於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但現在, 似乎是資本主義打敗民主了。
真的是如此嗎?
在赫茲這本書的後半部,她描述了九○年代中期以後的各種反抗運動,從消費者運動到公民運動,他們如何抵抗市場與企業的黑暗面,如何重新奪回民主。特別是自一九九九年西雅圖的世貿會議,一個新的反全球化抗爭網絡,或者所謂的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逐漸形成。
赫茲的書出版十多年後,世界有了什麼樣的變化呢?
基本上,她為後來至今的時代描繪了正確的趨勢:世界越來越不平等(過去幾年有非常多書討論這個現象2),企業對政治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民主越來越陷入危機──不論是在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或是新興民主國家。反抗運動也越來越洶湧。
然而,她沒預示到的是,二○○八年的金融危機讓世人反省到不受限制的金融化資本主義的問題──那一年,卡爾‧馬克思成為暢銷作者,而今年,法國學者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也成為明星書;此外,IMF等推行的華盛頓共識早已破產,新自由主義也早已千瘡百孔。
更重要的是,新的反抗運動出現了,從美國的占領華爾街到阿拉伯之春到土耳其到巴西、西班牙到台灣的太陽花。這些抗議運動基本上是對這個為特殊利益所操控壟斷、無能解決人民問題的民主,以及日益惡質的資本主義──或者說「當企業繼續購併國家」,提出最大的挑戰。
按照占領華爾街的發動者之一、左翼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所說3:「占領華爾街基本上一直是前瞻性的青年運動——一群往前看、但前面的路被擋住無法前進的民眾。他們依照規則行事,卻眼睜睜看著金融資產階級完全不按規則來玩,透過詐欺性的投機行為搞砸了世界經濟,竟獲得政府既迅速又大手筆的出手搭救,因此得以運用比以往更大的影響力、受到更尊崇的待遇,而他們自己卻被打入看來永無止盡的屈辱生活。因此,他們毫不避諱地訴諸階級政治,徹底改造現有的政治體系,呼籲(至少對許多人來說)不但要改革資本主義,而且還要開始把它完全廢除。」
我們或許很難想像廢除資本主義的烏托邦,但起碼,我們可以想像改造現行的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另一個世界。
(本文作者為政治評論人、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
註:
可以參考娜歐密‧克萊恩(Naomi Klein)所著的《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崛起》(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時報出版。
2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其著作The Price of Inequality(2012)中提到,現在的美國社會是「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他在二年發表過一篇文章以此為標題,啟發了占領華爾街的口號。
3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2014年,商周出版社。
推薦序
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危機與省思
文/呂秋遠
很榮幸可以擔任「當企業併購國家」這本書發行十週年的推薦人之一。這本書剛出版的時候,我正在英國,有機會與作者赫茲(Noreena Hertz)有短暫的面談。我的博士論文主要探討的議題就是亞洲金融危機與財團之間的關係,所以我對於財團與國家發展的議題,感受格外深刻。這本書對於我在日後補強論文時,有很大的影響。
這本書是以企業與國家的觀點,描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全球經濟發展與資本主義間的辯證關係。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回首這十年,全球化的趨勢並沒有停止,而造成的貧富差距則是日漸擴大。全球化卻反而使全球逐漸形成關稅壁壘,而企業在國家政策的發言權上則是動見觀瞻。本書英文書名是The Silent Takeover,takeover一字應該被翻譯為「接管」更為恰當。
因為政府並沒有真的被企業給「購併」了,但是的確有愈來愈多的資源分配是被企業所「接管」。國家為求企業留在國境內,努力釋放利多,提供這些企業「根留國內」,企業則回報以稅收或就業機會。Silent一字在全書中至為重要,因為這種趨勢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沒有噪音、沒有喧鬧,就像是理所當然一樣,如果有偶爾的雜音,政府就會以「妨害經濟發展」的帽子扣在反對者身上。而當企業大到不能倒時,國家最後就要以預算來解決問題,避免經濟全面崩盤,這就是從亞洲金融危機以後,越來越常見的場景。
財團與國家的關係,從國家自主性的觀點來看,就會更明瞭。政治經濟學者學者依凡斯(Peter Evans)曾以台灣為例,提出新的觀點。其理論主要探討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發展中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的變化。依凡斯認為,造成台灣發展成功的國家機關特性,就是官僚與企業的分離。
在台灣發展初期,國家機關與私人資本分離,因此在推動土地改革時,不會受到太多地主的干擾。政府菁英甚少與資本家互動與交流,使得國家自主性提高。此時官僚亦絕緣於資本家,而高級官僚具有較為廉潔之性格,其專業知識、團隊合作的組織氛圍、經濟決策之人事穩定、機關之間的橫向聯繫較少本位主義,以及經濟官僚機構的幕僚相當健全,因而形成國家機關在經濟發展上,強而有力的決策中心。當時的台灣將軍方排除於經濟決策圈外,國家機關之特性也由軍事征服轉為注重貿易,軍方不介入重大決策,這是台灣不同於一般開發中國家的重要之點。是以,國家決策是在政府高層決策者、高層經濟決策官員與美援會三組人共同影響下形成,亦即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之發展策略,遂使政府高層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與干預經濟之能力。
然而,台灣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國家機關之特性已經有所改變。經濟發展的結果使得本土資本家形成,並且已經滲透入國家機關中,設法利用國家機關攫取私人利益,也使國家自主性與能力相對減弱。民間社會成長,社會力量亦崛起,也使國家自主性減弱。經濟高層官員具有強烈國家干預經濟思維者減少,取而代之的新一代強調自由放任,國家之自主性遂更行衰退,而導致台灣在經濟成長上漸趨弱勢,國家在政策上逐漸傾向企業財團。
從依凡斯的理論與觀察來看,在台灣貧富差距日漸擴大之際,理解這本書就格外重要。或許作者提出世界社會組織(WSO)的理念還有待落實,然而我們必須存在這樣的理想,才能在資本主義與分配正義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點。
(本文作者為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