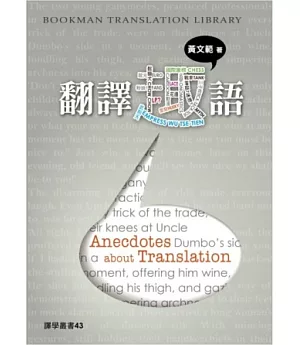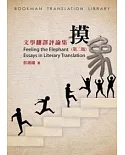序
名作家蘇雪林談她治《屈賦研究》的成果,提到治學之道,認為有皓首窮經的「陳陳相因」,與視同另類的「自闢蹊徑」兩種方式。
她說:「我國又有『直通』『橫通』之說,大概都把橫通做為譏嘲對象。我則不以為然。我曾設有一喻:今有寶物藏於竹竿中,蟲蛀始得。直通者自竹竿下端,節節上蛀,窮老盡氣尚不能達到寶藏的那一節。或已達矣,而對寶物竟熟視無賭,更向上鑽研;橫通者則像一隻鐵喙蜂,翩然飛來,端詳竹竿一下;即知寶藏何節,鐵喙一鑽,便直取寶物而歸了。」
蘇雪林的夫子自道,於我心有戚戚焉,我原是一個以軍事為專業的人,半世紀前,無意中踏上翻譯這條文學邊陲的偏僻路,為蒙名師指點,宛同一隻盤旋在書林譯海上空的孤鷹,縱翼橫通,掠地下攫,雖然不曾取得寶物歸,翅疾如風,也頗能「擒狡兔於平原,截鴻雁於河渚」,得到不少經驗與教訓。其所以樂此不疲,只緣「新徑」竟有一個「趣」字在,青年時啟發了「興趣」,能從茲專務此學,不稍旁顧,雖六十年而不倦;中年竟成為「志趣」所向,更是盛年「樂趣」之所由了。
因此我在一九八九年出版了一個翻譯理論集子《翻譯新語》,娓娓道出多年獨學無友的「單飛」經驗,提出了一些前人所未曾以的新見解與新主張。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國實施了尊《智慧財產權》的《著作權法》,為翻譯千年所未有的大變,從茲以後,翻譯並不一種可以隨意為之的工作,而必須取得原作人同意。此外,面對二十一世紀世界村趨榮景,惟有快速量多的「機器翻譯」,能適應這種新需求;然而優異的翻譯電腦卻要有優秀的翻譯家群才能設計出來。
面對「專業」與「電腦」的雙重挑戰,又遭遇了百年以來不注重翻譯人才的培育,以致形成了「人才斷層」,目前還投身於這項工作的人,就有了實質上與精神上的沉重負荷──翻譯理論的建立。
因之,我在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七年繼續出版了姊妹篇《翻譯偶語》及《翻譯小語》,以呼應翻譯界面臨的新局面,鼓吹翻譯家多多提供自己的經驗公諸譯眾,使翻譯做得更好。
翻譯理論為「知」,翻譯實作為「行」,兩者不能偏廢。做一個專業譯人,既要能「行其所知」,一步一步,本著翻譯理論踏踏實實的做;也要「知所能行」,把自己的心得與試誤後的實驗成果公諸於世。這原本是學術界的常態,學者必須經常提出有新見地的論文,以開拓視界,創建新知,提升學術水準,作為他學術地位的基石。翻譯界過去把「知」「行」分開,從事理論的專事理論,無暇以實譯來親自驗證;做翻譯的專事譯述,不肯將自己的金針度人。但而今以後,我們對從事翻譯工作的人,不但要以翻譯的「質」與「量」,作為衡文的玉尺,而且也要求以他的「論」作評斷的依歸;促使知行合一,翻譯工作者有更多的翻譯理論問世。
翻譯家蕭乾便說過「翻譯四成靠原文的理解,六成靠表達能力。」這是行家話,一般人很少說得這麼透徹。因此我在《翻譯偶語》中,特別論及翻譯文字的修飾,納入〈姓名的翻譯〉與〈疊字的翻譯〉兩篇發表過的論文,著重譯文的修辭與表達。
至於翻譯理論的建立,固然可以吸收前人與外人學說的精華,取精用宏,廣為我用;然而這些理論的「可行性」,則有待實務的磨鍊、體會與證實。
一甲子下來的孤翼獨翔,使我領悟從事翻譯,需要具備兩種文字的知識底子極為龐大,譽之者稱為「君子之學也博」,藐之者稱之為「士人之識也雜」,實則是胡適所說的「為學者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的一個「廣」字。這也就是朱子勉士人讀書:「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事,都要理會,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有了這種底子,治譯自會「嚴密理會,銖分毫析」,才能使建立的翻譯理論臻致高水平;治譯始有趣字可言了。
黃文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