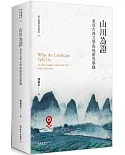序
談論台灣現當代詩史的構成,無非是從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角度做兩種向度的思索。從歷時性的角度言之,強調縱的時間座標,亦即是談論事件的連續性如何去組構一個文化思維與時代意識?而事件的發生又和整體的文化、社會思潮有何重大的聯繫?亦或是受到此思潮的影響?這些討論在歷時性的角度上是互動相涉的,縱使是斷代的定位,每一個被定位的斷代,實際上也是一首連續性的史詩,在史詩裡以一中心主旨去貫串說明歷史片段如何銜接的疑問,進而構築出所謂的「時代思潮」,其中所有的事件、人物,似乎都應被史家處理成此共相思潮下的一個環節,殊相則成為典律之外的歧出。當然,從共時性的角度討論詩史時,則注意的是在一空間內所有並列事物的殊異與同一性,尤其針對殊異點,共時性研究的詩史學者,著眼於橫的空間座標,所以力圖去建立各系統思維之間的關係與結構,在長時期的編年過程裡去定位形成斷代的可能,在已被定位的斷代中,去重現各集團群體的互動場域、界限、層次、觀念的區隔和辯證是如何組構出一個斷代的整體風格,這是共時性史家著力之處。如果說歷時性的討論忽視了整體文化思潮是由各種差異的辯證而組成此一事實的話,那共時性的思考則避開了整體文化思潮內在於各差異群體的深層影響此一問題,張漢良云:
連續性史觀統領了傳統通史的寫法。文學史的情況其實亦無二致。…我們經常聽到下面的論調:一切歧異現象都可透過傳統在源頭認同;任何創新都根植在一亙古不變的基礎上;文學的一切傳遞行為都可訴諸影響。更具體的說,文學史的材料是銜接的。…如果說連續論者的工作,是把缺乏自明環結的孤立歷史事件串連起來,非連續論者的工作則是把表面看來連續的編年史瓦解。非連續性並不是指歷史事件本身的時間斷層,而係史家的觀物方式與整理材料的方法。他眼中的歷史充滿了斷層與空白的材料,由差異、距離、代換與變形的交互作用構成…換言之,他的工作是建立分散的空間。
這個展示的過程中,所有正文彼此辯證,形成一個相互指涉的文化系統,每個被編年史定義的斷代,在非連續的史觀中,均成為相互侵奪的狀態,所有材料重新被閱讀,層次與界線並非獨立的狀態,而是交互地以網狀的方式構造出多重詮釋的詩史系統,在這樣的分散空間裡,詩史家詮釋思維或許就佔領填補了那個被連續性史觀所抹滅的空白與斷裂。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縱使所收集到的史料是客觀敘述的材料,甚至也有可能具備了某種程度的完整性,但詩史的構成絕不只是材料收集與方法運用的問題,還有一個根本的核心,就是史家的詮釋問題,因為「詩史的構成絕無律法可循,律法無非是史家對史實的詮釋」
,所以詩史家的詮釋便成為了一種具有霸權性格的典律,但弔詭的是,這個典律雖然並非具備文化的控制能力,卻可能因為一種錯誤的詮釋、過度的詮釋,會引起其他詩人以至於詩史家的辯證與討論。這種詮釋系統一旦寫定,的確在詩潮當中必然會引起一波波如潮汐般反覆出現的漣漪,這種文化上的影響是源遠流長而意義重大的。
就當代詩學研究的趨向而言,西方學者的關注已從物理科學的認識角度,轉向於意識現象的思維研究,因而如何連結知識哲學的分析,與想像詩學的心靈探究,是相當重要的思維進路。也就是說,本文面對的正在於物理空間與想像空間互相結構的問題,畢竟場域本來就是人類意識的存在場域,提供了文化、心理、社會與經濟層面的功能;而詩論則是詩人對於其處身之場域文化中,關於詩歌創作與反省的理論書寫。如果運用了場域(空間)分析的方式涉入詩論的思維意識,必然會得到新的可能,傳達不同系統詩學之間,彼此角力與融合的真實現象。艾倫.普列德(Allan
Pred)說:
「地方感」概念的形成,須經由人的居住,以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涉入;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積累過程;經由意象、觀念及符號等意義的給予;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的」經驗或動人事件,以及個體或社區的認同感、安全感及關懷(concern)的建立,才有可能由空間轉型為「地方」。
對於詩人而言,空間是情感投射的焦點,是讓他們架構文化建築,充斥文化意義的「場域」,各地域與地域間因著組成份子與領導核心之歧異,導致彼此的文化型態有極大的差異,詩人以自身為本位透過詩歌創作與詩歌理論的書寫,往往呈現場域影響下的特殊感受,不同場域便形成各自的藝術範型與人文意識。對於詩人而言,空間是情感投射的焦點,是讓他們架構文化建築,充斥文化意義的「場域」,而詩社群與社群發行之刊物便是詩人的「場域」,各地域與地域間因著組成份子與領導核心之歧異,導致彼此的文化型態有極大的差異,詩人透過創作與詩論的書寫,往往呈現不同場域各自的藝術範型與人文意識,畢竟場域本來就是人類意識存在之空間,提供了文化、心理、社會與經濟層面的功能;而詩學則是詩人對於其處身之詩壇場域中,關於詩歌創作與反省的理論書寫。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一個重要概念:
文學場是一個力量場,也是一個爭鬥場。這些鬥爭是為了改變或保持已確 立的力量關係:每一個行動者都把他從以前的鬥爭中獲取的力量(資本),交托給那些策略,而這些策略的運作方向取決于行動者在權力鬥爭中所佔的地位,取決於他所擁有的特殊資本。
五○年代迄今之文化場域,不斷產生新的權力資本,此資本的累積形成了新的文化權力與策略,控制了整個台灣的詩學走向。當然,斷代共時性的詩論研究,除對於空間、時間與權力場域的掌握分析外,最重要的還是屬於詩學理論這個主軸範疇,涉及了空間概念的社會學思維,方能架構場域詩學的深度視野。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在《空間詩學》一書裡也提出了一個現象學式的研究思維:
即使是一個孤立的詩意象,若是經過持續的表現鍛造而成為詩句,就可能發生現象學式的迴盪。……透過可感知的實在來證實它,並釐清它在詩句組構中的位置與角色,這兩件任務在我們要考慮的事情中只具有次要的地位。在詩意想像的初步現象學研究中,孤立的詩意象、發展它的詩句,和偶有詩意象在其中光芒四射的詩節,共同形構了語言空間(espaces de
langage),我們應該運用場域分析(toponanlyse)來加以研究。
的確,就詩歌創作而言,必然有其運用的意象與結構;就詩人的表現型態而言,這些限制加上澎湃的情感,以及環境與交誼的影響,也必然會形成可研究的詩論空間。換句話說,場域研究是一個討論詩論有效的方法。嚴勝雄認為:「空間的配合是人類經濟行為的產物,依經濟原則形成各空間位置與空間大小相互密切的有機關係,其間存在著某種秩序…」
,這段話蘊含重要的意義,經濟狀態必然影響空間呈現的文化秩序,場域詩學的研究,乃屬於地理、經濟、社會、文學以及空間思維的複合體。加斯東.巴舍拉提出「空間詩學」的論述方法:
就這種取向來看,這些研究可以稱得上是空間癖(topophilia),它們想釐清各種空間的人文價值,佔有的空間,抵抗敵對力量的庇護空間、鍾愛的空間。由於種種的理由,由於詩意明暗間所蘊涵的種種差異,此乃被歌頌的空間(espace
louanges)。這種空間稱得上具有正面的庇護價值,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附加的想像價值。……在意象的支配下,外在活動的空間與私空間並不是相互均衡的活動空間。
由此可知,詩論與群體思維的誕生,都與詩人面對的各種複雜空間有對應關係。當然,斷代共時性的詩論研究,除對於空間與時間的掌握分析外,最重要的還是屬於詩學理論這個主軸範疇,涉及了場域概念的社會學思維,方能架構詩學討論的深度視野。瑪格麗特.魏特罕(Margaret Wertheim)在《空間地圖》一書說:「由於空間必定是眾人群力的產物,空間概念會反映這一群人的社會形態也就不足為奇。」
,以此探討台灣現代詩發展趨向,與社會群體意識的互構狀態,亦能突顯本文的研究意義。
因此,本文便在此研究方法學概念的基礎上,分成十三章討論戰後台灣現代詩學的發展趨勢,從戰後至2010年做為討論斷限。第一章〈前言〉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方法,並就本文的每章書寫作一聯繫性的概要說明。第二章〈現代詩學的啟航點—「現代派論戰」重探〉以「現代派論戰」作為討論的對象,在過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思維「現代派論戰」在台灣戰後現代詩學發展趨勢的重要意義,藉此呈現五、六○年代詩學的文化傾向,與社會群體意識的互構狀態,亦能突顯本文的價值。本章在前述立論上討論台灣「現代派論戰」時期的詩論問題,分析討論當時各流派提出的寫作態度、方法、理論,其實也肩負著他們自身對於開創新文化視野的某種期待,這種想型塑「文化新典範」的意識,對於任何有機組成的詩社(刊),或多或少地都成為創社的宗旨之一。
第三章〈七○年代笠詩論研究〉、第四章〈八○年代笠詩論研究〉與第五章〈九○年代笠詩論研究〉是以本土詩學的建立作為聚焦的重點,以1964年創立的本土詩刊(社):「笠」作為討論範疇,分成七○年代與八○年代兩大部份,分別分析台灣本土詩學的建立到完成,透過七○年代《笠》批判現代詩走向超現實主義的末流,經過經過鄉土文學論戰與美麗島事件後,在八○年代眾聲喧嘩的詩壇下,笠同仁是如何在政經環境的劇烈演變中,繼續拓深織廣其在七○年代建立的本土詩學,並將其深化於九○年代台灣現代詩壇的場域中,創建出台灣本土且具備高度現代性的的現實詩學。
第六章〈九○年代台灣現代詩都市主題的多向變奏〉與第七章〈新世代詩人都市文本的空間想像〉則關注台灣戰後詩學的另一個趨向,隨著台灣八○年代以降各區域都市化與工業化的傾向日趨明顯,現代詩的書寫思維,也逐漸在嶄新的台灣社會中呈現都市化的傾向,也使得本土的定義必須要涵括日新月異的都市地域,書寫者以生活在都市中的經驗,作為都市觀察者對都市流動與變化的內在思維,其中主要的是要完成人走入都市叢林裡的各種樣態,詩人們開始思考到都市進入人類身體內來彼此互構的生活經驗,年青一代的詩人運用各種流竄在頹廢與解消邊界的語彙、語法、修辭技巧,去象徵或寫實人類本體即都市本體的內在經驗;另一方面新衣帶的書寫者,透過對於都市內空間群的書寫,再次傳達出與前行代相當不同的新詩思維與趨勢,那種與自身共生,在自體之內同化依存的都市思考,使得他們筆下的各種都市空間,不僅反映出單一的主題動線,更產生出某些可供他者重新填充的問號與括號。
第八章〈數位時代的來臨(上)──論九○年代網路詩界的發聲〉聚焦於台灣當代的詩文化卻使得新世代的一群處於矛盾與糾葛的狀態中,再加上接近世紀末出現的主體掙扎與荒蕪頹廢,更讓處於校園的學生陷溺在既不穩定卻又想尋找主體的確立的這種相互辯證的生命糾結裡,當他們抒寫生活思考的作品在平面詩壇場域的封殺下,似乎難以有刊登的出路與抒寫的管道,於是他們只有透過另一種糾合群眾的方式來自我夢囈,前往網路張貼扮裝後的原始自我,畢竟中生代和前行代對於新世代本來就抱著許多疑慮的態度,或許因為如此,我們反而可以在網路與校園詩刊裡看到更多的新詩創作。而網路詩的呈現,無論是將網路當成發表介面,或是網路本身就是創作工具(如超文本詩),實際上都存在「反文化霸權」的延伸思考,又因平面文字出版媒體掌握在特定權威的手上,網路創作者便採取以網路精選的方式,反過來再以文字出版品去尋求自我的定位,使得網路詩人橫跨兩個界域,取得了雙重身份的建構。新世代的詩人群體,也不需再執著於文字出版品的單向建構,或許經由網路仲介之後的雙向身份建構,反而可以擺脫前行代的夢魘,建立新的發表策略與模式。
第九章〈數位時代的來臨(下)──論八○至九○年代新詩社群的結構與思維〉則關注著自八○年代以降,至九○年代台灣詩社群與詩學之走向的兩條思考路線,一是大眾消費文化所宰制的詩出版場域,二是大型詩刊與報紙副刊所宰制的詩文學場域,台灣的新詩文化卻受制於這兩類型場域複雜錯綜的互涉控制,這種文化或隱或顯的控制使得九○年代產生的新世代的一群處於矛盾與糾葛的狀態中,而此時全新的媒體工具:網路得到快速的發展,讓對於平面媒體不滿的青年寫手,透過網路解構的特色抵拒平面的文化霸權,不再執著於文字出版品的單向建構,經由網路仲介之後的雙向身份建構,力圖擺脫前行代的夢魘,建立新的發表策略與模式。網路寫手便採取迂迴的方式,先以網路做為發表的工具與場域,反過來再以文字出版品去尋求自我的定位,使得網路詩人橫跨兩個界域,取得了雙重身份的建構。而此時的網路詩人的結社觀念,必然與前行代、中生代的社群觀念產生極大的差異,本章便透過這兩者概念與實際狀態的比較,呈現出戰後新詩走向九○年代以降的發展趨勢。
自第十章至第十三章,分別以詩人票選、兩大報文學獎新詩獎、情詩書寫與新世代定義的再商榷作為四個重要的討論對象,一方面我們從另一種爭奪文化權力與型塑典律的方式來觀察「詩人票選」,可以證明台灣新詩的發展趨勢存在著主流與邊緣藉由「抵制∕抗拒(解構、顛覆)」、「收編∕反利用」的辯證,來塑造所謂的經典,提高自身社群的文化權力。另一方面則透過文學獎場域的觀察,觀看文學獎書寫的結構與格式,而透過情詩書寫更能看出所為年輕一代在這最常經營的書寫主題中是如何與前世代作一區隔,結論時再次提出新世代定義的商榷,並非挑戰世代的定義,而是希望能夠找出另一種觀點與視角。畢竟在台灣戰後詩壇的權力架構中,可以發現過去以紙媒體為主的詩壇,似乎將本土的詩人視為邊緣,而九0年代以降的紙媒詩壇,則刻意忽視網路詩界的存在,而網路百大詩人的票選,便可以視為對紙媒詩界的嘲弄。另一方面藉此論述,突顯台灣戰後新詩的發展趨勢,由新詩的現代化,走向本土詩學的建立;同時,都市詩的大量書寫,更使現代詩走向都市化,迫使本土詩學接受都市也屬於本土的概念;九○年代以降,發表媒體與書寫工具的迅速進步,使得年輕詩人,進入網路,讓平面媒體與數位媒體在九○年代迄今,變成背離卻又互構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