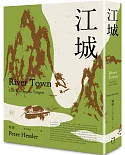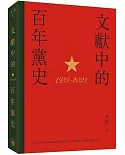劉潤和導讀
本書共收錄了三十五篇文章,全部環繞.香港早期法政歷史而開展,時間觸及由香港開埠到十九至二十世紀交替之間這個時段。表面看似是散篇零章的掌故文字,其實也不盡是如此。所謂
「掌故」即未經考證的史料,事實可真可假,有真有假,亦真亦假。可是本書的文章有很多地方都透露.考證的痕跡,引用了一定數量的中英文材料,如報章、政府文獻,及其他史著的論述等等,加上葉靈鳳是作家,文采斐然,生動有趣,實非一般掌故文章可比(連寫原本極為枯燥無味的香港鳥獸蟲魚等自然風物,也令人覺得趣味盎然,讀讀他的《香港方物志》便知道了)。只不過這裡輯錄的文字,都是刊於不同時段的報刊文章(本書各篇先後見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發刊的《星島日報》副刊《香港史地》,以香客的筆名發表),缺乏了一個貫穿前後的主軸,讀來雖覺有趣,但讀者若不明瞭當中的歷史背景,少不免有難於掌握之嘆。下面的文字就是為了填補這個缺憾而寫的,希望有助讀者加深對本書的了解。
一八四一年一月,當英軍在港島水坑口登陸,香港實際上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後,香港當時面臨.最少三種危機:一、與中國傳統基層鄉治組織斷裂的危機;二、中英文化甚至是中西文化衝突的危機;三、英國管治香港殖民地的危機。
首先,談與中國鄉治基層組織斷裂的危機,這與明清時期的保甲制有關。保甲制在明代原稱為「里甲制」,每里一百一十戶,設里長十人,由丁口及納糧多的十戶擔當,其餘一百戶就分為十甲,每甲十戶,每甲每年一人輪任甲首,負責管理一甲的事務。明代末期及清代,里甲制出現了變化,被保甲制所取代,因為里甲制成了專管賦役徵發的組織制度,保甲制就專責維持鄉里的社會秩序和保安管理,職責包括了催徵賦稅、監督勞力工作、圈派徭役、維護治安,及捕拿盜賊等等。每十家既為一甲,即為一牌,每家值勤十天,而每家門上懸牌均列明丁口人數,便利互相稽查。若遇不法之徒,必須舉報,不報者十家連坐。這種鄉里互保與防衛的系統十分嚴密,有利於及時發現與辦治奸邪分子。
英國於一八四一年佔領了香港島之後,由首席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和英軍總司令伯麥(G.
Bremer)於二月一日發佈了一個聯名公告,上面清楚表明所有居民,希望一切如舊,變動越少越好,因此承諾以大清朝行之有素的舊制,包括保甲制在內為管治香港的根本。根據這個公告,香港政府刊印了第一號憲報,宣佈政府將以普通法和《大清律例》互補使用,統治香港(參看書中〈第一號香港政府憲報〉一文),而基於此,港督戴維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任期一八四四年 –
一八四八年,這位港督並不受香港中外市民歡迎,政績乏善足陳,可參看本書〈中國通港督的失敗〉一文)亦於一八四四年正式立法推出保甲制。
這種制度既可令華人自治,減少政府壓力,增加管治效率,而且又不費公帑,因為保甲制內的牌頭、甲長、保長,或地保等等的職務都經選舉產生,並且是義務性質的。一八四四年的保甲制法例中,特別突出了其中地保一職的地位。政府又於一八五三年更新保甲制的法例時,擴闊了地保的權力,授權地保不只有調解之權,還有促成雙方和解之力,變相成了一種裁決權。源自明清的保甲制中,地保的權力只有上報、調解之權,卻無裁決權,可見香港島保甲制法例中的地保權力,比明清時期還要大。
一八五七年三月,政府再火速進行第二次有關地保的條款修訂,明確規定地保在本甲之內,可以行使一般警察權力,協助民政及軍政人員逐屋搜查、緝捕、詢問疑犯等刑事步驟。這時因為「亞羅號事件」令中英關係又出現緊張和不安(最後導至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當時港督寶靈(Sir John Bowring,任期一八五四年— 一八五九年)明指九龍是包藏禍心的地方,屢屢騷擾香港島,令港島的治安很不安寧。
殖民管治最重要是治安寧定,社會安然和諧,可惜由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五七年前後十三年多,顯然並未達到這個目標。政府於一八六一年正式取消地保的職能,等於宣佈了「以華治華」的理想破滅。保甲制的失敗及最終的消失,最重要的原因是制內的自毀成份,即地保本身的貪贓枉法。一八五八年末期,政府曾刊憲警告所有地保不能向華商勒索金錢,這反映了地保貪贓不潔的整體情況,否則政府何必如此公開揭自己瘡疤。至此,香港的管治危機似正逐步踏入一個不可挽回的險境。
第二,談中英文化甚至是中西文化衝突的危機;最明顯的衝突是言語不通,英國人不知如何把自己的訊息傳達給華人,否則他們也不需要利用保甲制這種傳統的管治手法了。另外還有生活習慣上的差異,英國人一直歧視華人的起居習慣,以為既不衛生,亦不健康,所以把華人居住的區域當成非人之居地,如於一八五六年頒佈的《華人屋宇條例》,嚴格規定居屋的門窗間隔一律必須按照外國規定辦理,這促成了香港最早一次的華籍商人大罷市(參看本書〈香港最早的中國商店罷市〉)。但令他們更大惑不解的,是華人極度抗拒西洋醫療文化的心理,竟到了寧死不從的境地。
一八六六年廣福義祠被發現除神主牌之外,還有內藏屍體的棺木,而更為驚人的是,義祠竟然是窮人等死待殮的葬身之地。傳媒得知事件之後,立即全城轟動。後來政府勒令清理並接管廣福義祠,趕走了所有等死待殮的人,結果尚未斷氣的就伏在街上等死,因為廣福義祠不再是他們的避難所了,結果是死屍就此隨便亂放街頭,不知如何了局。因為華人寧死也不肯進西式醫院,即寧願暴屍街頭,亦不妥協,令殖民統治者傷盡腦筋也找不出解決的辦法(這是後來政府決定贊助建置東華中醫院的重要契機)。
上面兩種因素最後直接導致英國管治香港殖民地的危機。英國開始殖民統治香港之日,表面採取「以華治華」的間接懷柔手法,其實真正的直接管治手法是十分嚴苛的,這種手法一般不易察覺,但卻從刑事審判及執行刑罰過程中完全暴露了出來(參看書中〈早年香港刑罰雜談〉、〈香港執行死刑沿革〉及〈香港笞刑史話〉)等文章)。
香港第六任總督麥當奴爵士(Sir Richard G. Macdonnell,任期一八六六年— 一八七二年)便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他一方面以苛酷的手法管治香港,另一方又催生東華醫院作為其間接管治的緩衝。何以如此?我們必須明白其間的來龍去脈,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其中的兩面管治手法。
港督麥當奴接任前後,香港正面臨.另一空前的衝擊與震盪。一八五六年十月發生了「亞羅號事件」,引發第二次鴉片戰爭。新安縣全縣士紳為此無不同仇敵愾,於一八五六年十二月議決嚴禁向香港供應食物,並號召港島華人停止糧食交易,一月內罷市還鄉,很多居港華人即時響應。香港政府立刻於一八五七年一月初頒佈《維持地方治安法例》,授權警察司頒發夜間通行證。每晚八時至黎明前,任何華人被發現於住宅外而沒有夜間通行證,太平紳士有權即席懲處,或罰款一至五十元,或拘留一至十四日,或當眾鞭笞二十鞭以上。任何人被懷疑為密探、搧動破壞者及海盜等,政府有權將之驅逐往其他中國地方。在宵禁期間,任何華人若被懷疑意圖不軌,軍警有權格殺勿論。這條極盡歧視華人能事的法例,足可看出當時華洋之間局面的緊張,與政府杯弓蛇影、寧枉無縱的手法(在此危疑不安的氣氛下,於一八五七年一月十五日爆發了「毒麵包案」,全港四百多名英國人,不分男女老幼,吃完張亞霖裕盛辦館供應的早餐麵包後,都中了砒毒,案情撲朔迷離,最終成了懸案。參看書中〈全港英人中毒的毒麵包案〉一文)。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割讓九龍半島告終,英國於一八六一年接管了九龍,面對的是更盛的華人怒火;同是一八六一年,政府正式宣佈取消保甲制和制內地保的職能,連間接管治以作緩衝的願望,也正式幻滅。一八六七年,清廷和香港因為走私鴉片的關稅問題而反目,清廷一怒之下,派出船艦封鎖香港二十年,由西自汲水門,到東面鯉魚門外的佛頭洲,及北面九龍城寨等地設立關卡收稅,大有同歸於盡的意思。
基於以上種種事態,實在無法令人相信英國的殖民手段會是前述 「以華治華」的間接緩衝方式。可是英國的直接嚴苛管治手段,在一八五七年頒發夜間通行證之前,不易令人察覺,只有在刑事審判的框架內才能夠看得比較清楚。
延伸至香港的英國法制與本土不同之處包括:一、香港沒有英國的大陪審團制度,這個制度決定法庭應否受理案件,不應的話法律程序就宣佈終結。二、香港以律政司取代了大陪審團的職能,由他決定案件應否受審,而又同時擔任主控官員。三、香港法庭的陪審團只有六名成員,是英國的一半,而所有陪審員均是歐籍人士,其中有些甚至不懂英語(參看書中〈陪審員制度〉)。四、香港受審的華人絕大部分不懂英語,過程中必須倚靠翻譯,而這些翻譯在法庭上起.決定性的作用,影響審訊至巨。歐籍人士更常常借此攻擊他們無能,水準低劣,貪污舞弊等等(參看書中〈早年的法庭通譯〉)。
法庭的中文翻譯由一八五○年代中期開始,當時最大的一宗醜聞是「高和爾(Daniel
Caldwell,他另有一個中文名字叫高三貴)事件」。高和爾語言天份極高,除英語外,還懂馬來語、印度斯坦語、葡萄牙語和廣東話。大部分審訊都由他負責翻譯,而他另外又常身兼兩職,即助理警察司及控方證人。後來高和爾被揭發貪贓枉法,私通海盜,如此的官員出任法庭翻譯員,在審訊過程中,真有司法公正可言嗎(參看書中〈高和爾與黃墨洲案〉及〈華民司憲高和爾的醜聞〉二文)?
但歐籍人士不斷向政府施壓,說一些罪犯本可順利定罪,但由於技術問題而被他們脫出法律網羅,又指責警察無能和法庭定罪率低。為了回應這些責難,政府於是採取激烈的改革,目的是加快定罪程序和提高定罪率。此外又盡量利用下級法庭審案,為避開陪審團審訊而減少使用高等法院,並以警察力量干涉個體自由,作出侵權的行為。這種改革即時令香港裁判司法庭的定罪率上升,因為改革令裁判司法庭內控方的舉證標準大為降低,令裁判司得以輕下判罪,間接令辯方的論證可有可無,草草了事。
在高等法院方面,也推出了四種激烈改革。第一,放寬定罪的嚴謹性,例如模糊不清的財產擁有權,及受害者名字並未弄清楚的環境下等等都可以令被告定罪,而非作為疑點,利益歸被告。第二,當證人潛逃不現身於法庭時,他被拘留時所作的文本宣誓證言,容許在審訊時作為證言宣讀。英國法院只容許證人因死亡缺席審訊時才能這樣做,否則無效。第三,由一八五一年九月以後,廢除陪審員全票定罪的規定,一般案件只需四比二票即可定罪,只有死刑案件才需要全票定罪。如此一來,陪審員定罪的速度自然加快。
一八五八年又修訂陪審員人數。由六人增至七人,定罪的多數票就更容易取得了。一八六七年以前,這種情況在英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第四,當時華人在法庭宣誓,如斬雞頭、摔破碗、燒黃紙等的發誓形式(參看書中〈早年法庭上的古怪宣誓方法〉一文),令人感覺十分可笑而被奚落嘲弄,香港法庭因此於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六年間將之取消。可見,在這五年裡香港法庭的做法等於逐步向陪審員指明華人的證詞是不可信的,完全可以置而不問,否則何以連宣誓也被作廢了!
傳統中國一向不鼓勵民眾告上法院,只希望在士紳或鄉里長老之間和解收場,但由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六六年二十年間,作為被告而現身香港低級法庭的人,接近十三萬四千人,每年約為六千七百人,等於當時人口的百分之八到十,有些年頭甚至達到百分之十二。這些被告大部分是華人,所犯的罪行在英國法律中簡直是聞所未聞,例如忘記攜帶登記證、夜行違反宵禁令、形跡可疑等等。其中少於三分一被告被裁判司判定無罪開釋,其餘大都被判處短期監禁、公開鞭笞、剪辮、驅逐出境和擔枷示眾等。
除法庭審案外,還有其他苛酷的措施,例如為了控制華人而實施的警政手段,包括夜間通行證及必須攜帶燈籠的規定;華人住民登記條例;大幅提高警力與民眾的比率;禁止娼妓、苦力等與歐籍人士的頻繁接觸等等。以上就是麥當奴爵士於一八六六年接任港督時需要直接面對的場景和實況。
港督麥當奴對此當然毫不畏縮,而且更加變本加厲。他叫自己的政策為對付華人的社會革命。他堅決認為,自己面對的是一班毫無人性的頑劣海盜暴徒,只會殺人縱火,結論是以文明的法律待暴徒,只會徒費心力而已。
接下來他又擴闊了控制和打擊範圍。他恢復了港督寶靈於一八五○年代末期已取消的華人戶籍登記,還加入了一些罪行的集體連坐責任;加大了管控娼妓和賭博的力度,以便警察監控;擴大了香港警隊的編制,成了英帝國最龐大的警隊編制之一;還有,他又推行了墨刑和驅逐離境的政策。根據規定,所有犯罪的華人,宣判後都容許緩刑,但必須於左耳珠刻一箭形符號,然後立即驅逐出境。若犯人潛回香港被捕,等於兩罪俱發,先公開接受鞭笞之刑,接.送回監房服完先前緩刑的全部刑期。其實這個政策於一八六六至一八七○年之間是違法施行的,因為並無法律依據,到一八七二年才完成立法的程序。
雖是如此,港督麥當奴並沒有放棄以間接緩衝的手法來治理香港,因為管治殖民地需要兩手準備,軟硬兼施。他於是利用先斬後奏的形式以賭博發牌政策把賭博合法化了(參看書中〈麥當奴的開賭法例〉及〈開賭助餉的防務館風光〉),並把由此而日益膨漲的收入,挪移去興建東華中醫院,最終催生了一個為政府默許的「華人政府」,完成了最初「以華治華」間接統治香港的初衷。由於不涉及本書的內容,這裡就不再多說了。
(劉潤和博士,歷史檔案管理學及歷史學者,現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副教授,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名譽院士,香港歷史博物館、文化博物館名譽顧問,主要著作有《新界簡史》、《香港市議會史一八八三至一九九九》、《歸程熹願:香港走過的道路》、《經明國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