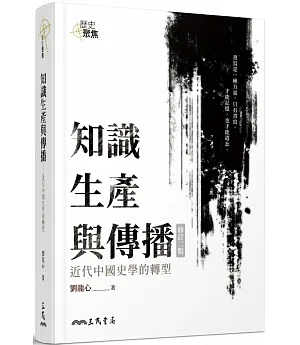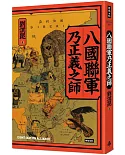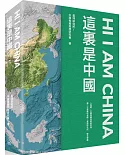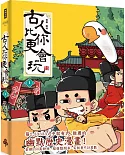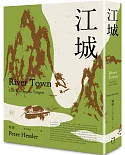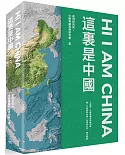修訂二版序
2019年初這本對我而言延宕已久的書終於面世,沒想到去年9月出版社通知我,書的庫存量已經不多,準備要再版了。當時有些驚訝,心想一年半不到的時間,這本討論近代史學的書就能再版,是不是表示這樣的課題還是有些讀者關心?因此藉著這個機會,把初版中的一些錯誤和不足之處加以增補修訂,並加上索引,方便讀者檢索,唯全書基本架構和論點不變。
二十幾年來,研究、教學幾乎占滿我所有的生活內容,而各種學術活動更成為我尋思往事、繫年紀事的座標。2020年好不容易迎來期盼多年的休假,不料遇上Covid-19全球疫情肆瘧,原本配合休假而安排的出國研究、開會等活動,一時之間全數停擺。日子忽然像一列急煞的列車,一下子慢了下來,原本清晰映襯在窗景中的自我忽地消失不見,這時,我才看出了遠山近樹之別、瓊田翠島之美,注視著那些停在平交道上等待列車通過的行人、騎士,才發現他們只是我生命中極為短促的一道風景,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不懂得他們的人生與苦樂。窗外移動的形體和車箱中的自己,其實是兩分的世界,一直以來在快速飛馳而過的窗景中觀看的自我,原來只是鏡像。
休了假,不能出國,留在臺北卻意外多出許多時間。7月下旬中研院近史所呂妙芬所長邀我在「思想文化史研習營」做了一場演講,談「史學史還可以怎麼做?」隨後又因科技部人才培育系列講座,以「知識論域與近代史學」為題,從去年(2020年)9月到今年4月,總共進行六次演講。這一連串的演講都和近代史學相關,準備過程中,我彷彿在慢下來的列車窗景中,體會到窗裡窗外兩分的世界,當窗外折射的鏡像不再,我才赫然發現自己其實一直只是坐在高速行駛的列車中,自以為的「預流」,不過是「物我合一」的鏡像。做為史學史研究者的我,竟未能覺察史學史研究從何時開始凋零若此?
1930年陳寅恪在〈燉煌劫餘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照理來說,史學史研究者應該是最敏於時代之變與學術潮流之人,可是為什麼我看得出學術潮流之變,卻對自己研究領域的凋零提不出任何解釋?是我太忙、太融入?還是所有的歷史研究者都太忙、太融入?當日子慢下來之後,我開始思索這些問題。陳寅恪說這話的時候,顯然在一個亟需倡議「新材料」重要性的年代裡,但如果是一個普遍重視新材料,卻不見得能夠相應提出新問題的年代,陳寅恪又會怎麼說呢?在學術分科愈來愈細的今天,我們是不是早已習慣在自己的分支次領域找材料、提問題?卻毫不在意自己在什麼樣的框架下認識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又有多少是從既有的研究脈絡出發,並持續影響著今天的我們?或者更多時候,我們是不是只能卑微地期待新材料的出現,或乞靈於國外的問題意識?如果大多數的歷史研究者沒能意識到這些問題,那麼史學史研究的凋零,恐怕就不只是一個分支次領域的事了。
不過身為史學史研究者的我們難道就沒有責任嗎?我們意識到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典範長久以來如何制約著我們嗎?1926年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裡提及「史學史的作法」時曾經表示:中國人「回頭看」的性質很強,常以過去經驗做個人行為的標準,所以史部的書特別多。然而「中國史書既然這麼多,幾千年的成績,應該有專史去敘述他,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也沒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種現象。」梁啟超這段話看來稀鬆平常,後來的研究者也沒怎麼注意,實際上梁啟超在似有若無間已將中國過去「幾千年的史書」串成一氣,使其前後相連,為的就是要讓人感覺不出古今之別。而久處學科體制下的我們,也早已習慣這種「古今無別」的提法,自然不覺得用「專史」去研究中國「幾千年來的史書」有什麼問題。殊不知「專史」是現代史學的一種表現形式,當我們從「專史」的角度重理中國史學時,就不可能不涉及舊史的「改造」,而這種改造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
梁啟超早在〈史之改造〉中曾毫不諱言地表示:中國古代著述,大多短句單辭,不相聯屬,少有長篇記載,所以事與事之間很難產生聯絡,而真史當如電影片,前張後張緊密銜接,成為一軸。因此他認為今日之史必須表現出人類活動的狀態,其性質為「整個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有機能的」、「有方向的」。要把原本不相聯屬的過去,連成整個的、成套的、緊密相銜的歷史,可見得梁啟超的改造方案實與20世紀以後的史學走向相彷彿,建制化的學科體制和科學史學的概念,一方面把「中國史」建構成一個從古到今,一以貫之的共同體,一方面把探討、描述中國過去幾千年史學成就的「中國史學史」塑造成中國歷史文化所留下來的史學遺產,兩者同具「集體同一性」的表徵。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史學史自始即以一種現代學科的視角,將中國史學視為一個持續發展、連續不斷的歷史進程,為了探究此一進程和綿延不絕的中國史如何為一代代的史家所紀錄與書寫,歷朝歷代的史書、史官、史家、史學就成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主要對象。說到底,中國史學史幾乎是為了說明中國史的正當性而存在的一門次學科領域。
然而,當歷史研究的課題愈來愈多樣化、細碎化之後,「大寫歷史」逐漸失去它的吸引力,各種新興的研究領域開始關注微觀的、日常的、地方的、去中心觀的、後殖民的歷史,「國史」不再是歷史研究的唯一視角,中國史學史存在的合理性也隨之動搖,多數學者長年浸淫在自己的研究課題中,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過去寫在CV上的學術專長從「研究領域」變成了「研究課題」,而外在的學術規範也助長了此一趨勢。近二十年來的期刊評比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進一步制約了學術論文的寫作格式,「研究回顧」成了「前言」或「研究背景」必要的欄位。當研究者提出一個個細碎而專精的研究課題時,需要回顧與對話的對象自然也就限縮在極小的範圍內,以史家、史書、史學為書寫對象的史學史便與絕大多數的研究課題斷離開來,再無用武之地。可是,此一現象史學史研究者發現了嗎?如果史學史研究者自己都沒有意識到此一轉變所帶來的影響,史學史研究恐怕真是凋零已極了。
史學史研究需要新的活水,新的視角。最近的思考沒來由地讓我想起很多年前一位來系上客座的教授,旁聽我在研究所開的中國近代史學史專題之後說:「你的課可以和任何一個人合開!」當時以為這只是一句玩笑話,並不以為意,多年後回想才知其深意。面對研究趨向的改變和學術環境的變化,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確需要新的思路與定位。也許我一直不能算是一個「典型」的史學史研究者,但長久在此耕耘,總有些不吐不快的想法。有關「新史學史」的具體做法,說來話長,無法在此細述,也許留待來日另文發表。再版在即,藉此機會聊記一年多來的想法,同時為慢下來的腳步留下一點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