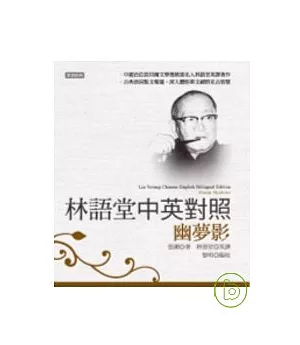推薦序
學貫中西,百年一人
兼具「君子」與「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之美的林語堂
作家 張曉風
在中國,在古代,如果你要讚美一個人(哦,所謂人,指的當然是男人),用的字眼可以很簡單,你稱他為「君子」就可以了。君子怎麼解釋呢?它意指一種受過完整教育,品德優美,宅心仁厚,不與人爭卻又頗有擔當的人。然而,「君子不器」,由於他的養成教育極好,所以他不適合作一個職業賣麵包的人或製車輪的人,他不投入實務的有價的操作,他該作的事是社會的精神導師,擘畫十年或二十年後國族該有的走向。
在西方,在中古之後,如果你要讚美一個人(哦,抱歉,此處所指的人仍是男人),該用的字眼應該是Renaissance
man,我姑譯為「文藝復興人物」。此詞的意旨和「君子」大致類同。例如,兩者皆同樣博雅多禮,同樣自期自許以天下為己任,但後者卻多了些務實的本領,有點像孔子說的「多能鄙事」。不過孔子在說這句話的時候,竟不免十分抱歉的先加一句「吾少賤,故……」。由於年輕時候卑微貧苦,孔子學會一些雜七八拉的技能,究竟是哪些技能?孔子沒說,想來其中有些是不登大雅的,例如煮飯。Renaissance
man卻不一樣,他們是「吾少貴(他們皆是識字的貴族),故多能伎藝」,這些伎藝包括儒家的音樂、射擊(或劍術)、駕駛、數學,以及儒家所沒有的現代天文地理知識,以及嫻於航海或機械的種種本事,算來「文藝復興人」應該是一種「極優良人種」。
我所知道的林語堂先生其實就是很難得的兼具有「君子」和「文藝復興人物」之長的人。前者比後者多一份優游園林的隱逸雅緻,後者比前者多幾分新時代男兒的彗黠矯健。
林語堂先生是民前出生的人,算起他的身分是既貧賤又富貴。他是福建漳州人,家住山區。那一帶原是窮地方,卻山清水秀。他的父親是一間小教會的牧師,薪資有限,但因教會和洋學堂有關係,林語堂因而擁有極好的教育資源。林氏自小穎悟,再加上環境關係,使得他的英語能力無人能敵。林氏啟蒙之際,在那個時代,多少要熟讀一些經書,所以他也就很自然的學涉中西。林氏後來又留了美、留了德,並且取得語言學方面的博士學位,但那頭銜和他一生的風雲際會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他的一生和什麼有關呢?譬如說,他是個健康愉悅的男孩,且是個極佳的短跑選手,這一項後來被他妻子視為優點(她曾在運動場上見過他的風姿),因而願意「下嫁」。妻子的廖氏家族非常富有,對林氏的前半生極有助益。
林氏的另一貴人是胡適,他曾「偷助」林氏一千銀元(若干年後,林氏知情歸還)。胡之所以助林,表面看是胡的俠氣,其實也是林氏來自家人之愛的少年意氣風發,令人愛重。
林氏的真本領是寫作,中文的以及英文的。
此外,林氏懂得向中國人推銷西式「幽默」,並且向西方人推銷中國的放達疏淡。在那個年代談幽默,喊打的人其實不少。一般思想親共的人哪能容得你一杯咖啡一塊蛋糕,並且言笑宴宴來論「幽默」呢?他們希望你「廿四小時都在為人民服務」。至於真正的人民是不是「被服務了」或「被殘害了」,那才是天知道。林氏的書多年來一直都是老共轄區內的禁書,但林氏向美國外銷中國文化這一部份卻極為成功。林氏的英文著作分三種,其一是創作,如《生活的藝術》。其二是改寫,如短篇小說,其中〈碾玉觀音〉一篇有極好的新詮釋,把個無聊的鬼故事,寫成了經典愛情。
後來姚一葦教授所編的〈碾玉觀音〉,劇本就是承襲林氏了不起的新詮(而不是採用明人重述的宋人平話)。其三是中翻英的翻譯,如張潮的《幽夢影》。三者皆是才子作,各有勝境。
林氏是少數靠一枝筆而活下來的文人。更奇怪的是他的「筆潤」來自美金,這大概是中國五千年來沒有的事。後來的美華作家如湯婷婷或譚恩美也曾暢銷一時,但她們畢竟是華裔美人。最近寫文革故事的哈金當然也算一員猛將,但還差林氏一截。林氏著作又多又好又極富使命感,百年之內恐怕很少有人能接近他所締造的光榮紀錄。
可是,林氏晚年為了想製作一架中文打字機而耗盡心血和金錢,機器終於做出來了,卻因沒人肯生產而成廢物。林氏和「文藝復興人物」一般,是自認有能力駕馭機械的人。林氏當年為之瘋狂投入的那一搏,其中種種艱辛,在電腦時代輕易就解決了。四十年前已謝世的林氏,如能看到電腦中文打字之便捷,恐怕不免為自己浪擲的時間而嘆息吧!
不過,以他的的性格而論,他大概也是「終不悔」的。
林氏安息在陽明山腰的故宅庭園?,面對著他生平最深愛的觀音山夕照。人世無常,什麼都會過去,書,也許是比較接近永恆的一種存在。在作者離世許久之後,仍繼續發言。
欣聞正中書局刊印林先生所譯英文書八種,並且是中英對照的,故欣為之序。
古知孔子,現代則知林語堂
馬健君
東吳大學英文系副教授暨林語堂故居執行長
很多人都說,一個人如果中文不好,英文一定也學得不好。為什麼會這樣呢?根據我多年英文教學的經驗,發現如果學生中文程度不好,他們在英文學習上也會面臨很多問題,不若其他中文程度佳的同學。反觀英文能力好的學生,中文程度也一定具備相當的能力,因為他對中文的高度理解加強了他的外語吸收與理解能力,使得他的外語得以運用自如。我們所熟知的林語堂先生便是箇中的佼佼者。
林語堂先生一生最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寫作上的成就;但他許多有關於翻譯的文章,更為世人所津津樂道。中西兼修的背景,使他的翻譯功力除了文字意境上的傳遞,更富有人文精神方面的諸多挹注。藉著文字,他將華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生活中細微之處,點點滴滴地傳達給西方讀者,使他們能夠瞭解其中巧妙之處,進而欣賞中華文化的精彩。如此珍貴的文化資產,是我們身為華人的幸福與驕傲。
在這次正中書局重新再版林語堂先生的八本譯著中,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孔子的智慧》。一般西方讀者對於孔子的了解,大多來自《論語》一書,以為孔子只是個滿口格言的智者。彷彿要為孔子「驗明正身」,林語堂先生翻譯《論語》時,他不逐字逐句消極翻譯,而是把原著內容重新分門別類,分成「孔子的生平」、「中庸」、「孔子的格言」、「儒家社會秩序三論」、「論教育」、「論音樂」以及「孟子」等等,從《四書》、《五經》以及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等書籍,以英文特有的表達方式,使西方讀者能夠經由各種面向來了解孔子的思想以及儒家的哲思。這種譯法,既能抓住原文的形式與精髓,又能讓西方讀者容易理解,知道孔子與儒家思想是如何深入華人人文世界。
《老子的智慧》,也就是林語堂英譯的《道德經》。他以深厚且淵博的國學背景,運用道地的英文,汲取中文文字間微妙的語意,忠實傳達《道德經》的精神,譯文內容深刻,表達平易淺近且貼切流暢,使人閱讀容易且印象深刻。
林語堂先生的翻譯中有創作,創作中有翻譯。他特別摘選一些為讀者所熟悉且別有幽默、風趣的文章,精心編輯成《蘇東坡詩文選》、《幽夢影》、《不亦快哉》、《西湖七月半》、《揚州瘦馬》以及《板橋家書》等書,把蘇東坡、張潮、金聖歎、鄭板橋等這些才華洋溢、樂享生活且曠達的文人介紹出來,使中文讀者藉其生花妙筆的英文書寫,增加學習英文的興趣;而西方讀者,則能透徹準確地理解原文,體會中華文化的優美與價值。無怪乎許多外國人在提到中國的文學與思想時,每每會以「古知孔子,現代則知林語堂」這句話作為概括。由此可以想見林語堂先生對溝通文化以及增進國際視聽的影響力。
反觀現在,隨著科技網路快速發展,以及國際化、全球化趨勢影響之下,英語文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同時,也隨著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華文世界人口增加速度高居全球之冠等因素,中文成為全世界僅次於英文的第二大使用語文。逢此時刻,林先生這幾本書的再版,更具意義。希望能有更多的中文以及英文老師把它們作為教材,讓我們的孩子除了提高中英文能力之外,也更能深入了解中華文化的豐富多元並且引以為榮。
導讀
安身立命的性靈之書
鍾怡雯
元智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作家
張潮具有多重身份,是詩人、詞人,亦以刻書家傳世,流傳的著作其實頗豐,然而,除了研究者,大概沒有人會讀《虞初新志》、《花影詞》、《心齋聊复集》、《奚囊寸錦》、《心齋詩集》、《飲中八仙令》、《鹿?花館詩?》,或者《檀几叢書》、《昭代叢書》之類的刻印作品,惟《幽夢影》因為林語堂,因為貼近生活,最廣為人知。這同時意味著,張潮最為人所熟悉的,是他那套以經史子集為底,浸透了傳統中國文人教養的生活觀。
我讀初二時,從老師那裡得到一本漢京版的王名稱校本,似懂非懂,竟然也讀得有滋有味。這本書為一個成長在赤道的文學少女,開啟了古典文學之門,讓我得以窺見龐大幽深的中國文化,窮一生也難以窮盡的深宮大院。傳統中國文人自小涵養於國學,隨手拈來皆學問,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話來講,他們是有教養的世代;至於我,出生於一個連文學教養都說不上的工人家庭,這本書遂只能成為「典範的追求」。
《幽夢影》語錄體條列式的隨興形式,適合在上下課候車的零碎時間閱讀,翻到哪裡讀哪裡,讀完之後盡可以在搖擺的校車裡慢慢發呆,回味,咀嚼。介於文言文與白話文之間的「淺白」文言文,恰好讓一個沒什麼古典文學基礎的中學生可以獨自揣摩,隨進入一個遙遠而美好的時空,得以暫時抽離現實,乃因此生出難以言喻的,孤獨的快樂。
如今回想,《幽夢影》的吸引力或許來自距離的美感。它展示了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品味,中國文人的生活態度。藉著張潮的眼睛,讓我發現瑣碎生活竟然如此不凡,月亮、石頭或一棵樹,雲霞、蝴蝶或花鳥,這些尋常之物,在作者靜觀、內省,經過個人的體悟之後,成了足以流傳的生命學問。
張潮正好生於清代,中國傳統學術總結之時,這本書的體驗和學問因此亦帶有總結性質。他的一家之言,乃是以中國學問為底,收束到個人性情裡頭再放出來的,個人風格強烈的生命哲學,絕非單純的知識。所以周作人說此書「是那樣的舊,又是這樣的新」。舊是指張潮學問的來源,新則是五四大力提倡的個人主義。這種既新又舊的生命情調同時也屬於林語堂,所以林語堂喜歡張潮。
林語堂曾創辦《人間世》、《論語》、《宇宙風》,提借散文應「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生活的藝術》流露的名士派風格,這些特質都承張潮「閒適哲學」是一脈;林語堂以軟性筆調介紹中國人的文化、生活、民族性、男人與女人,這種「抒情哲學」亦頗類張潮:在抒情與論述之間,夾敘夾議,充滿情趣,仰賴的完全是作者個人的魅力。張潮「以風流為道學,寓教化於詼諧(石龐〈幽夢影序〉)」,林語堂則提倡幽默,同時亦深得風流精髓。
林語堂曾說《幽夢影》是文人的格言,顯然他認為張潮極能體現中國傳統文人的人格特質,因此「數十年間孜孜不倦地推介《幽夢影》這部書」(見黎明編校序),翻譯此書,讓西方世界見識中國文化。兩人相交於不同的時空,卻同樣具有「純粹的生活」,那是明朝文人最重視的「性靈」,一種清潔、透明而單純的性情質地。作為基督徒的林語堂曾經說,《聖經》讓他嚮往「清潔的生活、純粹的生活、單純的生活、有用的生活」。《幽夢影》之於林語堂,則有如中國版的《聖經》,是那樣的有用又無用,那樣的能夠讓人在濁世裡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