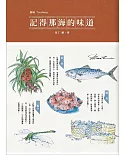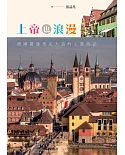臉上雀斑點點的報童當街叫賣,是西方電影裡常出現的場面,幾個鏡頭溶出溶入,身旁半人高一疊報紙不旋踵售罄,一樁攸關劇情走向的新聞立馬成為舊聞──這樣的景況總讓直至報業走下坡才入行的我,揚起一股仰之彌高的慨嘆和激昂,以為到了倫敦,還有機會瞻仰艦隊街的榮景,可惜落了個空,大城市裡固然書報攤星羅棋布,新聞紙市場大概仍保溫中,卻連九一一爆發,也不曾聽見有人扯著喉嚨鼎沸一般在高喊號外號外(電視上影音逼真,桌上還有外賣的披薩和可樂);不過,城市裡另有一群人,多半男性偶爾穿插一兩名女性,不定點地向人推銷The
Big Issue周刊,他們是失業者和游民,不願坐享社會福利的救濟或伸手向人乞討,遂走上街頭兜售The Big Issue,一本一英鎊,其中七成收益就用來協助失業者和游民。
我長期不看電視,但每天瀏覽報紙三五份,若說看電視是吸毒,則讀報是酗菸;國際版一向是我的最愛,一日我讀到一則花絮,英國女王掏出一枚一英鎊硬幣,(那硬幣正面鐫印的正是她自己的肖像),向一名失業漢買了一本The Big
Issue,女王說,這本雜誌資訊豐富,編得很好;儘管女王操著的,是不與下層階級相同的貴族口音,消息還是很快傳開,游民和失業者都受到了鼓舞;賣給女王一本雜誌的失業漢說,藉著販售The Big Issue,他得以有尊嚴地躋身這個社會。赫佛爾(Eric Hoffer, 1902-1983)曾挑明著講,「今日西方世界的工人視失業為一種墮落。」在英國,一批失業的工人則依憑The Big
Issue,重獲向上提昇的拉力;我在愛丁堡皇家哩就曾向一名年輕人買過The Big Issue,當我提出為他拍照的邀請時,他欣然擺起姿勢:兩腳跨開,左手扠腰、右手捧著雜誌,脊背挺直、臉微仰望天,藍天當背景他彷彿一尊睥睨不群的雕像,他是一名自信、樂觀、幽默,而且有尊嚴的失業者。
不過,骨質酥鬆畢竟是流行病,另有一批人不此之圖,他們或立或蹲或者乾脆躺臥在行人絡繹於途的所在,以言語以眼神以手勢或靜默無聲卻騷動無比的身體表情在向人乞討,從豐饒之島來的我初體驗,既驚又疑:英國自詡也普遍為世人認同是文明大國,怎麼有不能盡數的乞丐?怎麼能有不能盡數的乞丐?
經過數十年經濟上的銳意發展,台灣的乞丐在媒體一回又一回的揭秘下,已經主要作為一種易於致富的第三百六十一行而存在於這個社會,既有「職業不分貴賤」的大纛護航,也就首先通過了道德的檢視,自然不宜望之以憐憫或同情的眼神,但在我幼時,乞丐是既讓人可憐又為人所嫌惡的;讀小學時候,課外讀物裡有一本《蔣總統說故事》,這個蔣總統是經國先生,依附於一則則小故事的,是一個個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其中有個啟示我記得很牢:我們的手心要向下,不要向上。向下是授,向上是受;向下是施,向上是取;向下是給與,向上是乞求……正是媽媽說過的:凡事要自己先想辦法,不能老向人「伸手」。這套觀念應該是華人社會的集體價值吧?卻看到有人,而且是一大群人,輕易地不把它當一回事,未免讓我開了眼界,好像長久以來身為好學生遵守著老師的叮囑,眼睜睜望著壞學生一個又一個試探禁忌,又不齒又羨慕,既為堅守立場自豪,又吞吞口水好想也小小出一次軌。
更大的疑惑與衝擊,來自這些不事生產的男女,個個看起來都年輕,而且四肢健全;西方人不像咱們亞洲人讓人猜不出年紀,若覺得他們年齡不大,多半八九不離十,若覺得他們年齡不小,實情倒常在意料之外;要入乞丐這一行,在英倫沒有標準配備,不似臺灣,老與殘是必要偽裝術,是乞討者與施與者的無言契約;一回我在臺北鬧區看到人行道外側直挺挺趴著一個人,他滿身髒污,還缺了一條手,我走近一瞧,赫然發現他的另一條手臂藏在身體下方,不小心露出的半隻手掌頗為肥腴;也許天色漸暮,人行漸稀少的某一刻,正如媒體多次捕捉到的,他將迅速躍起,以無影腳的身手躲進一輛前來接應的寶馬車裡。
英國游民大增於十七、十八世紀圈地運動期間,當時毛紡業持續看俏,地主自佃農手中收回土地,改耕種為畜牧,大批農民被迫轉行,有的成了受薪階級,也有的淪為乞丐,離開家鄉,遠走他方;英國是階級分明的國度,上流社會互相交流、通婚,乞丐則與乞丐相互取暖,雖也可能如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在〈乞丐〉裡所說,生出一個大名鼎鼎的作家,卻通常是連乞丐這個身分也一併繼承了下來。
時至今日,儘管大城市裡仍見游民四界移徙,根據官方說法,卻無所謂的無家可歸者,說是英國住房數目遠遠超過住戶數量,法律並明文規定,區政府要為該區居民負責,不僅確保有房子住,不願住屋裡的,還要加以善意規勸,否則區政府將遭處罰;然而,大城市裡確實還有數不清的流浪漢啊,政府說他們是非法移民,要不就是離開了家鄉,來到外地,戶籍地有屋不住,落腳地區的政府倒沒有義務提供住房,也不會遭罰,但有辦理登記的措施,當然,這也僅止於軟性勸說;登記有案的流浪漢(既登記有案,還叫流浪漢嗎?)可以享有每天一頓早餐,麵包牛奶咖啡,每周須洗一回熱水澡,有趣的是,區政府可以強制執行後者,怕他們傷了健康又污染環境之故。
英國對流浪漢的政策,大抵拿捏在讓他們過得去但不能過得好的界線上,只恐一旦關心過頭,難保人數不會過分,比利時便有前車之鑑。
因此可以推斷,眼中所見這些游民,有一部分是他們自己「選擇」了身分,而非被迫,有些只是因為懶(多理直氣壯的理由啊),也有些或許另有追求,極端的例子是,紐約禪宗團體哈德遜河和平締造者中心,舉辦──本質上和我們的救國團舉辦的各種營隊相同嗎?──「街頭清修」已經超過十年,付費參加者多為企業主管,他們不僅把自己搞得渾身髒兮兮,還要設法飄出異味,道地的、刻板印象中的乞丐一個模樣,每十個人組成一個小團體,在周末假日上街討錢去,對他們而言,這款「行動劇」是儀式,恍如在宗教偶像前焚香拜祭、靜坐默想、祈禱告解,為的是鬆解辦公室裡積累的壓力,洗滌心靈,重新認識生命;目前這股風潮已自大蘋果蔓延至曾經的日不落國。
更早之前,在倫敦讀書的某朋友告訴過我,一日,他們的數學老師不告而別,哪裡去了?水露滴落旱地、氣味在風中揮發,沒人知曉;將近一年後,她到倫敦南方臨海小鎮旅行,大啖海鮮後走出餐館,不期然地竟與這名數學老師迎面相遇,數學老師瘦了、黑了,鬍荏有點參差,看來是落魄了,但她忽視不了他的眼神,清亮、堅定;數學老師沒有表示什麼,轉身離去,步伐穩健踏實。
她形容的那種清亮而且堅定的眼神,我並不陌生:亞維儂我遇過幾名男女,各自帶著一條黑色獵犬,他們的瞳眸褐白分明,獵鷹也似,他們的身軀精瘦,豹子一般,身上的每一分毫血肉都有它求生的必須;當我走過,其中一個男人向我伸出向上的手掌,沒有一絲乞憐,我未回應,他將手抽回,沒有一點失望,不亢不卑;我想,如果我掏出錢來,他們應該會給我一個微笑,但是,錢留下,同情請帶走。
必然有著什麼樣的哲學支持他們繼續這樣的生活,且在某一層面上的豐富足以彌補其他方面的匱乏,〈乞丐〉裡那名要飯的退伍大兵,以著對一知半解的詩歌的熱愛,竟至忽略現實中的病與貧窮;我還想到K:不是卡夫卡,無關虹影,是柯慈(J. M. Coetzee, 1940-)的《麥克?K的生命和時代》裡的主人翁,K。
K是個黑人,相貌醜怪,三十初渡,園丁的工作遭解職、母親病篤,戰火帶來惘惘的威脅,他決意實現母親的願望,帶她回少女時代的農莊;此時南非內戰方殷,苦等不到通行證之下,K以手推車載運母親起程,母親卻在半路上化成了一罈骨灰,一路上K遭遇一連串莫名的逮捕、監禁、奴役,而終於在強大的決心下,得以出逃,將骨灰撒在母親生前掛念的土地上;如今那塊土地成了廢墟,幸而仍未遺忘有被植物扎根的本能,K野獸一般晝伏夜出,彷彿蚯蚓或是鼴鼠,在大地上耕種在大地上生活,踏實而且詩意,物質上的肉體、精神上的心靈水乳交融;然而烽火畢竟不在天外而在眼前燃燒,他被捲入一樁陰謀叛變,再度送到集中營,他拒絕吃喝集中營裡的食物,身體瘦弱得影子一般薄,就在眾人都覺他來日無多時,至死方休的意志力讓他再度逃離了集中營……
柯慈被點名為「後反種族隔離作家」的開創者,他與其他反種族隔離作家的不同在於,他不受政治、現實事件的牽制,而直探更隱微、幽冥深處的人性,他曾自白:「對作家而言,更深刻的問題並不是讓自己去鑽研這種狀態(指種族隔離)所造成的困境,而疏忽了它對人性的褻瀆,以及自我的呈現;這也就是說,作家的挑戰,乃是不要被這種狀態的規則所引導,而是要建造自己的權威,以自己的表達方式去呈現死亡和受苦。」準此,固然從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去解讀《麥克?K的生命和時代》是一條線索,對域外的讀者,如我,受到的更大震動卻是K的追求,儘管書中直言「這個世界已經沒有家國是留給自由無羈的靈魂了」,但是K,不屈從、不放棄,甚至命在旦夕之時,仍吃不下集中營裡的食物,因為,他只吃自由的食物。
K是臻於寓言高度的人物,母親死後,他已一無所求,除了自由,一遇藩籬他便要翻越,逃,不斷地逃,宿命得好像障礙賽中的跑馬要躍過一道又一道逼到眼前的柵欄,撲倒了,再跑再逃,沒有終止;或許,大部分的人,不管是紐約參加街頭清修的企業主管,或者是我,是精神上的K,但只是精神上的,侏儒一般的行動使得精神上的巨人更顯得縛手縛腳,但也有些人用行動踐履了,比如那名數學老師,卸下種種定義和身分,來到遠方,重組讓定義和身分割裂成七零八碎的自我,正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所指出的,把人從分類秩序中拯救出來,一個看似「無用」的人,才是完整的人。
我的少年時候,〈橄欖樹〉四界傳唱,當主唱者齊豫一身披披掛掛、一頭蓬鬆亂髮出現在屏幕上時,我朦朦朧朧地相信,她從遠方來到又即將起程前往另一個遠方,那形象有個化名叫「自由」,與波西米亞、與吉卜賽、與他方相重疊;後來我回過頭去想,在與K相同年紀的三十一歲,我隻身去到英國,畢竟還是不脫一個庸俗旅人的標籤,但是內裡我所追尋的,其實是夢中的橄欖樹;出國前我沒有多作準備,唯一的準備是一定出國去,連去哪個地方都遲遲未定案,唯一定案的,是到沒到過的地方;出乎意料的,一個人在國外,鮮少意識到鄉愁,一發現此,初始我感覺到恐懼,好像地心引力失去,人漸漸騰空,不用著地的雙腳要演化成蹼,用以划風,而雙手變成翅膀更有用一點。
這樣的恐懼,來自於失根。
因為對植物的喜愛,我把自己這幾年的生命歷程象徵以植物:十七歲之前在故鄉的我是「根扎在農地,枝枝葉葉向著都市試探伸展」,高中畢業後,憧憬地來到台北,是「懷抱母土,投奔異鄉」,都市裡生活了幾年,也就習慣了也就喜歡了,台北已成我的另一個故鄉,「一顆來自故鄉的種籽,在哪裡落腳,便有自信在那裡穩穩地把根扎下」;這三個階段,都有「根」;直到人在英國,一日我去參觀「倫敦的後花園」雀兒喜藥草園,走進一座溫室,看見一株枯樹上披覆團團簇簇菼色的植物,像菟絲又像女蘿,但都不是,是一種西班牙鳳梨,它沒有根,甚至不必有根,吸收空中水汽便能夠存活;一時我頓悟,這植物已是我的今生,根則如蟬殼被蛻在前世,失去根的踏實也少掉根的羈絆;進一步我想到,會不會有一天,活著,活著像風像一束光,或者也不必像風像一束光,就像一個意念,無形無色,或者也不必像一個意念,像無,無無,形體釋去,而得到更進一步的自由。
就這樣,我竟日坐在愛丁堡植物園的長條椅上看松鼠忙碌鴿子求歡雨停了再度飄下來,我沿著泰晤士河南岸一路沒有終點地走下去,窩在加泰隆尼亞廣場邊看噴水池前愛侶直想把對方吞進自己的腹肚……街景在我眼前流淌,我捕捉它們一如鯨魚大張開口,任海水沖刷湧入,牠只濾取了能為牠所用的浮游生物。
這時候,也許正有另一條巨鯨,也不細揀擇地將我吞入腹中(不知我將成為牠的食物,或很快地隨著水柱排出?);這時候,也許正有另一名觀察者打量著我,也為我安一個流浪漢的頭銜(要別上「New Arrival」或「新手上路」比較妥適呢?)。
真有那麼一個夜晚,我從香蕉共和國走出來,天上飄著細雨,在夜燈映照下像一隻隻密密麻麻的針尖,皮膚是濕而且冷,但體內蓄積著方才在夜店裡的燥熱,像燒著一隻暖爐,冷和熱在互相抵抗著、牴觸著、抵消著;最早的一班地鐵還要兩個小時才會開出,我在街頭走著走著,也就無所謂地迷了路;後來我看到龐畢度中心,儘管彼時巴黎公立展場串聯罷工已有一些時日,但白日裡它仍有不能盡數的遊客,哺養著流浪漢、街頭藝術家及附近的商店,不過,午夜時分一切都歸於沉寂了,除了雨聲瀟瀟;我躲進屋簷底,疲倦使我索性坐了下來,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在最近的一個垃圾箱裡找到一個冰淇淋空盒,帶到屋簷下,就放在我的身軀前方;我躺倒在地,好像一顆等待發芽的種籽,姿勢則屈曲一如新發的草蕨,就這樣我偽裝成一名流浪漢,或者也不是偽裝,那只是一種身分的轉換,來自於心態的轉換,這時候我是一名乞討者了,手心向上(那名露出半隻肥腴手掌的乞丐,難道也是一名演員?)。
天色逐漸發亮,我的眼皮撐持不住地闔上,半睡半醒之間,我聽見了由遠而近人聲喧嘩逐漸向我靠近,然後遠去,又靠近;半睡半醒之間,我想像自己的形體在擴張,不斷地擴張,含納萬物,終於成一個抽象的存在,又想像自己在縮小,不斷地縮小,終於自人間蒸發……
一個有風格的作家底誕生(節錄)
●南方朔
儘管我和王盛弘並不相識,但這本《慢慢走》,在台灣的旅行文學裡,其深度廣度以及文采,的確是顆耀眼珠玉。
這本書有兩個部分,一部分以他的歐洲漫遊為題。每篇以一個當今大家已熟知的共通符號為切入點,?述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另外有個很小的部分則是每篇從一個關鍵字切入,把字當符號,去回想自己的記憶,那也是種生命之旅。以關鍵字和關鍵符號作為寫作的形式,就如同人們在寫作時尋找主題,它固然重要,但其實也不那麼重要,真正重要的仍在於內容,只有形式與內容兩相得兼,才成其為文章。而《慢慢走》就以它的理性與感性交融,證明了作者在台灣年輕作家裡少有的視野與才華。
就以他歐遊見聞這部分為例吧,他主要都在寫蘇格蘭與英格蘭,但他寫的都不是浮在上層的那些景點以及壯觀的事物,而是以漫遊者的態度,透過共通的符號,去看文明的基底,並將所見所思娓娓的加以編織。他做了許多根本的功課,使得漫遊有了智性的縱深;但又能將一切歸照自身,因而又有感性發抒的空間。
因此,他寫網路時代的@,不但能追根究源,也能去質問進步與鄉愁的本質;探討性別關係,能指出「當專注於男女之間的微小差異時,忽略的正是──相較於兩者的相同──差異極其微小」;他會為了代表金錢的孔方兄這個符號,從真菌這個比喻說起,並兼自嘲;他也由乞丐談到柯慈的《麥可?K的生命與時代》,而對人己關係和自由問題作出反思,自有其通達剔透的一面。
此外,他對植物和園藝的認知,其實也是很專業的,連我這個讀植物出身的人也覺得驚奇!
王盛弘是可以被期待的。他細細的用功,細細的編織,細細的想,有著另一種年輕而獨特的韻致。我不吝惜對這本書的推崇,是因為不能吝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