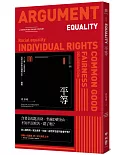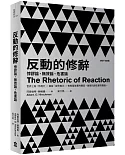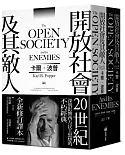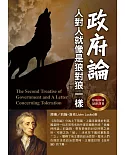譯序
湯馬斯.摩爾的世界與視界
湯馬斯.摩爾是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的賢達名士,出身法學世家,知友皆為鴻儒(荷蘭大儒依拉斯默斯是其一),中年之後仕途順遂,受到英王亨利八世倚重任命為宰相,最後因拒絕改信英國國教效忠英王,於1535年喪命斷頭台,四百年後於1935年被天主教會追封為聖徒。摩爾的一生兼治文史政治,著作等身,尤其精擅人文主義的五項學門(拉丁希臘文、修辭學、詩、歷史和政治倫理學),是當時英國學術界的代表性人物。他在事業巔峰時刻選擇忠於天主教信仰,不願變節改事俗世的新教君王,終究以身殉道。這樣的奇人高風曾經數度拍成電影,其一名為
“A Man for All Seasons”(全才全德之人,中譯片名為《良相佐國》),是大家所熟知。1999年伍頓(David Wootton)新譯《烏托邦》,仍延此名尊稱摩爾。
國科會於四年前推動經典譯注計畫,首輪獲得推薦翻譯的經典之一便是《烏托邦》。此書原以拉丁文寫成,1516年於魯汶出版,1517年於巴黎再版,後經摩爾修訂,增加附錄,於1518年3月在瑞士巴塞爾出版第三版,又於11月刊行第四版。第一本英文譯本於1551年由羅賓遜(Ralph
Robynson)翻譯,依據1516年版。此後多次重譯,仿作和評論更是不斷。最近的譯本為2001年米勒(Clarence H.
Miller)所譯,由耶魯大學出版。英譯本風格各異,有書卷氣較重者,也有刻意改為口語風格。無論如何,各個英譯本對拉丁原文的理解同中有些微差異,注釋有側重背景脈絡(如摩爾當時的政治、理想國的古典傳統等),有針對拉丁文歧義辨義者,亦有剖析摩爾和依拉斯默斯之間的學問切磋如何反映在《烏托邦》的行文中,更有辯論摩爾的用意(摩爾是否藉此書提倡共產主義),或推敲書中的曖昧語氣(摩爾在書尾貶損烏托邦的體制)是否誤筆?這一切種種未決之論使得《烏托邦》一書至今依然疑點重重,亦使得譯者前仆後繼,匍匐於譯事之道路,
深深著迷於摩爾的辯證弔詭的思維。中譯本有劉麟生(1934)、劉成邵(1957)、郭湘章(1966)和戴?齡(1982)等版。國科會「經典譯注」的系列希望著重注釋及評論,故而再度譯為中文。新譯力求信實清暢,
並且妥善注解原作文字與內容的幽微之處,期盼幫助讀者獲得老書新讀的樂趣。《烏托邦》寫成至今將近五百年,上承古希臘羅馬的人文傳統,下啟往後數百年的烏托邦文學與社會實踐,影響深遠。但是,由於文本揉合史實和虛構,兼容哲學思辯和文學手法,因此後世學者產生不同的解讀,甚且質疑摩爾的真正意圖並非建構,而是解構,古典的理想國。
《烏托邦》研究跨越哲學、政治和文學等領域,已有的成果浩大幽深如海洋如山林。下文將僅就摩爾的意圖與修辭等相關議題,扼要解說此書的多重面向。摩爾的生平以及時代背景的縱橫脈絡,學者詹柏士(R. W.
Chambers)已有專書詳述,亦已譯為中文(請見參考書目),此處不另重複,僅於書後附簡要的年表。書後所附參考書目含版本、譯本、傳記、重要研究成果,和摩爾所啟發的烏托邦∕反烏托邦文學,提供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閱讀。
構築烏托邦理想國:摩爾的意圖
烏托邦(utopia)一詞是摩爾自創,希臘原文的兩個字根有互相矛盾的雙重涵義:一為「樂土美地」(eu-topia),一為「烏有之邦」(ou-topia)。摩爾的用意在呈現烏托邦的辯證本質:它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國度。這層弔詭以不同的手法出現在《烏托邦》全書。
摩爾以柏拉圖的《理想國》(The
Republic)為雛形,取其小國寡民、階級分工和公有財產的理念,另外融合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Politics)書中所揄揚的「公民道德」(個人的群體義務,有別於私人操守),在《烏托邦》中構築一個非基督教、共產的城邦國,以理性為治國的上綱原則。但是《烏托邦》不只是哲學與政治學的思辯。摩爾的人文主義學養亦崇尚文學,是以加入文學性的虛構,將抽象的理念納入當時盛行的旅行文學的敘事框架,假託一名老水手拉斐爾.希適婁岱(Raphael
Hythloday)的海外見聞,勾勒烏托邦的典章制度。
全書分兩部分,第二部分為希適婁岱的獨白,描述烏托邦社會的種種制度和習俗;第一部分為對話體,由希適婁岱和摩爾就英國和歐陸的現實狀況提出對立的看法。此書靈感初孕於1515年5月,摩爾奉派至弗蘭德斯洽談貿易,閑暇時幽居客舍思考醞釀,旋即動筆寫就第二部分,10月返回倫敦再寫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建構理想,第一部分批判現狀,就體例和內容而言看似涇渭分明,
因此有學者索性說《烏托邦》是兩本書。
但有更多學者認為兩部分實有互補參照的作用,猶如一枚銅幣之兩面。第二部分的重點包括政府體制、公民教育、婚姻制度、有限的女權、海外殖民、正義的戰爭以及宗教寬容等。第一部分的兩個辯論要旨,一為出仕是否明智,一為偷盜行為之罪與罰(以及引發偷盜的社會、經濟因素)。兩個部分一談醜陋的現實面,一談無法實現的理想,可以說揉和摩爾的社會觀察和視界願景,以虛構月旦現實,既是言志,也抒發對現實的不滿。
首先,烏托邦是一個封閉的符號體系。摩爾如此為它造型:
烏托邦人所居住的島嶼中間最寬的部分有兩百哩,愈向兩端愈見狹窄,形成一個圓周約五百哩的圓形,全島外貌彷若一彎新月。新月的兩個犄角相距大約11哩,海水由此流進內陸,漫開形成一座海灣。由於三面有陸地環繞,此處海域波平如鏡,猶如大湖。全島內腹的海岸圍成一個大港,船隻航行無阻,便利百姓交通往來。海灣入口處一邊為淺灘,另一邊則為岩岸,航道極為險峻,中央突出一塊礁石清晰可見,因此不致造成危險。石上高處建有塔台,軍隊駐戍其中。其餘礁石暗藏水底,非常不利行船。進港的航道只有烏托邦人知道,外來人必須有在地的領航人指引,方能順利入港。
這個地理位置遙遠孤懸,拒絕外來異文化的混染。開國君主烏托帕斯於征服該島之後便挖掘海溝,引水環繞該島四周,截斷與大陸的連接。島國國防固若金湯,航道看似平靜,卻暗藏兇險,入境(initiation)必須由在地人指引。「我」與「他者」的分野明確。
希適婁岱一貫稱呼烏托邦為舉世無雙的國家體制,讚揚它的理性、秩序、嚴謹位階、集體一致和自給自足。島上有54座城市,建築規劃全無不同,彼此間隔等距,城鄉居民輪值勞動,無勞逸之分。於鄉間務農之國民以40人為一戶,配置奴隸兩名。每戶置男女戶長各一,30戶則置族長一人統領眾人。每年每戶有半數的人口回返城市,空缺由城市人口回流頂替,每人輪作兩年,其中有一年生手與熟手各半,一方面為求勞逸公平,另方面也為專業經驗得以順利接力。農戶生產生活必需品,供自己與城市居民消費。城市中的街區規劃亦循公有共享的原則,每戶前後各有一門,門不設鎖,進出自由,中庭則闢為花園,種植草木,四時茂盛。此處眉批特別註明如此的都市設計仿照柏拉圖,遍植草木則是學習維吉爾。
烏托邦的政府體制類似聯邦,由全國54座城市選擇位置居中的一座為首都。官員悉由選舉產生,有些由各戶直接普選,有些則由每個城市選出的代表間接選出。每座城市各選出市長一人。國家公眾之事皆在市參議會及全國大會中討論議決,國民若於私下議論決定,可處死刑。如此的政治架構襲自柏拉圖於《法律》(Laws)中宣示的理想,認為最健全的政府體制應是帝制、貴族統治和民主政體的結合。烏托邦的封閉體制亦見於職業的分派。市長、20名總族長、兩百名族長和13名神職人員不參與勞動生產,其餘國民除了務農之外,每人另外研習一門技藝,毛紡、織布、石工、木工等等。婦女擔任較輕便的職業,如毛紡、織布。衣著只區分性別和已婚、未婚,一生樣式不變。職業世襲,如欲中途改業,必須過繼他人為子。特別喜愛學術研究的國民,經過認證之後即以學者為業。如此,除少數人之外,全國國民皆有兩個職業,平日由族長監督,不許偷懶,否則逐出國門。
烏托邦的制度兼含齊頭式和立足點的平等。此外,烏托邦人奉行位階觀念,長幼有序,尊卑各如其分,集體進食之際長幼隔鄰而坐,長者維持秩序,並且適時進行生活教育。人人每日工作六小時,餘暇用於運動及聆聽演講。每日黎明之前的公眾演講用來灌輸群我之際的義理以及法律觀念。烏托邦人的理性並非天生,而是平日以有形與無形的方式制約培育。有形的教育訴諸法規,例如職業本分;無形的教育則經由習俗,例如男女結婚之前裸裎相見,彼此驗明身體長相,以免婚後反悔成為怨偶。離婚的條件不包括嫌棄外表。希適婁岱如此描述:
選擇配偶時他們謹慎肅穆地遵守一項習俗,可能會讓我們覺得愚蠢荒謬之至。無論初嫁或再嫁,女子由一位受人敬重的婦人陪同,裸身面對她的求婚者;同樣地,求婚者也由一位有名望的男士陪同,裸身面對這位女子。我們或許會嘲笑這個習俗,斥為荒唐;反之,烏托邦人對他國人民的愚昧也是吃驚不已。一般人買一匹小公馬,不過區區之錢,卻是小心翼翼,馬的全身已經赤裸猶不放心,惟恐鞍具蓋毯底下藏著膿包,必得卸下驗證無誤,方才付款成交。但是,擇偶一事攸關兩造後半生是幸福或是怨懟,男子卻草草將事,任令女子全身緊裹衣物,只看到她唯一露在外面的臉,這麼一塊巴掌大的部分,就決定娶她。婚後要是發現對方身體某部分有不能忍受之缺點,豈不冒著日日爭吵的忒大風險?
另一個培養理性的習俗是徹底逆轉金銀的價值:
烏托邦人如果把金銀上鎖,藏於高閣,百姓之中一定會有自以為是的人捏造謠言,說是市長與參議會抱有私心,意圖貪瀆自肥。當然,金銀可以用來打造器皿或藝品,但是如此一來百姓心有所繫,必要之時(例如,將這些金銀物件熔化,用來支付軍人的薪資)他們必不願割捨。為了避免這些問題,他們想出一個做法,完全契合他們的其他體制,但與我們的卻是南轅北轍。他們用陶皿盛食,以玻璃杯飲水,造型樸素但手工精緻。但是,夜壺和其他置於公共廳堂的低鄙的用具,卻是用金銀打造。此外,奴隸身上的鎖鏈腳銬亦是金銀所做。
《烏托邦》所揭櫫的理想經濟是一個無私無我,人盡其力、物盡其用的無貨幣的制度。摩爾年輕時原想成為神父,後來改習法律,留在紅塵俗世。他特別崇敬僧院中安貧守貞的誡律。希適婁岱描述烏托邦中的賢人:
人研究自然,進而敬畏自然,他們認為這是合乎上帝旨意的崇拜方式。國民之中有不少人由於宗教信仰虔誠,因此平日不從事學術研究,但這些人絕非怠惰之徒。他們勞苦自己的身體,造福他人,藉以追求死後的極樂。有些去照顧病人,有些去鋪路、疏浚溝渠、改建危橋,以及剷掘草皮、沙土和石塊;另有些人則伐木鋸材,運送木材、穀糧和其他物品至各個城市。他們為私人工作,也為公家工作,比奴隸還任勞任怨。任何粗重、乏味和困難的工作,一般人視為艱苦骯髒,避之唯恐不及,這些人卻做得滿心歡喜,勞苦自己,換取別人的悠閒,卻不居功,也不去批評別人的生活方式。他們愈是以奴隸看待自己,愈是受到別人尊崇。
這恐怕就是摩爾最真心的個人理想。他在俗世為人夫、為人父、為人臣子,但是心所嚮往的卻是如此的「去我執」的奉獻情操。他的理想國的基石委實便是公社制度、共產共工。《烏托邦》第一部分譴責錢財為萬惡之首,第二部分說「驕傲」(以榮華富貴自負自喜)是萬惡之源,除惡之道唯有廢除私有財產。
實話虛言:摩爾的修辭策略
《烏托邦》鼓吹共產理想,用以匡正當代歐洲的社會亂象,其中尤以貧富不均、酷法傷民(竊銖者誅)和佞臣當道為甚。摩爾虛構對話,辯論而不下結論;在命名中暗藏玄機,例如希適婁岱的名字意為「瞎掰之人」,首都艾默若意為「晦暗不明」等等,刻意留下曖昧空間,不做定論。尤其全書結尾摩爾所下的結語更是反覆推託,耐人尋味:
聽完拉斐爾講的故事,我實在覺得烏托邦的法律和習俗有不少甚是荒謬。比如說他們的戰爭方法,他們的宗教措施,以及其他的風俗。但是我最不能認同他們的基本體制,也就是集體生活和不使用金錢的經濟制度。單是這個體制就足以完全抹殺一般人所認定的一個國家的炫爛光采:它的高貴、宏偉、壯麗和皇族氣派等。可是我知道拉斐爾說得倦了,也不確定他能不能接受相反的意見,又記起來他曾經罵過某種人,說他們惟恐被認為無知,因而拼命在別人話裡找碴。我於是一邊讚美烏托邦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精采敘述,一邊牽起他的手領他到屋裡用餐。進屋之前我說將來要再找時間,跟他進一步討論這些事情。但願這個願望可以實現!
如此的隱晦修辭對一位久在仕途、老於世道的摩爾是必要的自保策略。他攻擊甚多當代的政經亂象,其一是苛法,其次便是朝政。《烏托邦》批判16世紀初的「新政治」和「新經濟」。前者獨尊君王的謀略,朝臣阿諛奉承攀緣急進;後者執行圈地政策,圖利地主,廢除傳統公田農地,致使貧民無地生產糧食,終致淪為盜賊,陷困法律羅網遭處極刑。「新經濟」的受益者除了貴族地主之外,尚有當時新興的自耕農,圖望政府徹底實行土地私有制。摩爾的願景其實是向後看,回到柏拉圖的共有體制,以及中古時期群體社會的農業生產模式。希適婁岱在第一部分摹想自己勸諫君王勿窮兵黷武,要愛民如子,要興利革弊,要端正朝風,一如他在烏托邦所見。他自覺與仕途格格不入,實是代言摩爾內心的矛盾,也使摩爾借此與當時麥基維利《君王論》所倡行的「朝廷青雲路」隔空辯論。置於當時政治與經濟的「新」格局之中來看,《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理念顯然是不合時宜的,或者可以說是傻子的行徑(folly)。摩爾在全書結尾說反話,刻意以「荒謬」稱之。依拉斯默斯在《傻人頌》(The
Praise of Folly)中談傻子的行徑,其中之一正是在滔滔濁世奢談仁義道德。此書拉丁文書名為 Moriae Encomium ,拉丁文morus原意為「傻子」,與摩爾的姓 (More)相近。《傻人頌》成稿於依氏做客摩爾府邸時,其實便是頌揚摩爾的不合時宜的人品道德與理想願景。
烏托邦不是樂園
古典希臘羅馬文學的傳統中早有樂園的文類,描寫一個無拘無束、不虞匱乏的極樂世界。「柯坎樂土」(The Land of
Cockayne)和「農神節慶」(Saturnalia)是兩個知名的例子。在樂園之中沒有憂愁勞苦,亦無法律道德的綑綁,人人飲食享樂稱心如意。《烏托邦》不是樂園,它倡議的是行為規範、集體生活、公民教育和肅穆的宗教信仰。人生的價值可以總結為「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人生的目標不在當下的享樂,而在追求靈魂的不朽。摩爾雖建構一個非基督教的城邦理想國,但是卻以討論宗教信仰為全書收尾;雖不明白宣揚基督教,其實所談一神論和貶抑拜物迷信等,皆在鋪架基督教的基礎教義。他特別讚許僧院的公有共工及守貞制度,認為是人類克己復禮(上帝之道)的極致行為。如此的理念與古典希臘羅馬的俗世欲念大相逕庭,甚至可以說是「違反人性」的。後世出現的「反烏托邦」主題,批判的正是烏托邦的壓抑個體。
摩爾的《烏托邦》和他所揭櫫的理念隱含許多弔詭,有些屬於形式和技巧 (例如,對話和文字創意),有些卻是反映人類面對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徘徊猶豫。烏托邦人將快樂定義為生時悟道之樂與死後靈魂的極樂,與多數人類追求的俗世快樂完全不同。摩爾少時曾想出世為僧,後來卻出仕為官享受高位,最終選擇「傻子行徑」,為了信仰拋捨頭顱,畢竟都是一己的抉擇。
烏托邦的想像視界虛實糾葛,陳述的是個人內心的欲求,在現實世界中很難或無法實現的願景。
烏托邦文類衍異至21世紀,種類繁多,單以性別主題而言,有女性主義烏托邦,爭取與男性平等的自主權;亦有同志烏托邦,抗拒傳統的男∕女區分。摩爾在《烏托邦》中提高婦女的地位(例如,年長的寡婦有資格被選舉擔任神職),但是為人妻者在每月月尾之日必須遵照傳統,向丈夫下跪,懺悔一個月來所犯的過錯。摩爾彷彿單腳跨進「現代」的門檻,另一隻腳卻還懸在中古時期。他對我們今天所界定的人權猶不一定擁護,遑論女權。但是,平等民主,確是他鼓吹的重要理想。
理想國的想像因人而異,建構成為政治和社會的藍圖,則需要擘劃執行面的典章制度。摩爾的烏托邦強調教育,用以培養公民道德,以今天的說法就是利用國家機器來鞏固群體意識,這正是傅柯(Michel Foucault) 等人所要顛覆的權力宰制。但是,無可諱言地,理想國的社會秩序和福利卻也是眾多現代人心之所嚮往。因此,烏托邦的想像是一則選擇題,不是一則是非題。
疑點重重:烏托邦是不是摩爾的理想國?
長久以來,研究《烏托邦》的學者經常擺盪在兩個選項之間,爭議烏托邦究竟是,或者不是,摩爾心目中的理想國。烏托邦的終極理想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制度,以及崇尚理性的行為制約。前者的體現為公有財產,後者則藉由教育和法律達成。個人福祉必須依存於公眾福祉之下,集體安定絕對優先於私人自由。如此之理念與執行方法與近世啟蒙以降的個人主義思潮簡直南轅北轍。烏托邦的制度對人民的日常生活有諸多限制,例如旅行必須報准、職業世襲、房舍設計排除隱私權、設奴隸階級,以及家內由父權宰理等,在在皆壓制「自由、平等、博愛」的浪漫情操。另外,烏托邦人用兵之道首重賄賂及刺殺,似非君子之所為。他們依賴傭兵鞏固國防,也會為紓解國內人口壓力,取得殖民地而興戰。這些做法自然是考量本國的利益,為了維護鞏固經濟和社會的安定,但在道德上卻萬萬稱不上「理想」。
持正面看法的學者則認為,《烏托邦》揭櫫理想,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心情意圖匡正人心。詹柏士說:「烏托邦人只有理性作為人生的指引便有如此之境界;哀乎,信仰基督的英國人!哀乎,信仰基督的歐洲人!」(128) 大儒劉易士(C. S. Lewis)亦讚揚此書諷諫世道的立意和文學技巧,認為它成功地展現「一面諷刺的明鏡」(“a satiric
glass”)(68),照映世人的貪婪。劍橋大學出版的《烏托邦》英譯本的三位譯者(Logan, Adams, Miller)贊同此一功能論,為書中烏托邦人的殖民政策緩頰,認為摩爾面對社會動亂和擴張主義的兩難,選擇他認為的較小的禍害。他們說,《烏托邦》是一本鬱卒的書(“a rather melancholy
book”)(xxxiii),從作者選擇書名Utopia(烏有之美邦)以及主角之名Hythloday(瞎掰的人),可以看出他的自我調侃。全書結尾時,他更說烏托邦難以在現世實現。書中諸多矛盾語或不合世情的細節,甚多出自促狹的修辭策略,也顯露摩爾的游移進退的心情。此外,摩爾長久浸淫於路西安(Lucian)的詭譎傳統,善於利用對話的辯證特質,同時並陳對立的兩種立場,但不明示結論。實則,他自少即仰慕僧院的共工共產制度,以及發揚古哲的理想國理念,一生不曾改變。
另派學者則單挑書中負面的意象及修辭。烏托邦狀若新月,兩個犄角既不完美亦非吉兆;首都艾默若字義晦暗;烏托邦人喜愛僱用兇煞殺手札波人;雖不愛金銀,卻以金銀作為勝戰的工具;女權不張,妻子須向丈夫下跪告解等等。既有如許多的瑕疵,如何稱得上理想國?
這些質疑都是書中的事實。摩爾沒有為烏托邦人的道德辯解,讀者只能依自己的自由心證,自行判斷褒貶。但不可否認的是,摩爾仿效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傳統的理想城邦,描繪守分盡責的國民;他寫的不是君子國和仙界聖人。事實上,烏托邦的理想——小國寡民,自給自足——在摩爾的時代早已是過時之物(anachronism),或者說是一個無以實現的欲求。自摩爾以後,文人模仿《烏托邦》之作甚多,甚且有付諸行動的實踐,可見認同者所在多有。但是,理想往往擱淺在現實的礁石上,失敗也成了公社實驗的常律。史上有名的例子包括19世紀30年代盛行的傅立葉主義(Fourierism),和它所啟迪的波士頓郊外的公社組織Brook
Farm。亦有懷疑其理想性者,則突顯烏托邦體制的威權,以及它對人性的宰制,例如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咸認為是反烏托邦文學的代表作。
烏托邦是善是惡?摩爾已然列位仙班,無從求解。他即便在世,恐怕只會莞爾一笑,淡淡地說:信者恆信。
翻譯《烏托邦》
本書除了《烏托邦》正文,另譯出正文前後的信函和讚詩,以及正文頁緣的眉批。這些附文(parerga)(另含地圖與烏托邦字母表)先後收錄於四個拉丁文版本中,是摩爾和一群人文主義學者友人的集體創作,為此書營造聲勢和加強其「真實性」。翟理斯和摩爾以及卜茲萊頓之間的信函解釋書中為何未提烏托邦的地理位置(希適婁岱正說時一旁有人咳嗽,把他的話遮了過去),以及希適婁岱確有其人(據說當年3月1日還有人見到他)等,保證「書中一無謊言」。眉批是翟理斯在付印之前所加,用以加強文意或製造反諷效果。讚詩類近打油詩,由摩爾一群歐陸文友學者分頭寫就,顯現此輩文儒慣常採用的嘻笑風格,刻意吹捧此書。正文和附文相輔相成,合成一則理想國的虛構想像。
《烏托邦》拉丁文版共有四版,學者以第三版(1518年3月巴塞爾版)為標準版。英文版則以1995年劍橋大學版的注釋最為詳盡,且附拉丁文原文供參照。此次再譯為中文,除正文之外亦譯出附文的重要篇章,冀求呈現摩爾書寫策略的全貌。落筆之時亦參考比對不同英譯本和拉丁文原文,原文所無之句讀分段悉依劍大版。原文語意不明而致各版英譯有所差異時,則取簡潔合理之義。摩爾的拉丁文體混合不同的語用特色(俗語、教會講道用語、法律用語、歷史敘述用語等),語法則難脫拉丁文的迂迴本色,英譯本亦常見冗長晦澀的句子,偶令譯者興起擲筆逃遁之心。此書譯事過程之中重溫荒廢多年的拉丁文,此外要感謝不同的英譯者,他們的譯文和注釋令我受益良多。幾位中譯前輩也在許多地方指引我免於犯錯,在此一併申謝。如仍有誤,未來如有再版定予校正。
宋美?
92年元月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