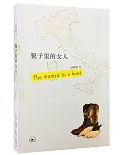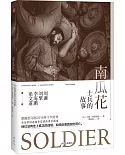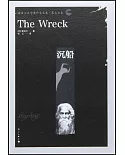《飛鳥集》是一部富於哲理的英文格言詩集,共收錄詩325首,初版於1916年完成。
其中一部分由詩人譯自自己的孟加拉文格言詩集《碎玉集》(1899),另外一部分則是詩人1916年造訪日本時的即興英文詩作。
詩人在日本居留三月有余,不斷有淑女求其題寫扇面或紀念冊。
考慮到這一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些詩何以大多只有一兩行。詩人曾經盛贊日本俳句的簡潔,他的《飛鳥集》顯然受到了這種詩體的影響。
因此,深刻的智慧和簡短的篇幅為其鮮明特色。美籍華人學者周策縱先生認為,這些小詩「真像海灘上晶瑩的鵝卵石,每一顆自有一個天地。
它們是零碎的、短小的;但卻是豐富的、深刻的」,可謂言之有理。
《新月集》是詩人歷經人世滄桑之後,從睿智潔凈心靈唱出的天真的兒歌,詩人熔鑄兒時的經驗,借助兒童的目光,營造了一個晶瑩的童話世界。而深達的哲理,則時時從童稚的話語和天真的畫面中流露出來。
可以說,智者的心靈與純真的童心在《新月集》里達到了最 好的融合。
《吉檀迦利》最 早顯示了泰戈爾的獨特風格。
從形式上看,這是一部獻給神的頌歌,「吉檀迦利」就是「獻詩」的意思。
但泰戈爾歌頌的並不是「一神教」擁有絕對權威、巍然凌駕於萬物之上的神,而是萬物化成一體的泛神,是人人可以親近、具有濃厚平民色彩的存在。
《吉檀迦利》所表現出的泛神論思想,無疑與印度古代典籍如《奧義書》等息息相通。但泰戈爾在發揚本民族傳統的時候,並無意營造一個封閉的世界,他渴望長期隔絕的東西方能夠不斷接近、溝通。
《園丁集》是一部「生命之歌」,但較多地融進了詩人青春時代的體驗,細膩地描敘了愛情的幸福、煩惱與憂傷,其實可以視為一部青春戀歌。
不過,詩人是在回首往事時吟唱出這些戀歌的,在回味青春心靈的悸動時,他無疑又與自己的青春經驗保有一定距離,可以相對地進行理性審視和思考,從而使這部戀歌不時閃爍出哲理的光彩。
冰心(1900—1999),福建長樂人,原名謝婉瑩。現代著名詩人、作家、翻譯家、兒童文學家。作品充滿了對母愛和童真的贊頌、對大自然的詠嘆與熱愛,以及對人生的思考與感悟。
母愛、童真、自然構成了她「愛的哲學」,「有了愛就有了一切」是她的創作信仰。語言風格典雅秀逸,清麗淡遠,柔和凝練的文字之中滲透著率真的個性。其代表作多次入選語文課本,成為永恆的經典,影響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生於浙江溫州,原籍福建長樂。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泰戈爾,印度的一位傑出的詩人、小說家、戲劇家。
在他長達60年的文學生涯中,他總共創作了50多部詩集,12部中、長篇小說,100多篇短篇小說,20多個劇本,此外,還寫了大量的關於文學、語言、宗教、哲學、歷史、政治等方面的論著,為印度近代文學奠定了基礎,也為整個東方文學贏得了廣泛的世界聲譽。
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東方作家,他的詩在印度享有史詩的地位
著名作家冰心等翻譯,印度的「詩聖」完美演繹生命與哲理的相遇。
他熏陶了一批中國最有才華的詩人和作家,郭沫若、冰心等深受影響。
1919年他拒絕了英國國王授予的騎士頭餃,成為第一個拒絕英王授予的榮譽的人
序
譯詩是一件最 不容易的工作。原詩音節的保留固然是絕不可能的事!
就是原詩意義的完全移植,也有十分的困難。散文詩算是最 容易譯的,但有時也須費十分的力氣。如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葉集》便是一個例子。
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有許多詩中特用的美麗文句,差不多是不能移動的。
在一種文字里,這種字眼是「詩的」是「美的」,如果把他移植在第二種文字中,不是找不到相當的好字,便是把原意丑化了,變成非「詩的」了。在泰戈爾的《人格論》中,曾討論到這一層。
他以為詩總是選擇那「有生氣的」字眼,——就是那些不僅僅為報告用而能融化於我們心中,不因市井常用而損壞它的形式的字眼。譬如在英文里,「意識」(consciousness)這個字,帶有多少科學的意義,所以詩中不常用它。印度文的同意字chetana則是一個「有生氣」而常用於詩歌里的字。
又如英文的「感情」(feeling)這個字是充滿了生命的,但彭加利文①里的同意字anubhuti則詩中絕無用之者。
在這些地方,譯詩的人實在感到萬分的困難;第二,詩歌的文句總是含蓄的,暗示的。
他的句法的構造,多簡短而含義豐富。有的時候,簡直不能譯。如直譯,則不能達意。如稍加詮釋,則又把原文的風韻與含蓄完全消滅,而使之不成一首詩了。
就是原詩意義的完全移植,也有十分的困難。散文詩算是最 容易譯的,但有時也須費十分的力氣。如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葉集》便是一個例子。
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有許多詩中特用的美麗文句,差不多是不能移動的。
在一種文字里,這種字眼是「詩的」是「美的」,如果把他移植在第二種文字中,不是找不到相當的好字,便是把原意丑化了,變成非「詩的」了。在泰戈爾的《人格論》中,曾討論到這一層。
他以為詩總是選擇那「有生氣的」字眼,——就是那些不僅僅為報告用而能融化於我們心中,不因市井常用而損壞它的形式的字眼。譬如在英文里,「意識」(consciousness)這個字,帶有多少科學的意義,所以詩中不常用它。印度文的同意字chetana則是一個「有生氣」而常用於詩歌里的字。
又如英文的「感情」(feeling)這個字是充滿了生命的,但彭加利文①里的同意字anubhuti則詩中絕無用之者。
在這些地方,譯詩的人實在感到萬分的困難;第二,詩歌的文句總是含蓄的,暗示的。
他的句法的構造,多簡短而含義豐富。有的時候,簡直不能譯。如直譯,則不能達意。如稍加詮釋,則又把原文的風韻與含蓄完全消滅,而使之不成一首詩了。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