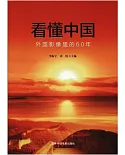看戲久了,人也變戲了——王家衛、許鞍華、止庵,約你一起與馬家輝看戲
本書是香港著名作家馬家輝繼《江湖有事》和《愛戀無聲》之後的最新影評力作,評論所及均為當下熱門的電影和電影人、文化人。
從奪得奧斯卡大獎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生死朗讀》到新近電影《南京!南京!》、《天水圍的日與夜》、《赤壁》、《梅蘭芳》、《葉問》等;從老伍迪、西恩•潘、黑澤明談到王家衛、徐克、許鞍華、吳宇森、陳可辛、沈殿霞、李小龍、張愛玲等。作者如數家珍,娓娓道來,借影像起始,寫盡人間情事。銀幕上下戲里戲外的人生交織成一幅如夢如幻的美妙畫卷。
電影院是馬家輝精神和肉身的“comfort zone”,影評是馬家輝愛恨情仇的宣泄表達。“馬家輝式”影評書寫的不僅是電影,更是作者對人生種種的看法。這一次,馬家輝用整本《明暗》寫盡人間情事。
書中除了影評,更有一些時事評論文章把馬家輝的學院派理論根底、傳媒人的開闊視野與文人的筆墨功夫展露無遺。從錢鐘書、柏楊、高信疆談到塞林格、蘇珊•桑塔格,從一段段關于個體生活的曲折輪廓與隱約紋路中,作者寫出了所寄身的民族和國家共同經歷的時代,以及時代背後所有的繾綣顧念與微言大義。
書中品電影、談文化、寫情感、說人生,每一種都刻印著時間的風塵,埋藏著歲月的情愫,展現的不僅是一位俯首書案的讀書人對于電影、文化、人生的理解和釋讀,也是回首前塵的懷舊者對于生活的感知和體悟。
馬家輝,傳媒人、專欄作家、文化評論學者、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嘉賓。1963年出生于香港。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威斯康星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香港《明報》世紀副刊創意策劃,為兩岸三地多份報章雜志撰寫評論及隨筆。2008年以“博雅之魅”獲選《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國魅力五十人物”之一。
目錄
序 發乎情,不止乎理
自序 送一本書給電影院
[輯一]戀繁花
繼續微笑
在婚姻里遺忘愛情
終于看懂了王家衛
媚艷的觀音
男人的眼淚
誰欺負了梅蘭芳
花樣容顏
又見天水圍
有這樣的一位小觀眾
張愛玲回來了
[輯二]憶殘夢
始終是吳宇森
陳可辛的好兄弟
如果‧南京
最曖昧的所在
奔跑在城市
黑暗回廊
執起一把武士刀
這群叔叔伯伯以及嬸嬸
死亡的滋味
某年某月某些人
自序 送一本書給電影院
[輯一]戀繁花
繼續微笑
在婚姻里遺忘愛情
終于看懂了王家衛
媚艷的觀音
男人的眼淚
誰欺負了梅蘭芳
花樣容顏
又見天水圍
有這樣的一位小觀眾
張愛玲回來了
[輯二]憶殘夢
始終是吳宇森
陳可辛的好兄弟
如果‧南京
最曖昧的所在
奔跑在城市
黑暗回廊
執起一把武士刀
這群叔叔伯伯以及嬸嬸
死亡的滋味
某年某月某些人
序
家輝兄的文章,我最早是在《深圳商報》的“文化廣場”讀到,還記得專欄的名字叫“深港情書”。從前廢名說梁遇春,“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處處閃眼,然而沒有一個線索,稍縱即逝,他不能同一面鏡子一樣,把什麼都收藏起來。”( 《序》)我對家輝兄亦有此等感慨,我佩服他文思敏捷,而且無所不談。
我一向羨慕能寫專欄的朋友,自己就成。偶有編輯約寫,我總把交稿期盡量推遲,生怕到時交不了卷。這除了才情高下有別,亦與文章寫法不同有關。我們看一部電影,讀一本書,思考是個延續的過程,專欄文章寫的是上半句”,另一路寫的是“下半句”。廢民所講也是這種區別。相比之下,或者或許稍稍安穩,但也少了許多鮮活,而且沒有“上半句”,經常也就沒有“下半句”。胡適在日記中說︰“今天在《晨報》上看徐彥之君的《去國日記》的末段引Graham Wallas的話︰﹀人的思想是流動的,你如果不當時把他用文字記下,過時不見,再尋他不得。所以一枝筆和一片紙,要常常帶在身邊。﹀這話很使我感動。我這三四年來,我也知被我的懶筆斷送了多少很可有結果的思想,也不知被他損失了多少可以供將來的人做參考資料的事實。”我看《明暗》,覺得正可移來用上,蓋這里多有“很可有結果的思想”,多有“可以供將來的人做參考資料的事實”;而我對此只能發發的“我的懶筆”之類的感慨了。
我們寫文章,常常是“發乎情,止乎理”;家輝兄則是“發乎情,不止乎理”。他好像有意要把《明暗》這類文字,與他那些看來分量更重的評論作品區分開來。周作人在《美文》中說︰“外國文學理由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里邊又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所雲“論文”,即與散文中間的橋。”應該是專就抒情一路而言。後來周作人為俞平伯《燕知草》寫跋,又提到“論文——不,或者不如說小品文,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抒情分子為主的,有人稱他為﹀絮語﹀過的那種散文”,《明暗》正是這種“絮語”。中國新聞學史上,寫“絮語”大概要推梁遇春為最長乘,特別是《淚與笑》,比他的《春集》更好。開頭所引廢名的話,是站在批評和敘事的立場去看抒情,他接了苦雨齋的衣缽,早已“止乎理”了,我所發類似感慨亦如是,說穿了都是“門戶之見”。相比之下還是知堂翁胸襟寬廣,因為其實他也不寫抒情之作的。
……
我一向羨慕能寫專欄的朋友,自己就成。偶有編輯約寫,我總把交稿期盡量推遲,生怕到時交不了卷。這除了才情高下有別,亦與文章寫法不同有關。我們看一部電影,讀一本書,思考是個延續的過程,專欄文章寫的是上半句”,另一路寫的是“下半句”。廢民所講也是這種區別。相比之下,或者或許稍稍安穩,但也少了許多鮮活,而且沒有“上半句”,經常也就沒有“下半句”。胡適在日記中說︰“今天在《晨報》上看徐彥之君的《去國日記》的末段引Graham Wallas的話︰﹀人的思想是流動的,你如果不當時把他用文字記下,過時不見,再尋他不得。所以一枝筆和一片紙,要常常帶在身邊。﹀這話很使我感動。我這三四年來,我也知被我的懶筆斷送了多少很可有結果的思想,也不知被他損失了多少可以供將來的人做參考資料的事實。”我看《明暗》,覺得正可移來用上,蓋這里多有“很可有結果的思想”,多有“可以供將來的人做參考資料的事實”;而我對此只能發發的“我的懶筆”之類的感慨了。
我們寫文章,常常是“發乎情,止乎理”;家輝兄則是“發乎情,不止乎理”。他好像有意要把《明暗》這類文字,與他那些看來分量更重的評論作品區分開來。周作人在《美文》中說︰“外國文學理由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里邊又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所雲“論文”,即與散文中間的橋。”應該是專就抒情一路而言。後來周作人為俞平伯《燕知草》寫跋,又提到“論文——不,或者不如說小品文,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抒情分子為主的,有人稱他為﹀絮語﹀過的那種散文”,《明暗》正是這種“絮語”。中國新聞學史上,寫“絮語”大概要推梁遇春為最長乘,特別是《淚與笑》,比他的《春集》更好。開頭所引廢名的話,是站在批評和敘事的立場去看抒情,他接了苦雨齋的衣缽,早已“止乎理”了,我所發類似感慨亦如是,說穿了都是“門戶之見”。相比之下還是知堂翁胸襟寬廣,因為其實他也不寫抒情之作的。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