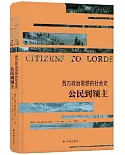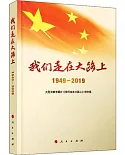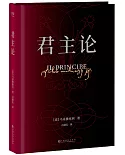三十多年以來,本書在它所涉及的領域內,不僅是一本權威的教科書,而且也是一本得到廣泛承認的經典之作。毋庸贅言,對這樣一部書進行修訂,多少會令人感到有些畏懼的。不過,我知道,我的任務乃是推進、承繼和發展薩拜因教授這部巨著中的觀點,而不是對其論旨或內容做實質性的改動。
修訂另一位作者的著作,肯定是會遇到困難的,而其最大的根源也許是修訂者與原作者在知識視角方面是否一致的問題。薩拜因教授在本書1937年初版的序言中曾經指出,他本人的觀點同大衛·休謨(DavidHume)的觀點在實質上是相似的,尤其是在體謨對自然法的各種基礎性觀點所做的邏輯批判方面。我本人撰寫的《民主的邏輯》(The LogicofDemocracy,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2)一書,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按照休謨的思想傳統來闡發我對政治哲學的看法的。因此,我想這樣說是有道理的,即我對休謨的論辯(懷疑論和經驗主義)的有效性是理解的,也是贊賞的。
然而,像休謨一樣,當然也像薩拜因一樣,我深信文化傳統和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對政治學和政治判斷力有着根本的重要性。拙著《生物政治學》(Bipolitics,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0)為贊同一種認為文化進化(cultural
evoluti。n)是生物進化之擴展或延伸的理論進行了論證。雖說這種理論非常符合上文論及的歷史觀的精神,不過我想,它卻會令休謨和薩拜因略感不快。盡管這里肯定不是對這些問題進行廣泛詳盡討論的場合,但我還是想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即在過去幾十年中,各個領域對人類這一動物的本性和起源所進行的大量研究工作,使得人們對休謨的邏輯批判根本無法否棄的有關人類和自然(本性)的問題進行認識或理解有了可能。
以上所述意味着:我發現自己要比薩拜因教授更贊同自然法傳統和黑格爾與馬克思的進化觀,而這一傾向則構成了我修訂本書的基礎。《政治學說史》本版的第一章是新增的,其目的在於將政治理論史納進一個由人類進化和前希臘(即前哲學思想)構成的背景之中。原本我還打算就西方政治理論對非西方世界滲透的問題做一番詳盡的討論,但是在本次的修訂工作中,我只是在討論共產主義一章中新增添了有關中國和毛澤東的一節文字。此外,我對許多散見於本書論述中的判斷做了更為溫和的處理,而這通常是通過刪節若干詞句的方法達到的,最為顯見的便是我在論黑格爾一章中刪去了好幾頁文字。
在《政治學說史》的第三版(1961年)當中,薩拜因不僅重寫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縮短了他對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討論。然而,在過去的十二年中,人們對這個論題的興趣卻因為種種緣故而在各個地方又被重新激發了出來,因此我把薩拜因有關上述問題的原有討論文字又重新刊發了出來。再者,參考文獻也已根據相關研究的發展而做了全面的更新,並在若干地方增加了新的腳注或在已有的腳注中增加了新的文獻。
最后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是,《政治學說史》第四版的版式和字體也做了全新的設計和安排,期望此舉能夠使人們更方便且更舒服地閱讀喬治·薩拜因的聰穎智慧和偉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