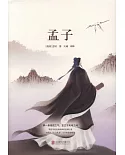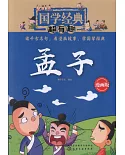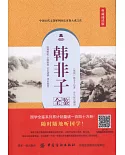內容簡介
《莊子》是中國古代的絕世經典,兩千多年來,對其解讀注釋者不一而足。本書是一部全新的解讀《莊子》之作,作者在領會莊文時強調了“懸置”概念思維,並力圖以莊文借以產生的“象思維”走進莊子文本,因而別開生面。莊文主體為寓言,其中所謂重言、卮言都從屬于寓言本旨。這種本旨,就是“以文築象,以象生境,以境寫意”。這就使莊文具有以象征和隱喻表現的詩意不確定性,並使莊文在思想上具有開啟原發性創生的無限可能性,而莊文的博大深邃和永恆魅力亦在于此。全書重心在于體悟和具體闡發莊子“道通為一”這種大智慧,將詮釋寓于評述之中,逐篇評述,評釋結合,並注意古今比較與中西比較,從而不僅揭示出莊文之思的本真意蘊,而且揭示出它的現代意義與世界意義。
目錄
自序
緒論
內篇
《內篇》引言
“游無窮”——《逍遙游》述評
“道通為一”——《齊物論》述評
“緣督以為經” 而由技入道——《養生主》述評
“心齋”“坐忘”與 “無用之用”——《人間世》述評
“德者成和”而 “德不形”——《德充符》述評
“朝徹”“見獨”“無古今”“不死不生”——《大宗師》述評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應帝王》述評
外篇
《外篇》引言
“非以仁義易其性”——《駢拇》述評
“同德”“天放”——《馬蹄》述評
“好知而無道則天下亂”——《篋》述評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宥》述評
“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天地》述評
“明于天,通于聖”——《天道》述評
“所常無窮”“道不可壅”——《天運》述評
“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刻意》述評
“以恬養知”“莫之為而常自然” ——《繕性》述評
“萬物一齊”“道無終始”——《秋水》述評
“至樂無樂” ——《至樂》述評
“其天守全,其神無”——《達生》述評
“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述評
“哀莫大于心死”——《田子方》述評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知北游》述評
雜篇
《雜篇》引言
“萬物出乎無有”“動不知所為”——《庚桑楚》述評
“以天待人”——《徐無鬼》述評
“道者為之公”——《則陽》述評
“去小知而大知明”——《外物》述評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述評
“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 ——《讓王》述評
“不以美害生,不以事害己”——《盜跖》述評
“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漁父》述評
“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列御寇》述評
“析萬物之理,察古今之全”——《天下》述評
參考文獻
後記
緒論
內篇
《內篇》引言
“游無窮”——《逍遙游》述評
“道通為一”——《齊物論》述評
“緣督以為經” 而由技入道——《養生主》述評
“心齋”“坐忘”與 “無用之用”——《人間世》述評
“德者成和”而 “德不形”——《德充符》述評
“朝徹”“見獨”“無古今”“不死不生”——《大宗師》述評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應帝王》述評
外篇
《外篇》引言
“非以仁義易其性”——《駢拇》述評
“同德”“天放”——《馬蹄》述評
“好知而無道則天下亂”——《篋》述評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宥》述評
“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天地》述評
“明于天,通于聖”——《天道》述評
“所常無窮”“道不可壅”——《天運》述評
“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刻意》述評
“以恬養知”“莫之為而常自然” ——《繕性》述評
“萬物一齊”“道無終始”——《秋水》述評
“至樂無樂” ——《至樂》述評
“其天守全,其神無”——《達生》述評
“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述評
“哀莫大于心死”——《田子方》述評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知北游》述評
雜篇
《雜篇》引言
“萬物出乎無有”“動不知所為”——《庚桑楚》述評
“以天待人”——《徐無鬼》述評
“道者為之公”——《則陽》述評
“去小知而大知明”——《外物》述評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述評
“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 ——《讓王》述評
“不以美害生,不以事害己”——《盜跖》述評
“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漁父》述評
“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列御寇》述評
“析萬物之理,察古今之全”——《天下》述評
參考文獻
後記
序
《莊子》一書主要以象征隱喻的寓言表達其思想,它是一種詩意的表達。如果說“詩無達詁”,那麼《莊子》也屬于“無達詁”之列。至于《莊子》書中在表達上具有跳躍性和看似不著邊際的“卮言”,以及具有史實性的“重言”,也都是服從于以寓言喻道這條主線。即使是作為具有史實性的“重言”,也不是為了揭示和討論歷史,而是借史實使喻道之喻更加充實有力。莊周及其弟子們,其所以采用詩意的表達,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作為道家的繼承者和集大成者,深刻領會了“道”之可體悟而不可言傳性,如老子所說“道可道,非常道”,以至于“道”之名,老子都認為是“強字之曰”。後來禪宗的“不立文字,以心傳心”,可以說與“道”之可體悟而不可言傳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雖如此說,老子不還是道說了五千言嗎?禪宗不也有《六祖壇經》和諸多傳燈錄嗎?可知,人類發明了語言,語言就與人類結下了不解之緣。因此,問題不是用不用語言,而是如何用語言。實際上,從老子到莊子及其弟子,都是用詩意的語言在築境的描述中喻道,而不是用概念規定性的語言來指稱道。“道可道,非常道”,就是指出使用概念規定性的語言所作的道說,結果只能是背離“常道”。莊子則進一步說︰“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知北游》)那麼,用詩意的語言來喻道,例如老子常用比興的詩體和莊子用詩意盎然的寓言,又會如何?
從“詩無達詁”來看,詩意的表達具有多指向的不確定性和模糊的混沌性,讀之不像概念規定那樣確定和明晰,特別是莊子的寓言,其隱喻性甚至使人有墮五里霧中之感。然而,如果我們能領會“道”的本性,就不難知曉老莊用詩意的寓言喻道之良苦用心了。那麼,道之本性如何呢?與西方哲學最高實體本質不同的“道”,乃是非實體性的。實體是一種概念,是以主客二分為前提的,是對象性的和現成性的。因此,可以作為對象而發問“實體是什麼”的問題,即可以借助概念思維怍規定和分析推理。而“道”不是可以作為對象的實體概念,而是以“天人合一”或主客一體不分為前提的,因之“道”是非對象性的和非現成性的。或者說,“道”與靜態的非整體性的實體不同,它是動態整體性的。所以,對于動態整體性的“道”,根本不能問“道是什麼”的問題,因為這種發問就是從概念思維出發的,就是引向“S是P”這種概念思維的規定和分析推理。由這種發問而進入概念思維,不僅不能把握“道”,而且容易使“道”在對象化和現成化中被肢解和僵化,導致從根本上背離“道”。莊子就此問題有這樣的論說︰“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知北游》)由此可知,“道”的提出,源自不同于概念思維的另一種思維,即“象思維”。因此,把握“道”也不能不用這種有別于概念思維的“象思維”。無論是老子比興的詩體表達,還是莊子詩意盎然的寓言表達,都是悟性的“象思維”之產物。這種詩意表達也是老莊引導讀者進入悟性的“象思維”來體“道”,而非作概念思維的邏輯推理。
《莊子》一書通過寓言所喻,是深邃的道境。因此,對于《莊子》一書,若想把握其“道”的玄旨,就不能不首先“懸置”概念思維的慣常心態,用把玩和體悟的心態,去玩味和領悟寓言所築之境。如《莊子》中所謂“心齋”、“坐忘”、“外物”、“無古今”、“吾喪我”、“虛室生白”等等.都不是概念規定,而是境域和境界的描述。顯然,這種境域和境界用概念規定是無從把握的,而只有徜徉在隱喻之象的境域中,虛心地細細領會,才能領悟其“道”之玄旨。“道”囊括萬有而又無所不在的整體性及其“生生不已”的原發創生性,是多姿多彩而又永遠鮮活的。老子所謂“道之為物”,即表明“道”無所不在,而且“道”也在“生由不已”中表現為時時鮮活。所以,對之描述和隱喻也不能不是多彩而又鮮活的。這樣.莊子及其弟子的寓言描述哆彩紛呈,也就不難理解了。莊子的道境給我們提供的是一種原發創生的動態整體觀,即所謂“道通為一”,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因此,對于“道”的描述也就處處時時皆可為之。由此所給予人的重要啟示是,“道”既然如此處處時時鮮活,人之體“道”也就可以處處時時為之。六祖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完全與此相通。
可以說,領會《莊子》一書的原發創生的動態整體觀,是把握《莊子》一書的大前提。因為,原發創生的動態整體觀是貫穿《莊子》一書的靈魂主線。在書中,無論批判“道”外種種不能“道法自然”的逆思逆行,還是弘揚回歸“道”內能順乎“自然之道”的思與行,都是圍繞這條靈魂主線展開的。以往對《莊子》的研究,更多是對詞語的考證和注疏,有的甚至陷入支離瑣碎而不能把握整體之“道”,或者是囿于概念思維視角,與“道”隔離,這樣就更不可能真正領會“道”之玄旨。在《莊子》研究中,能站在原發創生的動態整體觀這一高度,注意到《莊子》一書思維方式的特質的,似乎還不多。本書作者也只是試圖朝這個方向努力而已。
……
從“詩無達詁”來看,詩意的表達具有多指向的不確定性和模糊的混沌性,讀之不像概念規定那樣確定和明晰,特別是莊子的寓言,其隱喻性甚至使人有墮五里霧中之感。然而,如果我們能領會“道”的本性,就不難知曉老莊用詩意的寓言喻道之良苦用心了。那麼,道之本性如何呢?與西方哲學最高實體本質不同的“道”,乃是非實體性的。實體是一種概念,是以主客二分為前提的,是對象性的和現成性的。因此,可以作為對象而發問“實體是什麼”的問題,即可以借助概念思維怍規定和分析推理。而“道”不是可以作為對象的實體概念,而是以“天人合一”或主客一體不分為前提的,因之“道”是非對象性的和非現成性的。或者說,“道”與靜態的非整體性的實體不同,它是動態整體性的。所以,對于動態整體性的“道”,根本不能問“道是什麼”的問題,因為這種發問就是從概念思維出發的,就是引向“S是P”這種概念思維的規定和分析推理。由這種發問而進入概念思維,不僅不能把握“道”,而且容易使“道”在對象化和現成化中被肢解和僵化,導致從根本上背離“道”。莊子就此問題有這樣的論說︰“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知北游》)由此可知,“道”的提出,源自不同于概念思維的另一種思維,即“象思維”。因此,把握“道”也不能不用這種有別于概念思維的“象思維”。無論是老子比興的詩體表達,還是莊子詩意盎然的寓言表達,都是悟性的“象思維”之產物。這種詩意表達也是老莊引導讀者進入悟性的“象思維”來體“道”,而非作概念思維的邏輯推理。
《莊子》一書通過寓言所喻,是深邃的道境。因此,對于《莊子》一書,若想把握其“道”的玄旨,就不能不首先“懸置”概念思維的慣常心態,用把玩和體悟的心態,去玩味和領悟寓言所築之境。如《莊子》中所謂“心齋”、“坐忘”、“外物”、“無古今”、“吾喪我”、“虛室生白”等等.都不是概念規定,而是境域和境界的描述。顯然,這種境域和境界用概念規定是無從把握的,而只有徜徉在隱喻之象的境域中,虛心地細細領會,才能領悟其“道”之玄旨。“道”囊括萬有而又無所不在的整體性及其“生生不已”的原發創生性,是多姿多彩而又永遠鮮活的。老子所謂“道之為物”,即表明“道”無所不在,而且“道”也在“生由不已”中表現為時時鮮活。所以,對之描述和隱喻也不能不是多彩而又鮮活的。這樣.莊子及其弟子的寓言描述哆彩紛呈,也就不難理解了。莊子的道境給我們提供的是一種原發創生的動態整體觀,即所謂“道通為一”,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因此,對于“道”的描述也就處處時時皆可為之。由此所給予人的重要啟示是,“道”既然如此處處時時鮮活,人之體“道”也就可以處處時時為之。六祖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完全與此相通。
可以說,領會《莊子》一書的原發創生的動態整體觀,是把握《莊子》一書的大前提。因為,原發創生的動態整體觀是貫穿《莊子》一書的靈魂主線。在書中,無論批判“道”外種種不能“道法自然”的逆思逆行,還是弘揚回歸“道”內能順乎“自然之道”的思與行,都是圍繞這條靈魂主線展開的。以往對《莊子》的研究,更多是對詞語的考證和注疏,有的甚至陷入支離瑣碎而不能把握整體之“道”,或者是囿于概念思維視角,與“道”隔離,這樣就更不可能真正領會“道”之玄旨。在《莊子》研究中,能站在原發創生的動態整體觀這一高度,注意到《莊子》一書思維方式的特質的,似乎還不多。本書作者也只是試圖朝這個方向努力而已。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