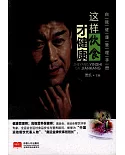人類一日三餐的日常進食行為,被作者上下開合引發出去,竟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吃」不僅僅與政治,戰爭,經濟產生了密切的關系,甚至對人類的思想形成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在作者幽默的論述中,我們重新認識了「吃」的發展和歷程。
「吃」,是生物的本能,但對人類而言,食物絕對不只是果腹的東西,進文化娛樂活動也不只是為了充飢。入口的食物,包含了吃下它的種種過去;而「吃」這個動作,也總有約定俗成的意義,能傳達人類的思想。二次大戰時,美國年輕戰士說,他們是「籽了保衛喝可口可樂的權利而戰。」受盡欺壓勞苦的加勒比海地區奴隸,只有在生產和烹調食物時,才能品嘗到自由的滋味。在甜食市場里,糖和蜂蜜掀起了世紀爭霸戰,由於人類選擇了糖,進而改變了歐洲的經濟和社會形態。而西方社會對於「純潔」的長久向往,對於齒頰間香口感的無限追求,終於在「白色的杏仁蛋白質糖霜」上得到滿足。「吃」,滿足了人類身體上的渴望,實現了情感上、心智上至高無上的追求。
序
家父是個廚子。多年前我姐姐糾正我的說法,堅持要稱為「餐廳老板」。不過我知道他就是個廚子。他最後以廚藝維生,有一段曲折離奇的歷程——大半顛沛流離的苦合人,都有類似的這麽一段過去。
我父母於二十世紀初剛到紐約時,兩人尚未結婚,家父謝洛姆·明茨(Shlomo Mintz)是個制模工,在通信營服完六年兵役,從沙皇軍退伍。家母芙若美·利亞·明茨(Fromme Leah Mintz),曾經在一個名叫德美同盟會(Bund)的猶太人社會主義組織里工作,這個組織受到沙皇政府嚴厲迫害,當她到了紐約,就成為縫紉廉價勞工。不久後,她就加入了世界產業勞工組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簡稱IWW),時人稱該組織會員為「Wobbly」,擔任紐約服裝行業的召集人。我祖父母並不贊成這件事,而且這份工作的薪資也不多。
男性的薪資也好不到哪里。據家父說,一九O一年時,紐約制模工人的周薪才三塊半美元。他又去做服飾業務員,在卡納街工作,老板是某位遠親,不用說,家父每一分種都在咒罵這個工作。不過這里頭又有另一段故事。
我父母的婚姻是表兄妹的親上加親,這是德系猶太人的風俗,不過家母要求要移居到遠離紐約市的小鎮才肯嫁給家父,她不希望在城市里養孩子。家父於是寫信給軍中的老戰友班·杜夫曼(Ben Dorfman),他在新澤西州多佛鎮一家餐館里冼盤子。老班是個孤兒,在軍樂隊里吹奏低音號(tuba),駐防營區碰巧跟家父的單位相同。
他們這對難兄難弟真是再怪不過了。家父對於書本、文字及大半的思想沒什麽興趣,而老班則只對這些東西有興趣;怪的是他們親得很。碰巧當時餐廳老板想再雇用一名晚班的洗盤工人,於是家父離開卡納街這個男裝的業務工作,加入老班在多佛鎮冼碗槽邊的行列。
在紐約一完婚(家母羞於把婚事向IWW的同事公告,因為婚姻是中產階級的制度),父母便搭上火車抵達多佛鎮,再乘一輛單馬馬車到他們的新居,那是間租來的房子,老班則成為在我家長住的客人。他一直住到死於癌症為止,當時我已是個孩童。新澤西州的多佛鎮便是我與手足出生及成長的地方。
我父母搬到那里大約十年之後,「賴卡瓦納小館」(Lackawanna House,就是家父工作的那家餐廳)的老板,買下一座摩天輪,於是把飯館頂給了老班跟家父,然後就跟著流動游樂場走了。我知道這聽起來像是胡謅,不過大人是這麽說的。老班跟家父從我們搬到多佛起,兩人就開始存錢,這時候則一起經營餐館,後來賺夠了錢便另蓋一間大餐廳與旅館。他們走上餐飲業的真正原因,我一直不知道,不過這個決定正好與盧西塔尼亞號被炸沉。及美國加入一次世界大戰吻合。當時由於紐澤西州的多佛鎮有幸成為政府兵工廠與彈藥廠的所在地,餐飲業與旅館業因此蓬勃發展,於是家父也順勢成為「餐廳老板」,這是老姐屢屢要我注意的說法。他還自以為財務金融他也在行。於是這個「老板」的頭餃就一直持續到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跟著所有人一起賠個一窮二白,一夜之間,他從餐廳老板變成了廚子,在別人的餐館里討口飯吃。到他去世前不久,他都只能干個廚子。
……
我父母於二十世紀初剛到紐約時,兩人尚未結婚,家父謝洛姆·明茨(Shlomo Mintz)是個制模工,在通信營服完六年兵役,從沙皇軍退伍。家母芙若美·利亞·明茨(Fromme Leah Mintz),曾經在一個名叫德美同盟會(Bund)的猶太人社會主義組織里工作,這個組織受到沙皇政府嚴厲迫害,當她到了紐約,就成為縫紉廉價勞工。不久後,她就加入了世界產業勞工組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簡稱IWW),時人稱該組織會員為「Wobbly」,擔任紐約服裝行業的召集人。我祖父母並不贊成這件事,而且這份工作的薪資也不多。
男性的薪資也好不到哪里。據家父說,一九O一年時,紐約制模工人的周薪才三塊半美元。他又去做服飾業務員,在卡納街工作,老板是某位遠親,不用說,家父每一分種都在咒罵這個工作。不過這里頭又有另一段故事。
我父母的婚姻是表兄妹的親上加親,這是德系猶太人的風俗,不過家母要求要移居到遠離紐約市的小鎮才肯嫁給家父,她不希望在城市里養孩子。家父於是寫信給軍中的老戰友班·杜夫曼(Ben Dorfman),他在新澤西州多佛鎮一家餐館里冼盤子。老班是個孤兒,在軍樂隊里吹奏低音號(tuba),駐防營區碰巧跟家父的單位相同。
他們這對難兄難弟真是再怪不過了。家父對於書本、文字及大半的思想沒什麽興趣,而老班則只對這些東西有興趣;怪的是他們親得很。碰巧當時餐廳老板想再雇用一名晚班的洗盤工人,於是家父離開卡納街這個男裝的業務工作,加入老班在多佛鎮冼碗槽邊的行列。
在紐約一完婚(家母羞於把婚事向IWW的同事公告,因為婚姻是中產階級的制度),父母便搭上火車抵達多佛鎮,再乘一輛單馬馬車到他們的新居,那是間租來的房子,老班則成為在我家長住的客人。他一直住到死於癌症為止,當時我已是個孩童。新澤西州的多佛鎮便是我與手足出生及成長的地方。
我父母搬到那里大約十年之後,「賴卡瓦納小館」(Lackawanna House,就是家父工作的那家餐廳)的老板,買下一座摩天輪,於是把飯館頂給了老班跟家父,然後就跟著流動游樂場走了。我知道這聽起來像是胡謅,不過大人是這麽說的。老班跟家父從我們搬到多佛起,兩人就開始存錢,這時候則一起經營餐館,後來賺夠了錢便另蓋一間大餐廳與旅館。他們走上餐飲業的真正原因,我一直不知道,不過這個決定正好與盧西塔尼亞號被炸沉。及美國加入一次世界大戰吻合。當時由於紐澤西州的多佛鎮有幸成為政府兵工廠與彈藥廠的所在地,餐飲業與旅館業因此蓬勃發展,於是家父也順勢成為「餐廳老板」,這是老姐屢屢要我注意的說法。他還自以為財務金融他也在行。於是這個「老板」的頭餃就一直持續到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跟著所有人一起賠個一窮二白,一夜之間,他從餐廳老板變成了廚子,在別人的餐館里討口飯吃。到他去世前不久,他都只能干個廚子。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94